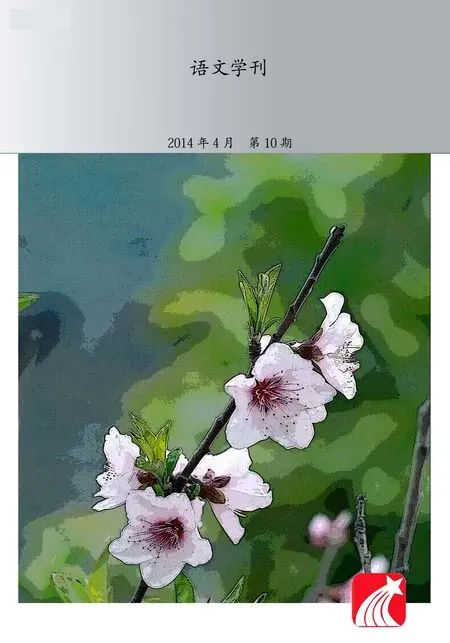中國古代課程文化的價值訴求
○石蘭榮
(商丘師范學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課程文化以學校中群體活動為載體,是師生雙方互動的產物。它包括課程傳承的文化與課程本身的文化特性兩個方面。前者指課程是文化的載體,后者指課程是一種文化形態而言。本文通過梳理中國古代課程文化的發展線索,分析古代課程文化的價值訴求,以期對當代課程文化的建構有所啟示。
一、中國古代課程文化回眸
中國古代語文課程文化歷史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時期,已有了以“六藝”為代表的系統的課程體系。“六藝”課程大致始于周公“制作禮樂”,形成于“成康之治”時期。“六藝”課程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課程中“禮”的主要內容是有關制度、禮儀的知識,包括政治、倫理、法律、風俗等方面。“樂”是藝術理論和實踐知識,包括詩歌、音樂、舞蹈。“射”指射箭的知識,“御”指駕馭馬拉戰車的技術。“書”指的是文字,“數”指的是算法,二者屬于基礎文化知識。
孔子繼承西周“六藝”課程的傳統,在課程設置上,仍采用“六藝”的名稱,但已對課程內容作了調整。《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論語·天運篇》記載,孔子見老聃之后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教材后人稱為“六經”。從所選教材看,孔子的課程內容偏向于社會歷史政治倫理,輕視科技知識與生產勞動知識。
孔子在春秋時期創制的較為完備的課程體系,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至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學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儒家學說遂由民間私學一躍而為官學的課程內容。漢武帝時期在太學設五經博士,《五經》即《易》、《書》、《詩》、《禮》、《春秋》。在《五經》的傳授過程中,由于傳授途徑不一,形成了不同的傳本,代表了不同的經學大師的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即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
隋朝以科舉取士制代替兩漢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作為選拔人才的制度。這一選拔人才制度的改革,使經學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強,以經學為核心的課程內容逐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唐初規定學校教材為《五經正義》,后為了士人修習研讀,對五經作了標準的注釋和義疏;以五經為本,提出九經之名:《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唐前期九經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論語》、《孝經》、《爾雅》三經,經學的內容從九經增加到十二經,經學達到空前統一。至此,中國古代的課程體系已經逐漸完善。
至南宋時期,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將原來屬于《禮記》的《大學》和《中庸》兩篇單獨列出,與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和記載孟子言行的《孟子》并列,分別進行注解,合成《四書章句集注》,簡稱為《章句集注》或《四書》。在宋寧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四書》作為官方課程在全國實施。從本時期開始,到清末廢除科舉制度的近700年間,《四書》、《五經》成為中國官方的統一課程。
明清時期,《四書》作為官方教材,其內容卻不是一成不變。明朝統治者在推崇程朱理學的同時,對其中不利于專制統治的學說,則采取排斥的態度。如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就曾下令對《孟子》一書進行審查,對其中185處進行刪除,規定凡刪除的內容“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刪節后的《孟子節文》在全國學校頒行。清統治者陸續出版《欽定四書文》、《御纂四經》、《欽定三禮》。
二、中國古代課程文化的價值訴求
中國古代課程文化大體分為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兩類。其中道德教育始終是第一位的,知識教育的內容居于第二位,即所謂“學所以為道”。統治者以文教政策為導向,使道德教育在古代教育中始終處于主體地位。
(一)以培養人為課程的終極目標
古代課程以培養人作為終極目標。以儒學課程為代表的古代課程,自始至終都把培養圣賢之人作為課程目標。孔子所說的人才,是具有人倫社會道德教化知識的政治人才,而不是精通某門學科或者技藝的專門人才。根據孔子的教學目標設計,他們應該具有高尚的品德,施行仁政、治國安邦。這一課程目標迎合了當時社會對人才的新訴求,對其后的中國課程體系的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的主張和孔子如出一轍,他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一大快樂中的“英才”,很明顯也是治理國家的政治人才。在繼承孔孟課程目標的基礎上,作為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朱熹提出課程的目標在于造就一代“醇儒”,即圣賢之人,即“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朱熹認為,所謂圣人,要有美好的品格及洞察一切的才能。
可見,古代課程思想家的課程旨趣,不在于知識的獲取,而是把教人學做人作為課程目標。其基本精神是人道主義,是對人的尊嚴、人的品格的提升。
(二)以人倫道德教育為核心的課程內容
中國古代課程內容以人倫道德教育為核心,主要通過教材內容的選擇與國家政策的導向,確保道德教育內容在課程體系中的地位。
先秦時期,儒家在選擇課程內容時,把倫理道德教化的內容放在首位,希望通過道德修養,達到完善的道德境界,這是治理好國家的基礎;當一個人完成了道德修養,成為君子后,就應積極入仕,成就“既仁且圣”的偉業。這種“學而優則仕”的課程價值取向使儒學在課程知識的選擇上重視治國策略和道德倫理。
其后,秦王朝“以吏為師”的文教政策的實施,課程為政治服務的職能得到強化。從漢代開始,儒學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兩漢時期,統治者推崇儒學,多次召集群儒論《五經》,使讀經成為傳統官學教育的靈魂,使課程的道德教育觀念深入人心。西漢的課程設置,對古代課程內容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其后雖歷經王朝更替、時代變遷,但漢代課程內容的經學傳統大多得到延續,以人文社會知識為主的經學課程成為中國古代課程體系的一條主線。
在延續兩漢課程內容的基礎上,唐代統治者又把儒家思想倫理規范的《孝經》、《論語》作為課程的基本教材,進一步將道德教育制度化,并以之作為科舉取士的內容。至宋代,在“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統領下,儒學成為“帝道之綱”。中央政府對各級各類學校官學教材的編寫、印制與發行,均進行宏觀調控和指導,語文教材也以經學教材為主。明朝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經典在課程體系中的地位,從培養學生的德行情操著手,朱元璋還親自制定了監規,要求學生“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此實現思想改造的目的。
由是觀之,歷朝統治者都通過制定文教政策,規定課程內容,把社會倫理道德教育納入課程體系之中。
(三)課程評價體系對德行教育的強化
肇始于隋朝,確立于唐代的科舉考試,在中國課程史上歷經1300多年,對強化古代德行教化的內容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實行科舉考試制度后,考試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至《五經正義》頒行后,從唐到北宋的400多年間,一直是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
受科舉考試的影響,宋代官學的課程設置主要是經義和詩賦課程。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學校課程設置、內容安排、科舉考試的科目有所調整。北宋前期,官方指定9本經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南宋嘉定以后,隨著程朱理學在官學體系中地位的確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進而成為官方認定的經學教材。這個課程體系一直延續到元、明、清時期。元代科舉考試重視德行,崇尚經術,排斥浮華,以經學中的理學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清朝的八股文題目用《四書》、《五經》中的現成話,“代圣人立言”,有嚴格的寫作格式與寫作內容,八股的文風必須“清真雅正”,不能用詩賦式的華麗辭藻。至此,經書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自古以來的“文以載道”的“道”,成為政治與社會倫理道德的化身,成為課程評價的主要內容。德行成為人的類特性的第一要義。
(四)實現課程目標的途徑
既然入仕是課程知識的價值所在,而經學又是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所以,人們花費很大精力,對經學進行不厭其煩的詮釋、注疏、考據、考證。顯然,這種世世代代對窮經的不懈追求,既不是出于認知的需要,也不是經學本身的吸引力。孔子的“學而優則仕”道破了其中的奧秘。經學之所以值得人們窮其畢生精力去學習,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入仕的門徑。因此,從某種意義說,這種學習活動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求真的活動,而是作為一種“中介”而存在。這種入仕的“中介”是讓人投身其中的外在的激勵機制,而外在激勵機制的極大誘惑力又把其內化為個體的行為自覺。儒學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課程的顯學,主要是其以科舉入仕為目的的強烈的實踐性以及其化成民俗的顯性的教化思想。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課程體系的主線儒學課程,以培養人為課程的終極目標,內圣外王是其課程的價值追求,社會人倫道德教化是儒家課程內容的核心,課程評價體系進一步強化了德行教育,而向內用功的道德實踐是其實現課程目標的根本途徑和方法。
[1]黃維海.中國古代課程發展回顧[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
[2]靳健.我國古代語文課程的性質、特征及其教育功能[J].教育研究,2006(2).
[3]劉啟迪.課程文化:涵義、價值取向與建設策略[J].課程·教材·教法,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