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給我的愛
小徑稀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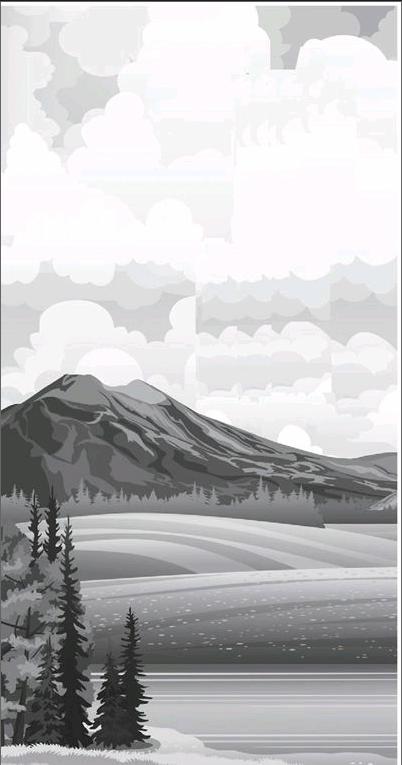
1
阿爸的電話來得不合時(shí)宜,我掛了,他又打,我只好接起來:“阿爸,我現(xiàn)在很忙,半個(gè)小時(shí)后給你打過去。”他一連說了3個(gè)好,我怕他不守信用,索性關(guān)了手機(jī)。
阿爸打電話從來都是這樣,不分時(shí)候想打就打,而且會一直打到你接為止。可是他說來說去,無非是那些無關(guān)緊要的生活瑣碎。
一忙起來就忘了開手機(jī)。下班回到家,阿爸正窩在家門口,倚著大包小包閉著眼睛。正值數(shù)九寒天,他卻坐在生冷的地板上,我喊了聲:“阿爸!”
阿爸“嗖”地站起來,一連打了幾個(gè)噴嚏。我一邊開門,一邊埋怨他:“怎么不給寶音打電話?”
他把鞋子在門墊上蹭了又蹭:“我覺得他挺忙,就沒說。”我倒吸了一口涼氣:“所以你等了一天?”“沒事兒!”阿爸笑了,“我在草原上放羊也是一待就一天。”
飯做好了,寶音把菜放在阿爸那邊,我需要伸長胳膊才能夠到。阿爸看到后,慌忙把菜又推到我跟前:“托婭,你多吃點(diǎn)兒。”
從我嫁給寶音第一天起,他就給我取了“托婭”這個(gè)蒙古名字。他說寶音在蒙語中是福氣的意思,托婭是霞光的意思,都是吉利的名字。
2
晚飯后,阿爸把帶來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掏出來,大到羊腿、風(fēng)干牛肉,小到粉條、芝麻。羊腿處理起來很麻煩,阿爸拿著刀麻利地把羊肉割下,把骨頭沿骨縫剁開,然后分裝在不同的食品袋里。廚房里,到處是肉屑油漬,我一邊收拾一邊叮囑阿爸:“下次來什么都別帶。你看,多麻煩。”阿爸拿著半尺長的煙鍋,沒說話。
阿爸這一住就是半個(gè)月。我每天下班都要匆匆忙忙地跑回去,給家里的兩個(gè)男人做飯,單位離家遠(yuǎn),天寒地凍的,我騎著自行車很辛苦。
臨走的那天晚上,阿爸塞給我一個(gè)布包:“托婭,買輛車吧,每天上下班騎自行車,太受罪。”
我捏了捏布包,笑著還給他。他不接,我執(zhí)意要給,他突然耷拉著腦袋:“有點(diǎn)兒少!”
看他神情落寞,我忙開玩笑地說:“等你攢夠了,一齊給我。”阿爸馬上神采奕奕地說:“好,我一定給你攢夠了。”說完,他哈哈大笑,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3
五一假期,我們回草原看阿爸。見到我們,阿爸笑得合不攏嘴:“我今天老聽見喜鵲叫,原來是你們要回來了。”
他到院子里轉(zhuǎn)了一圈,自言自語:“該吃些什么呢?”他去羊圈里看了一眼,又打量牛圈里那幾頭小家伙:“托婭嫌羊肉膻,我們殺頭牛吧。”那頭小牛正甩著尾巴吃草。我于心不忍,這牛再喂一年半載,能賣好幾千塊錢呢。我說:“我想吃菜。”說完,我又后悔。這方圓百里人煙稀少,又是青黃不接的五月,哪兒有什么新鮮蔬菜。
果然,寶音白了我一眼。阿爸搓著手,不知所措:“那該怎么辦?”寶音給我使了個(gè)眼色:“她愛吃干豆角!”我連連點(diǎn)頭。
最后,阿爸殺了兩只雞,吩咐額吉(媽媽)做了。他盤腿坐在炕上,點(diǎn)燃旱煙,遺憾地說:“你怎么不喜歡吃肉?凈便宜了寶音。”
我看了眼寶音,打趣地說:“是啊,他膘肥體壯,能賣個(gè)好價(jià)錢。”寶音作勢要打我,我笑著躲開了。
阿爸慈祥地看著我們打鬧,吸一口旱煙,愜意地笑了。
4
阿爸再來的時(shí)候,已是半年后。當(dāng)時(shí),我和寶音因瑣事爭吵,正在冷戰(zhàn),突然接到阿爸電話:“托婭,我來看你們了,可是下錯(cuò)站了……”我還在氣頭上,就說:“阿爸,我正忙,你給寶音打。”
下班回到家,家里沒有人。我急忙給阿爸打電話。電話撥出去,是寶音接的:“阿爸暈倒了!我們在醫(yī)院。”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打了車直奔醫(yī)院。
還好,阿爸只是輕微的腦出血,沒有生命危險(xiǎn),但是以后說話都不利索了。
出院后,他就在我家養(yǎng)病。一次,寶音隨手拿了一張碟給他看,不想正是我父親葬禮的那張。我跟寶音結(jié)婚不久,父親就去世了。記得當(dāng)時(shí),阿爸連夜趕來,在我父親靈前磕了3個(gè)頭,用蒙語念念叨叨,陪著我掉眼淚。
我想換碟,阿爸不肯。看著看著,他突然像個(gè)孩子似的號啕大哭。過了好一會兒,他止住哭聲,說:“托婭,我是想,多活幾年,替你爸疼你。可我現(xiàn)在……”
原來,當(dāng)年他在父親靈前念叨的是這個(gè)。我的眼淚像決堤的洪水,滿臉都是:“你會好的,阿爸。我要吃你帶的羊肉,你要給我掙錢買車。我永遠(yuǎn)都是你的托婭。”
阿爸緩緩轉(zhuǎn)過身,看著我,咧了咧嘴,笑了。
我想,阿爸給我的,是人世間最無私的愛。
(趙紅星摘自《淡定的人生不寂寞3》華文出版社)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