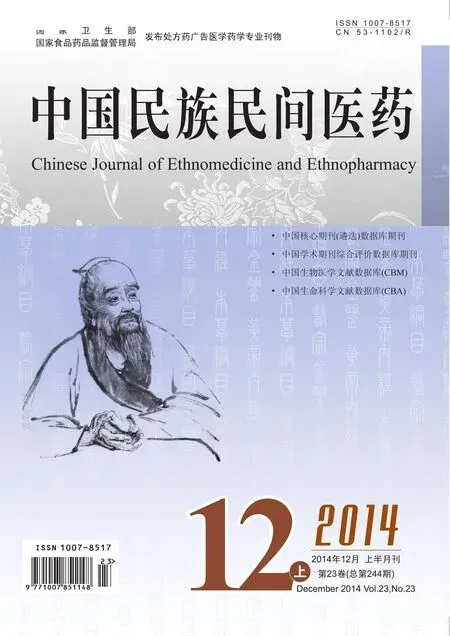從天啟《滇志》管窺明代云南醫藥文化
云南中醫學院基礎醫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從天啟《滇志》管窺明代云南醫藥文化
王慧峰王寅
云南中醫學院基礎醫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考察天啟《滇志》中相關醫藥內容可管窺明代云南醫藥文化。明代云南中醫發展以儒學教育的普及為文化背景,建立有與內地類似之醫事制度,除委派醫官與行政官員兼醫外,尚有謫戍或致仕官員行醫,本地醫學著作開始出現,儒醫的大量出現成為明代云南醫藥文化的重要特點,從一些特殊療法和特產藥物來看,中醫學在云南的發展具備了一定的本地特色。
天啟《滇志》;醫藥文化;儒醫;明代
地方志是記載自然、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著述,包涵內容廣泛,其中有關醫藥的內容更是研究醫藥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料。在現存明代云南志書中,內容最為豐富者當屬天啟《滇志》[1]。其纂修者劉文征,字懋學,昆明右衛人,生于嘉靖年間,萬歷間中癸未科進士,曾任新都縣令、刑部郎中、四川右參政、四川按察史、陜西右布政使等職,晚年以太仆卿之銜致仕,此后專心于撰修《滇志》,完稿于天啟年間,故后人稱為天啟《滇志》。由于在傳統文化中,醫學被視為雜流小技,所以在天啟《滇志》中所涉及的醫藥內容也比較有限,如對明代云南名醫蘭茂的記載僅涉及其文學詩賦,但即使如此,仍可透過有限的記載,管窺當時云南醫藥文化的發展狀況。
1 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中醫學得以在邊地發展的重要基礎。漢文化在云南的傳播歷史久遠,據《華陽國志》記載:“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萬歷《云南通志》更附以“授經教學,今云南有古漢學基。”《滇志》從之。然此后雖歷經數代,其發展依然緩慢,直至元代“設云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規模仍然有限。
及至明洪武十四年,明軍平定云南后,大力推行漢文化教育,規模逐步擴大,《滇志·地理志》記載:“(洪武)十五年春,城云南,建諸衙門及儒學。……永樂元年,設楚雄縣儒學,……五年,設鎮南州儒學,……十年,設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儒學,……(萬歷)十六年,設羅平州儒學……(天啟)二年,建彌勒、富民、陽宗三州縣儒學”。同時派遣學官,府學派教授、州學派學正、縣學派教諭或訓導。教化效果亦佳,如《滇志·地理志·風俗》言:“(尋甸府)置流建學以來,其俗漸改,人文可睹”,“(武定府)近建學校之后,舊習漸遷”。
漢文化以儒學為基礎并極具包容性的特點是使其成為中國主導文化的重要原因,在歷史上多次民族融合中,表現出兼收并蓄的特點,這也是使其能夠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中醫學是在漢文化背景下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它的傳播也必然依賴于漢文化的普及,因此漢文化的傳播發展為中醫學在云南邊地的落地開花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2 醫事與教育
明代云南已具備較為完善的醫事制度。明定云南后,承元制在云南設三司轄府、州、縣,并設各級官職,委派官員與土官并行。以云南府為例,據《滇志·建設志》載,包括醫官在內,各級官員有24人之多,這還不包括下轄州、縣的官員。其中醫官的構成與內地類似,即府、州、縣均設專職醫官,府設醫學正科,為九品,州設典科,縣設訓科,為從九品或不設品級,統計《滇志》所載,各地各級醫官職位計23個,官員則大多由政府委派入滇,這應該僅為當時云南醫官職位的一部分。在一些派不出醫官的地區,則由行政官員中兼通醫藥者兼任,如《滇志》所載的孔聘賢等人。
除委派之醫官外,還有謫戍或致仕的官員亦兼行醫,如《滇志》記載的劉寅、李良金、楊經、龍施、包文偉等。此外,平定云南時大量入滇并駐扎當地的軍隊,其中隨軍醫生多有定居于云南各地者,亦多以行醫為業。
除醫官制度外,各地所設養濟院亦與內地類似,養濟院以收養鰥寡孤獨貧病無依者為主要功能,院中有醫官擔任治療,物資由政府供給。《滇志》所載設有養濟院的地區有蒙化府、鶴慶府、姚安府、廣西府、尋甸府、武定府、景東府、元江府、麗江府、廣南府、順寧府、鎮沅府。其中有些養濟院亦有荒廢,如元江府,其原因可能與醫官、供給等問題有關。
醫學教育仍以父子相傳、師徒相傳為主,各級醫官亦是授徒之主體。本地醫學著作增多,對促進云南醫學的教育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據《滇志》所載主要醫學著述有劉寅《傷寒脈賦》、《標幽賦注》,龍施《心濟醫宗》,孔聘賢《可知》、《因病》,然而這些著作均未流傳至今,實為遺憾。明代云南醫著流傳至今者,當數楊林蘭茂所著之《滇南本草》、《醫門擥要》,但《滇志·藝文志》提及劉寅所著醫書《標幽賦注》,而關于蘭茂卻僅列其政史雜文,也是極令人疑惑之處。
3 儒士通醫
儒醫之名雖始于北宋,然自古不乏儒士通醫者,遠如建安之仲景、華佗、董奉等,皆能通解五經。明代云南由于其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使得因儒而通醫更成為一種必然。雖然明代云南業醫群體中醫官占重要比例,但從《滇志》內容來看,有較多文字記載的多為通儒兼醫的謫戍官員或本地知識分子。前者如劉寅,《滇志·官師志》所載“劉寅,山西崞縣人,洪武庚戌進士,……以罪戍金齒,貨藥訓蒙,所著有《武經直解》、《傷寒脈賦》、《標幽賦注》。”而本地知識分子所占比例更多,《滇志·人物志》載:“(云南府)李良金,字南夫,郡人,舉人……歸隱于北莊口,為小兒醫,搗諸藥各為一囊,視病之所投合而授之,每每奇中,所保赤子賴全活者無算。”“(大理府)包文偉,太和人,舉人……常制藥餌,作橋梁,以濟病者及涉者。”“(臨安府)孔聘賢,通海人,萬歷乙酉舉人……會歲大疫,念邊人或為庸醫所誤,乃著《可知》、《因病》二論,仍揭之通衢,每坐堂皇,邊人皆投牘言其病狀,隨方授之,所全活甚眾。”此外如楊經、龍施、賈惟孝等,皆有醫名。以醫理喻政者亦多有之,如《滇志·藝文志》卷二十三所收錄的“條地方事宜疏”,說明很多儒士官員雖不業醫,卻對醫道有一定的通解。
《滇志》所記載的有醫名的醫生,大多為飽學之士,很多曾中過科舉,擔任過各種官職,許多官員在任時即兼以行醫,一些在罷官或致仕后從事醫療活動,也有許多由科舉失意轉而業醫。這種情況的出現自然與明代云南漢文化教育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文化的普及為醫學的發展和醫生的培養提供了重要條件,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似乎儒士通醫已經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一種時尚,儒醫的大量出現是明代云南中醫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4 特色療法
《滇志》中還記載了許多與當地地理、風俗相關的特色療法,其中最多的是各種水的運用,志中記載具有治療疾病效果的泉、井11處。如《滇志·地理志》載:“(麗江府)苦泉有二,一出吳烈山澗內,一出州南刺沙村,其味皆微苦,飲之祛疾。”中醫學對各種水的功效認識早已有之,地方志中的記載雖不及本草著作之詳,但也足以反應當地醫藥發展狀況。這些對不同水的認識及使用,很多在當地已經成為共識或習俗,所以并非全為漢醫藥傳入及發展后所發現,而是當地人民在生產生活過程中所認識。其中比較有趣的是《滇志·地理志》所載:“(武定府)又有香水泉,春雨零而香發,居人祭而后汲,以蔗漿、酸角和飲之,去疾。”酸角是云南地區特產的一種藥食兩用作物,在當地各民族醫藥中被廣泛運用,由此也可看出明代云南中醫藥亦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顯現出中醫學與民族醫學融合的跡象。除具有療病作用的水以外,還記載了各種宜于烹茶、釀酒、造紙的水,以及具有毒性的水。
還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特色的療法。《滇志·地理志》載:“(鶴慶府)西南十里曰朝霞山,常見彩霞,山半有風洞,徑六寸,有風氣噓吸,夏至日,郡人群聚就洞口,以目薰之,可愈目青。”此可謂之“氣療”。“(臨安府)西北……十里有火焰山,有熱氣蒸爍,履之灼足,著苦葉輒焦,人臥其上,可以去疾。”可以謂之“熱療”。
此外,《滇志·地理志》中還記載了許多當地所出產的藥物種類,其中大多為中醫藥學中常用藥物,有一些為云南的道地藥材,也有一些以當地俗名稱之而難考的藥材,還有一些云南當地民族醫藥中所使用的特色藥材。
5 小結
明代云南醫藥文化的發展得益于漢文化教育的普及,一方面使得知識分子具備了掌握中醫學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也使得當地民眾在理論上和診療中更能夠接受中醫。從醫事制度與教育傳承來看與內地相近,而更多以行政官員身份從醫和以謫戍、致仕身份業醫者,儒士通醫成為明代云南醫藥文化的重要特點,科舉失意或官場失意的飽學之士,在寄情于山水之外,亦多留心于醫藥研究,通過解除民眾的病痛,以貫行儒家的仁愛思想。《滇志》中對于民族醫藥的發展狀況仍然存在一定偏見,如指其“病無醫藥,用夷巫禳之”,而從書中所載特色療法和特產藥物的地方特色來看,可能存在中醫學與民族醫學融合的跡象。
地方志是研究地方中醫藥文化的重要資料,僅從一部天啟《滇志》中獲得的資料仍是十分有限的,明代云南全省性方志除天啟《滇志》外,還有《云南圖經志書》、《滇略》等,同時還有許多州縣方志,通過對這些地方志的綜合研究,對明代云南醫藥文化的發展將會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發現。
[1]張秀華,呂天然,張繼文.云南方志的特征及價值[J].云南圖書館,2008,(4):71-74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十二五”重點培育學科云南中醫學院“中醫文化學”學科項目;云南中醫學院科學研究基金項目(XK201348)。
王慧峰(1979 -),男,山西晉城人,中醫學博士,講師,主要從事中醫藥文化研究。
R-092
A
1007-8517(2014)23-0004-02
2014.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