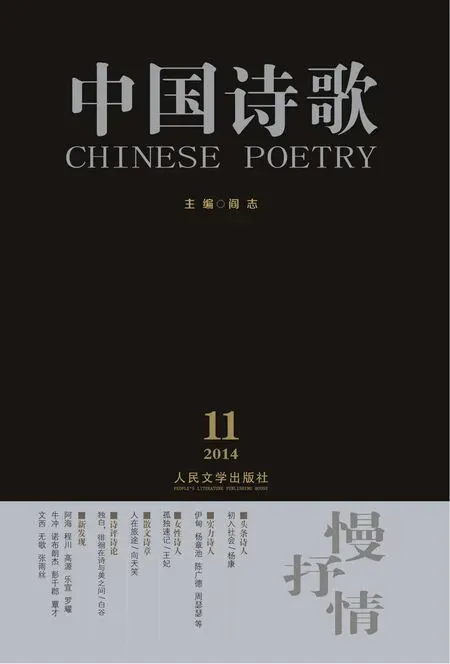孤獨速記組詩
王 妃
孤獨速記組詩
王 妃
乘車速記
前方到站,哪一站
都是周而復始的循環
封閉的圈子,空調機疲倦的喘息
各懷心事的乘客,渾濁的氣流
在身體里游走。
“前方到站……”到哪里?
我帶著無處安放的眼神,空空的心
為什么我總是這么容易心生厭倦?
在這里,只有擦肩而過的人。
前排橫座上的嬰兒,坐著坐著
就成了一位老人——
他瘦骨嶙峋,裸臂上的青筋暴出
一條河流已現枯竭之勢
但他有發亮的金表、銀戒,嗓音洪亮
顯然,他對生活知足,但還不忘指點江山
像我站在樟樹下指手畫腳的父親
前方到站。滾動的車輪
慢慢停下來。車身隨之晃動了幾下
老人木質的拐棍順勢倒過來
在我稍顯麻木的腿部輕輕一擊
早安,率水速記
有時候是一只,有時候是一群
水鳥們在率水里游弋、嬉戲
水紋展開,一幅幅素凈的扇面
此時的文峰橋,空與靜分立兩端
岸邊灌木抽出的新綠,和朝露一起顫動
垂釣者緊盯著浮標,與水鳥兩不相擾
第一中學早操前強勁的流行樂
很快由巨大的空曠稀釋成一層柔軟的薄紗
在江面上抖動……
天空疏朗。
東方的橙彩,和西方的晦暗
都被遠遠推開。
早安,率水
多么美!這面鏡子——
有潔凈的蒼穹
自由的翅膀,和幸福的波瀾
黃昏速記
螺螄山頂,鐘聲陡峭。
歸鳥與蟬鳴在松林中交雜
嘈雜的市聲矮下去
小到在山窩的一灣清泉里也找不見了
汽車、摩托車、行人,皆為螻蟻,在低處爬行
高端的別墅群,形如一排排整齊擺放的盒子
夕陽露出寬和之美
構筑樓群的僵硬線條
因為余暉的撫慰
而柔軟
孤獨速記
上帝偷走了他的睡眠
也偷走了他的親人
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把手中的小放音機音量開到最大
他想吵醒上帝
啞巴速記
他嘴里叼著四五根煙,腋下夾著三兩個礦泉水瓶子。
他在人群里爆發出怒吼——
單音節的,像隨心所欲的,又像是蓄謀已久的
有時候在你的身前,有時候在你的身后
仿佛這吼聲,是從你的身體里發出來的
當你驚愕,準備側身
他已經大搖大擺,快速穿過了你
他渾身發散著的氣味
是你熟悉的,卻拒絕接受的
睡前速記
人到中年
睡眠有時就是快車道
在一條暗黑的隧道里,隨時會遇見
年少的自己:上樹捉鳥,下河摸魚
摸蝦,摸螃蟹。當然,
也摸到死蛇
——一聲尖叫,鉆出隧道的
童年,在燈光下喘著粗氣
虛汗淋漓
我承認,在睡眠里,我是另一個
我。與愛過的人,或恨過的人
纏綿。戰爭。即使淚雨滂沱
都是快意恩仇,從不后悔
更多的夢,是一個人的戰爭
我是不死之神,每次行將死去之前
我會把自己叫醒
兩個世界,猶如兩頭惡獸
撕扯著我的黑白人生
“睡,比不睡更累”。
我擁著被子,困在睡與不睡之間
星 星
1
早晨五點半起床,第二天零點落燈
我的白天總比黑夜多。
我是母親、妻子、女兒、職員
我是女人。
我把這眾多的身份奉獻給了白晝
把沉重的肉身留給自己
把僅存的、可憐的兩片羽毛
帶進黑夜,獻給你
——星星
2
是暮色的圍裹,迫我尋找突圍的光:
是的,我看見了你,星星。
只有你,會穿過茉莉花的香氣
靠近我;而你的光
總在我夢囈之前,照見
我流淌著的口水和淚水
3
誰能搶走,或者遮蔽
你的光芒
陽光普照、霧霾,還是陰云密布?
我分明看見:在天河里
你托著幸福的水鳥,卻從不弄濕
它們的羽毛;而岸邊早春的
柳芽,只選擇在和風中端坐
不想讓光禿禿的桃枝
暗生慚愧之心
這就是你。
這只能是你。
即使整個人間陷入霓虹的心跳
我也能識別那惟一的光源
4
是的。
只有我,能感知你:
在你溫和而深邃的光里——
我愿你是我的父親,而我就是
那滾倒在紫花地丁、紫云英相伴的
童年里沉睡的女兒
我的天真、柔軟、脆弱和細膩
跟隨著云朵一起恍惚
還未醒來
我愿你是我的孩子,而我就是你依戀的
母親,耗盡我全部的骨血
喂養你。
你可以拿走我的一切
像嬰兒,吮空我
直到發出噼啪斷裂的脆響
5
假如,你僅僅是一顆堅硬的石頭
那我就是平行的另一顆:
蹲駐在河流、山澗、田野、公園的角落里
各自抱著冰團過夜。
我們奉著齏粉之心,決不用撞擊
來盜取彼此的火焰
如果,你是一顆行走的星星
我就是行走的另一顆
“我們都是奔向死亡的存在”
——像牛郎和織女
我們之間隔著迢迢銀河
我們都發著光。
這些光,是亮著的燈盞
人間的影子永遠不會走失
鏡子的背面
在鏡子的正面
我們是已婚者,是體面的
陌生人,雙眼渾濁
隱在鏡片之后
臉上的皺紋擠壓著最后的廉恥
雀斑是理智的化妝品
點綴了嬌羞
把鏡子的正面緊緊扣向桌面
把即將暴露的可能反過來
開口唱吧:“郎有情呀妹有意”
我們開始含情脈脈
看不見自己的人。
在鏡子的背面
你不是你,我也不是我
兩個替代品,像模特兒
裸身,站在櫥窗里
手挽著手
婚 姻
他無條件地忍受著我的夢囈
就像我無條件忍受他的鼾聲如雷
當我夢見一場盛大的婚禮
他在枕邊正露出甜蜜的一笑
我是幸福的新娘。但
幸福的新郎到底是誰?
參加婚禮的賓朋更像好奇的過客
我記得他們明明多次踏過我們的門檻
我的手就要被套上戒指了
現在,我就要幸福地一哭
他那么快地醒來終止了我的哭泣
就像我那么快就擦干眼淚起身為他準備早餐
你要在遠方等我
要不動聲色。任由人們的目光,
還停留在萬木的枯朽上
不能讓青草的嫩芽
那么快就鉆出來。
水面上還躺著浮冰,請告誡
那兩只激動的白鷗
要摁住喜悅的紅掌,輕輕推送——
不要暴露一池春水那細微的蕩漾。
蘇淺說,“最愛,總是要放在最遠。
弱水三千,都是想出來的。”
當溫潤的小南風一吹,我就會從
生活的更深處蘇醒過來
你要有足夠的耐心,在遠方等我
等我,從更遠的遠方
攜著朝露返回
器 物
好吧,現在,我們來說一說器物
你的,我的,或者不分你我的
器物。
我希望這樣的討論是平心靜氣的
說到價值,請原諒我的眼拙
作為一個主婦,我是經驗主義者
更是實用主義者:有用,還是無用
與好不好看沒有必然的關系
相對于把玩的古瓷,我更需要盛米的
大缸。請拿走那些價值連城的
把贗品留給我,我喜歡用這些器物的空
來填補我的生活。
至于你所強調的關系,我認為
一種器物在遇到另一種器物之前
它也僅僅是孤立的器物(譬如茶壺和茶杯)
它所不具備的可比性,又導致它的惟一性
也就是說,器物與器物之間的獨立
又恰恰埋下了它們彼此關聯的伏筆
(當茶壺和茶杯放在一起,該是
一個多么美妙的新的整體)
這難免又讓我想到了人——
男人,女人,他們各自的
以及相互珍視或漠視的
器物
釘 子
遇見一個人,就給自己蓋上一塊白布
愛上一個人,就給自己釘上一枚釘子
初戀是一枚釘子
(如今它早已銹死在肉里)
第二根釘子一直亮著
(掛著一塊紅布、一份契約)
不能再愛上別人了
盡管你的身上已經蓋上了密密麻麻的白布
那惟一的紅布,和惟一的契約
紅色,是多么醒目!
你終究還是要給自己釘上最后一枚釘子嗎?
想好了,就對著心臟,狠狠釘下去!
讓白布都染成紅布
讓契約化成一團軟泥……
讓兩枚發亮的釘子
掛著蒼白的你
這里是空的
滿塘的清水不見了。隨之不見的
是游弋的小魚、憨頭憨腦的鴨群、搗衣聲里
此起彼伏的歡笑
是裸身站在塘邊的大石塊上,往水里扎猛子的小
伙伴
是嬉笑、呵斥、呼號、求救
——攪亂一塘好水
而如今,這里空余下了
河蚌張開的兩翼。醉后扔掉的酒瓶。
洗衣漿裳的麻條石,早已面目全非
積塵裹著赭色,向前延伸著
像吐出的一截黯淡的舌頭
散亂的塑料袋兜著空氣,兀自翻滾著
塘底干裂。干涸的眼洞,不再有咸澀的淚水
好時光已走遠了
這里是空的。凜冽的風聲
一陣緊過一陣
李花謝了梨花白
風吹雨淋的委頓、蜂蝶的嬉戲與流連
還有所謂的愛花人,對著自己的一頓狂拍
這些已經發生的,它都默默承受了
接下來,它還要承受:
陣痛、喜悅、苦難、犧牲……
千朵萬朵,手里絞著彩巾的姑娘們
正鉚著勁兒往前擠
再湊近一點
能聽到春潮里汩汩涌動的心跳
它把白出讓給了梨花
喧鬧也留下來了。
現在,它正在默默承受
——凋零
它還來不及想太多
萬條垂下綠絲絳
雨水聚集。
走過的兩岸,陷進了多少雙鞋子
空氣中充斥著膨脹的腥氣
精靈們都醒了
梅蘭桃李杏……
她們的體內都住著妖。櫻桃小口
先吞掉扭結的肉身
再吞掉猙獰的面皮
然后,露出五顏六色的牙齒

柳樹頷首低眉,臨水而居
它的身體里住著神
誰經過它,便點化誰
它披頭散發,手執軟鞭
抽過來——
有時代替忠貞
有時代替悲憤
女性詩人
POETESS

王妃
WANGFEI
本名王佩玲,安徽桐城人,現居黃山。作品散見于《詩刊》、《人民文學》、《青年文學》、《詩選刊》、《詩歌月刊》、《中國詩歌》、《芳草》等。獲第二屆上官軍樂詩歌獎未名詩人獎等獎項。著有詩集《風吹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