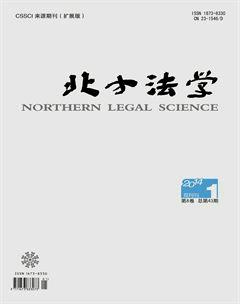中國刑事案件中的涉鑒上訪及其治理
摘 要:在中國刑事程序中,涉鑒上訪現象頻頻發生,且相對集中于死亡原因、損傷程度等法醫鑒定領域,它被當事人視為不滿公安、司法機關鑒定意見時最常見的訴訟外救濟措施和抗爭策略。然而,涉鑒上訪,尤其是重復上訪、越級上訪、多頭上訪等形式,卻顛覆了程序自治,使案件爭議久拖不決,司法權威一落千丈。涉鑒上訪存在的眾多問題在實踐中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目前卻亟須國家重點治理,其核心措施在于建立“過程導向信任”的鑒定機制,利用程序的開放性與主體的多方參與性,吸納與化解當事人對鑒定過程與結果的不滿;將當事人上訪作為例外的“底限救濟”權。
關鍵詞:刑事案件 司法鑒定 涉鑒上訪
中圖分類號:DF7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4)01-0091-10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上訪現象古已有之,從上古綿延到清末,并延續至今。①僅1949年后的上訪歷程,就經歷了幾番功能變更。②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轉型社會各種矛盾、官民沖突的進一步激發,以及民眾維權意識的增強,中國上訪潮一直居高不下,引起各界持續而強烈的關注。為此,學者們提出“依法抗爭”與“以法抗爭”等社會學解釋框架,③也開創出偏重制度建構與改革建議的法學研究路徑。④然而,上述對于中國上訪現象籠統、寬泛的理解、解釋,無法切中肯綮,也不利于對上訪問題的分類治理,唯有采取“小敘事—大視野”的研究范式,從微觀、具體的上訪現象入手,方能邁向細微與宏大、具體與抽象、理論分析與立法對策相結合的實踐法學。⑤
按照該研究范式,筆者將選擇刑事案件中的“涉鑒上訪”作為觀察樣本,原因在于,刑事程序中的涉鑒上訪頻頻發生,形勢嚴峻,乃至被視為中國當前上訪中最令人頭痛、最麻煩、最難以解決的問題。⑥而且,目前論者研究刑事案件中涉鑒上訪的成果寥寥,且多集中于對上訪原因與對策的探究。⑦特別是既有研究遮蔽了涉鑒上訪在中國法律、政治語境中的悖論:它雖被主流意識解讀為一種維權模式,⑧一度還被中央視為傾聽基層民聲、監督地方機關的政治渠道,但同時,過度的涉鑒上訪卻顛覆了程序自治,成為法治敵人,罔顧程序正義,⑨使社會沖突久拖不決,費時耗財,刑事司法權威聲名掃地;更糟糕的是,近年各種上訪潮水般涌向京城,有理、無理上訪混雜難辨,纏訪、鬧訪屢禁不絕,不僅祛除了上訪救濟與糾紛解決功能的正當性,⑩還催生出基層國家機關在上級考核壓力下的暴力截訪、非法拘禁等行為。
因此,筆者將從微觀層面揭示當事人或上訪人不滿官方鑒定意見而上訪的現象,深度闡釋其發生的內在邏輯,并根據上訪的分類治理、“各個擊破”的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國家亟須建立“過程導向信任”的鑒定程序機制,利用程序的開放性與當事人的多方參與性,吸納當事人不滿,減少并消除上訪。此外,鑒于當前司法機關信譽度偏低、完全實現訴訟的定紛止爭功能尚需時日,應在例外情況下,將上訪作為當事人訴訟外的一種“底限救濟”權。
二、當前涉鑒上訪的特征
筆者將結合(但不限于)眾多經典案例(如江蘇南通王逸案、湖北老河口市的高鶯鶯案、湖南湘潭的黃靜案、貴州甕安的李樹芬案、廣西南寧的黎朝陽案、河南周口的李勝利案、黑龍江嫩江的代義案等),同時,批判性地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參考各地披露的涉鑒上訪情況及其應對策略,與本文相關論斷進行印證或互戡。
(一)涉鑒類型
案例顯示,刑事程序中的涉鑒上訪,主要發生在法醫鑒定領域,且集中于傷情鑒定與死因鑒定案件,有時也見于(官方對嫌疑人或被告人進行)精神病鑒定的案件。這可從其他研究得到印證:一是河南省2004年1月至10月,到公安部涉嫌上訪的160例案件中,其中111例涉及法醫鑒定,占69.4%。二是筆者搜集到的目前關于刑案中因鑒定而上訪的研究論文,討論的幾乎都是傷情鑒定或死因鑒定。三是據研究者指出,從2005年5月18日至9月6日,山西省公安機關受理的群眾對刑事科學技術鑒定結論不服而提出申訴的信訪案件的統計數字來看,傷情鑒定51起,約占54%,死因鑒定43起,約占46%。四是2006年至2008年,河南省汝州市共發生因群眾不滿司法機關對刑事案件的處理而引發的赴省進京上訪案72件,其中輕傷害案32件,占上訪案件的44%,居各類案件之首,且在這些上訪案中,當事人都對輕傷鑒定結果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五是2005年,公安部在全國掀起聲勢浩大的“大接訪”活動,發現涉及法醫鑒定而上訪的案件占40%以上,據時任公安部辦公廳信訪辦主任歐振平透露,“大接訪”活動的前兩天,群眾反映較多的問題,就是對公安機關死因鑒定和傷情鑒定處理的不滿。
(二)上訪主體
刑事案件中上訪的主體因案件的鑒定類別而異。在死因鑒定中,上訪人為“疑似”被害人之親屬(父母、兄弟姊妹);而傷情鑒定與精神病鑒定案件(針對嫌疑人或被告人),上訪人則可能是當事人(本人或其親屬)一方,或雙方交錯進行。鑒于中國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高羈押率、超期羈押所表征出的“羈押常態原則” ,其不滿官方鑒定意見,一般都是親屬代為上訪。當然,上訪主體幾乎不會錯位上訪,即上訪人不會為對方利益而上訪。同時,上訪人往往會通過媒體、網絡發布案件信息,或聘請律師、鑒定專家尋求智力、法律與道義上的支持,這些措施強化了上訪的持續、反復進行。
(三)時空
當事人上訪持續時間少則一二年,多則十年。上訪既可能發生于偵查機關立案前,也可能發生在訴訟程序的各階段,即便在訴訟程序結束后、乃至當事人服刑完,也存在上訪現象。當然,就刑事鑒定意見的性質而言,因不服辦案部門死因鑒定意見的上訪,基本發生在立案前。原因在于,當被害人被疑似非正常死亡后,死因鑒定往往決定著偵查機關是否立案,以及有無必要追究相關人員刑事責任等核心問題;而傷情鑒定案件,當事人上訪從初查、偵查持續到審判階段,因為輕微傷、輕傷、重傷等不同的鑒定意見,不僅決定著偵查機關是否立案,也關系到被告人罪責之定罪量刑。
當事人初次上訪,上訪地點逐步升級,從地方上訪直至赴京上訪;再次上訪時,則傾向直接進京上訪。同樣,當事人上訪的部門,涉及從地方到中央的黨政機關、人大、政協、司法機關。當然,根據刑案的性質,上訪相對集中于政法系統。結合上述兩方面的特征,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等機關,成為常見上訪部門。
(四)手段
當事人多數情況下(尤其初次)采取合法手段上訪,如到上訪部門排隊、領取表格、等待通知,遞交上訪材料。但基于上訪渠道不暢、上訪被拒、上訪無故被拖、上訪效果欠佳等原因,有些當事人嘗試采取邊緣性、干擾性手段,如到上訪部門門前靜坐、下跪,到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公共場合打出標語、橫幅,或圍堵上訪部門。如在江蘇南通王逸傷害案中,被害人及其家屬曾先后到南通、南京、北京等地各級政府部門反映情況,并以請愿、下跪等多種形式表示強烈抗議。有的上訪人還采用暴力手段,如自傷、自殘、自焚、跳樓、自殺等。一些對刑事鑒定不滿的當事人或其家屬(如黃靜案),還利用新聞媒體、網絡等,發布消息、表達訴求、擴大影響。
(五)不滿指向
當事人不滿鑒定而上訪,涉及公安、司法機關各部門。當事人針對偵查機關(尤其公安機關)鑒定而上訪的頻率最高,其次是法院、檢察院,蓋因90%以上的刑事鑒定均由偵查機關在偵查或初查階段獨立啟動與完成,況且,偵查機關進行的鑒定,往往決定著是否立案,以及能否追究相關當事人罪責的輕重,因此不滿方在此階段頻繁上訪乃情理之中。至于審判階段的上訪,是因為鑒定意見將最終決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他必須放手一搏。但因法院相對客觀、中立,審判相對透明,以及律師更廣泛的參與,都使審判時鑒定意見更能被接受,上訪現象相對較少。而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基于其與偵查機關追訴犯罪立場一致,而較少啟動鑒定機制,故當事人幾乎不會針對其鑒定而上訪。
(六)上訪后果
雖然上訪在“侵權—維權”的話語維度中被賦予了“天然”正當性,確實為一些當事人洗刷了冤情,但它卻導致了如下負面后果:從個人而言,上訪為上訪人帶來難以承受的經濟、精神、時間成本,一些上訪家庭為此傾家蕩產、負債累累,且對于“職業”上訪者而言,長期的上訪已經讓其無法回歸故土,甚至為其帶來嚴重的心理與精神疾病。同時,上訪、特別是重復上訪為國家帶來怵目驚心的治理成本;更可怕的是,上訪惡化了本已脆弱不堪的司法信任,產生惡劣的“示范效應”,譬如“不信任(鑒定)—上訪—再不信任—再上訪”的惡性循環,還鼓勵出惡意上訪。
案例顯示,上訪雖被當事人頻繁運用,但卻未必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上訪雖表面上撕破了基層關系網,但實際上常常遭遇高層信訪部門將上訪人的要求簡單向基層批轉的命運(如高鶯鶯案)。當然,更多的情況是,案件當事人及家屬的上訪不是杳無音信,就是被告知耐心等待,這是上訪部門運用自如的“拖延”術(如黎朝陽案、曾仲生案)。原因在于,根據國家對上訪的處理原則,上訪問題最終需要在基層解決,事情出在哪里還得由哪里來解決;同時,鬧訪、纏訪、無理上訪與有理上訪難辨,上訪部門(尤其是中央)針對無以計數的片面信息無法有效甄別;當然部分原因還在于,上訪部門過多,彼此有相互推諉責任之嫌。
三、涉鑒上訪的成因分析
(一)宏觀背景:當事人與辦案部門互不信任
按照盧曼的觀點,信任是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它是個人在信息不對稱或現代社會高度分工情況下作出的合理抉擇,因此,信任可以產生合作、彼此認同,減少社會交流或運作的成本。涉鑒上訪的產生,部分基于當事人與辦案部門之間缺乏信任。
1.當事人不信任公安司法部門。雖然伯爾曼提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然而,中國此刻遭遇的真正問題,并非對法律的“信仰”危機,而是對法律的“信任”危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2009年8月10日至14日召開的全國法院大法官社會主義理念專題研討班上說: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信任危機早已投射在刑事司法中。論者實證研究顯示:3/4的民眾對公安、司法機關不大信任或非常不信任;公安司法部門的整體形象和威信堪憂。
缺乏信任的刑事司法在鑒定領域危機重重。譬如,重復鑒定盛行。據偵查機關和人民法院的粗略統計,在刑事案件中,同一事項鑒定兩次以上的占鑒定總數的60%以上,一些案件反復鑒定達到五六次,甚至更多。其次,刑事鑒定因鑒定爭議而備受質疑與指責。在黃靜案、代義案、李喬明等案中,辦案部門之間或辦案部門與當事人之間,對鑒定意見存在持續而強烈的爭議,他們互不買賬、針鋒相對。再次,部分鑒定機構與鑒定人的中立性、公正性岌岌可危,如死因鑒定、精神病鑒定中,他們過度考慮社會、政治因素,罔顧鑒定的科學性,或者故意錯鑒,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如2009年發生在內蒙古的鑒定腐敗窩案,涉案30余人,其中26人為司法干警、法醫及法官,使鑒定公信力嚴重受損。事實上,反復鑒定、對鑒定意見爭論不休、錯鑒此起彼伏等問題,早已撩起了科學鑒定的神圣面紗,使一度被譽為“證據之王”的鑒定意見,被戲謔為“是非之王”。
辦案部門信譽度的流失,通過典型案例被當事人感同身受,并在媒體的放大中,沉淀并塑造為民眾的深層認知結構,進而影響到涉案個體的行為選擇。事實上,因不被信任,在諸如涂遠高案、高鶯鶯案、戴海靜案、代義案等案件中,辦案部門的鑒定意見受到當事人家屬的強烈抵制。在這些案件中,當事人或其家屬不僅重復、越級上訪,還做出暴力搶尸、私設靈堂、游行示威、自殺式威脅、武力對抗等過激行為。缺乏信任,增加了官方鑒定意見被當事人接受的運作成本。在現代社會,國家權威或統治的生命力需借助民眾的自覺服從,“正如心理學研究現在已經證明的那樣,在確保遵從規則方面,其他因素如信任、公正、信實性和歸屬感等遠較強制力為重要”,而不信任的心理具有擴散性,以至于在一些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尸檢還未進行,而上訪卻已展開。最悲劇的是,互不信任還造成流血事件。
2.辦案部門不信任當事人。上訪具有“下情上達”的信息傳遞、監督糾錯和糾紛處理的功能。然而,當事人濫用上訪,卻逐漸消解了自身權利救濟的正當性,引起信譽危機。原因可能是,上訪一時成功的便利、高效,以及上訪案例的“示范”效應,使當事人視上訪為解決問題的終南捷徑,形成慣性依賴,動輒上訪。當然,上訪合法性根基或意識形態話語權的被解構,還在于實踐中無理上訪——謀利型上訪、精神病人的上訪、沒有合法或合理依據的偏執型上訪——對其正當性的沖擊。實踐中,一些法醫就認為,上訪案件中,部分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期望過高,或是對鑒定標準的片面理解,或是鑒定結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堅持認為鑒定結果有誤。一些學者還指出,有的當事人在長期上訪的經歷中通過反復訴說事件,逐漸形成思維定勢,堅信自己有冤情。日常生活中一旦捕捉到相關信息,就聞風而動,反復上訪,表現為精神上偏執,固執己見。當事人有時上訪的直接動因還在于得到更多的經濟賠償。如葉某某駕駛拖拉機到施工場地運沙,與施工場地看管員王某(男,70歲)發生爭執,爾后王摔倒當場死亡。經法醫學鑒定,死者王某某系冠心病猝死。王某家屬認為法醫鑒定有誤,要求重新鑒定,不斷上訪。半年后,經多次調解,王某家屬得到大筆賠款,也不再上訪了。后來其家屬講,他們也知道王某有心臟病,內心也認同法醫的鑒定結論,上訪是為了造輿論,給公安機關、給對方施加壓力,以便得到更多的賠款。
由于涉鑒上訪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無理上訪,勢必影響辦案部門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信任與看法。在辦案部門看來,當事人對鑒定意見不滿而上訪,除特殊情況外,多半是他們采取的一種抗爭姿態,或者是精神偏執所致,其目的是追求不正當利益,未必真有冤屈。辦案部門對當事人不信任而產生的這種理解偏向,具有連帶的負面后果:當事人合理且正當的訴訟內權利救濟——申請重新鑒定——也被無故拒絕,這促使當事人又回到上訪之路上。
(二)具體背景:當事人雙方錯綜復雜的關系
縱然現代法律程序試圖簡化或過濾當事人的社會特征,但法律規范本身卻無法創造一個獨立于外部環境的“隔音空間”。事實上,刑事程序中涉鑒上訪案件反而呈現出如下畫面:當事人之間復雜的社會關系,往往是決定著他們是否上訪的重要變量。案例顯示,因傷情鑒定而上訪的案件,當事人關系最為明確與特殊。他們大多發生于鄰里之間或相熟識或存在一定關系的人之中。當事人雙方在實施暴力前,就長年因各種雞毛蒜皮或其他瑣碎之事而積怨頗深,暴力傷害的最終發生,往往是糾紛沖突長期累積的總爆發。一些論者的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論斷,如在河南汝州,因輕傷害鑒定意見而上訪的案件大多發生于農村,在案件發生之前,被害人、犯罪嫌疑人雙方因耕地、宅基地、用水用地相鄰權等產生矛盾糾紛的占71%。雙方矛盾一直持續到案發。當事人雙方長年累月蓄積的恩怨,必將注入或延續于國家解決糾紛的刑事程序中。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傷害案件中,傷情鑒定意見至關重要,必為雙方當事人錙銖必較,辦案部門給出的任何鑒定意見均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不滿。
在因死因鑒定的上訪案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同樣復雜。研究發現,在這些案件中,被害人或與嫌疑人存在家庭、戀愛、朋友等關系,或被害人死于偵查機關的羈押場所或訊問期間,或被害人死于工作單位(如賓館、工廠)。在第一類案件中(如代義案與郭偉案),當事人可能存在家庭或戀愛糾紛,被害人死亡后,被害人的直系親屬不相信其為自殺,堅持要求國家懲辦兇手,由此而赴省進京上訪。在第二類案件中(如黎朝陽案),因為偵查機關不被信任,背負刑訊逼供的惡名,加之部分嫌疑人被虐待致死的曝光,使家屬根本不相信官方給出的自殺身亡的尸檢意見。而在第三類案件中(如高鶯鶯案),因涉案單位的性質(被外界視為涉黑涉黃場所)及其與地方政府千絲萬縷的關系,家屬對官方作出的死者系自殺的尸檢意見同樣不信任,再加上被害人之死過于蹊蹺、死前毫無征兆、身體傷痕無法合理解釋、辦案部門乃至地方政府處理失當等問題,更增添了當事人家屬的懷疑。何況,死亡案件非一般案件可比,而尸檢意見又決定著被懷疑之人是否能夠被繩之以法,因此,查明被害人死因就成為家屬責無旁貸、當仁不讓的責任。
當事人雙方之間事前存在恩怨或其他矛盾的案件,給死因與傷情鑒定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性,雙方的對立還可能延伸至法院判決后,范圍涉及兩個家庭乃至家族。由此看來,死因鑒定與傷情鑒定的刑事案件必須重視主體特征或其負荷的政治、社會與家庭因素,否則我們無法理解其上訪中被植入過多的情感,也難以理解當事人一再重復上訪、越級上訪的動力所在。
曾經發生在天臺縣的一例案件很好地闡釋了這一問題。天臺人陳啟忠死于與鄰居的一場混戰,事故發生后,天臺縣公安局認為陳因“腦基底動脈梗塞死亡”,且“與外傷無關”。隨后,法院的判決卻采用另一鑒定機構出具的“身體多種傷害共同參與導致死亡”的鑒定意見。判決后,雙方兩個家族持續對立:一邊是陳啟忠的親戚們在網絡上發帖,希望嚴懲兇手;另一邊是被告人家屬認為一審法院判決不公,開始上訴,并附上了長達數頁的支持者名單。參見李笛:《天臺陳啟忠死亡之“謎”》, 載《青年時報》2010年10月19日第A10版。
比如在第十一屆司法精神病學會議上,一位與會專家說:“(司法精神鑒定)考慮的社會因素太多,按下葫蘆起了瓢,沒完沒了。如果老這么偏,偏到哪里啊?有沒有原則?”參見柴會群:《司法之困:那些犯下命案的精神病人》,載《南方周末》2009年6月4日第A03版。
參見鄒明理:《重新鑒定增多原因與對策研究》,載《證據科學》2012年第1期,第6—7頁。
如在李樹芬案件中,在第二次鑒定過程中,參與前次鑒定的鑒定人沒有回避,且法醫的傾向性非常明顯。當法醫提取胃內物時,有家屬就問:“有敵敵畏嗎?”主持鑒定的法醫反問道:“敵敵畏有臭味,誰會喝?”沒有鑒定,僅憑氣味斷定,法醫焉能服人?蔡如鵬:《少女李樹芬三次尸檢內幕》,載《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5期,第32—34頁。
(三)直接原因:刑事鑒定問題重重而訴訟內救濟功能不足
中國刑事鑒定目前存在鑒定過程不可信、鑒定意見不可靠等諸多問題:如鑒定程序由辦案部門排他地決定是否需要啟動,單方指定或聘請鑒定人;鑒定過程過于封閉,排斥當事人或其家屬參與(甚至在尸檢案件中);鑒定人不回避。另外,部分法醫鑒定需要解決的問題疑難復雜,或鑒定技術欠缺、標準不科學(如傷情鑒定)。何況在有些案件中,鑒定人尸檢不全面、草率,并使檢材被銷毀、污染或變質;當然,關鍵原因還是部分鑒定人根據政治、社會需要鑒定,或故意錯鑒。關于上述問題,既往研究已取得共識,毋庸贅述。
而當前,當事人不滿相關鑒定的救濟主要是申請重新鑒定(包括補充鑒定),但重新鑒定救濟功能不足。首先是啟動難。不滿辦案部門鑒定意見,法律賦予當事人有權申請重新鑒定,但幾個問題限制了重新鑒定的開啟,如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重新鑒定的條件;是否允許重新鑒定,其決定權仍然操控在偵控機關與法院手中;針對辦案部門不允許重新鑒定的裁決,當事人并無救濟途徑;辦案部門亦無須對拒絕重新鑒定進行說理。其次,重新鑒定程序仍然問題重重。即便辦案部門許可重新鑒定,但當事人同樣不能參與鑒定機構與鑒定人的選擇,以及監督、見證鑒定過程在重新鑒定的鑒定過程中,一些問題依然存在。再次,重新鑒定可信度不高。初次鑒定意見即便是錯誤的,重新鑒定也難以糾正,如李勝利案、黎朝陽案,再次鑒定仍然維護、肯定初次鑒定意見。最后,重新鑒定存在高昂的鑒定費。雖然法律沒有規定,但重新鑒定的費用一般由申請者承擔,一些辦案部門以此為借口(甚至故意提高鑒定費),要求當事人預交鑒定費,否則不予重新鑒定。
四、上訪的邏輯與作為抗爭策略的上訪
(一)上訪的行動邏輯
選擇上訪,尤其赴京上訪,除部分上訪偏好者外,大部分都是當事人身處基層“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下的行動邏輯,是當事人在特定背景中的理性行為,不管事實層面是否合理。當事人(或其親屬)上訪,表面看來是為了推翻官方的先前鑒定意見,其實質,對于被害人方上訪而言,是希望嚴懲嫌疑人或被告人;對于被告人方上訪而言,則是期冀開脫、減輕罪責。當然,部分案件的當事人或其家屬是為了追求其他利益,如更多或更少的經濟賠償。故追問上訪發生、發展的事實邏輯,需要對當事人最終選擇上訪的過程進行簡要分析。
不滿官方鑒定意見,當事人或其家屬的本能反應就是向辦案機關表達不滿或異議,這是程序框架內的合理反映。他們希望通過否定或抗議的程度與頻率,促使辦案單位自行啟動再次鑒定來否定先前的鑒定意見。但與單純的否定、不滿相比,當事人更容易申請重新鑒定,這是法律規定的救濟權,而且目的更明確。申請重新鑒定,當事人一般需要提出理由或證據,就當前的趨勢而言,他們提出的依據,已經從最初對鑒定意見存有異議,擴展到鑒定人、鑒定機構違背了鑒定程序、鑒定規則、職業道德與紀律等問題,甚至深入到鑒定科學的可靠性等深層次問題。理由的變換,說明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的深思熟慮。盡管如此,純粹表達不滿或僅申請重新鑒定,都不必然引起辦案部門啟動重新鑒定機制,或即便官方啟動了重新鑒定,亦不必然改變鑒定意見或達到當事人的預期,此時,當事人可能選擇接受現實,或再次抗議與申請重新鑒定;但在一部分當事人非得討個“說法”的案件中,他們也可能采取進一步的措施:自行委托鑒定、通過網絡或媒體發布信息尋求社會支持、到辦案部門鬧事、自傷自殘式威脅、群體性暴力,或上訪。
然而,當事人自行鑒定獲得的鑒定意見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常常被辦案機構拒絕承認,它最大的功能是印證當事人懷疑,作為申請重新鑒定的輔助證據,但鑒定費用的不菲與鑒定檢材的難得,使其并不常見。而當事人采取的過激措施,如到辦案部門鬧事、游行示威、以死抗爭,或借助群體性事件對辦案部門施壓,卻難以把握合理限度,反而可能把事情搞砸,甚至會被認為影響社會安定、危及司法秩序,而被治安處罰或刑事處分,更何況,它們的影響局限在地方。至于尋求網絡與媒體支持,也要能夠吸引眼球,引起社會關注,形成聲勢浩大的輿論壓力,但在這個對不公已感覺麻木的時代,常規性的“故事”已無人問津。
綜上,選擇被法律、政治話語所承認,且幾千年歷史積淀而成的上訪,是當事人較為理性的策略。上訪雖然成功率不高,但往往“一步到位”,領導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問題。而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卻可能曠日持久,成本不菲,且效果不佳,甚至招致官方的報復性再次鑒定;有時,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取得的鑒定意見,即便證明了辦案部門的鑒定意見明顯有誤,也仍然不會被法院采信。而對上訪部門來說,尤其是領導的批示卻比申請重新鑒定更管用。上訪失敗,只是刺激當事人再次上訪的動因,在他們看來,失敗說明他們自身努力不夠。
當然,當事人選擇上訪,有時還因為其訴求無法被法律程序格式化,如無法提出新的線索,或重新鑒定已客觀不能。最典型的是辦案部門經過鑒定后,在現有的法律程序內,案件已經終結,但當事人的訴求卻有道義上的正當性,即從常識、常情與常理來說,當事人不滿官方鑒定意見是有理的,但其實際上已經喪失了重新鑒定的可能性。
而上訪所需要的不是法律框架內的細節舉證,而是一種小民百姓在面對青天大老爺時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將官(辦案機構)民(當事人)糾紛變成一種可以被言說、渲染和傳播的“苦”,這種“訴苦”的技術一向為中國民眾所熟悉。而且,它與暴力沖撞、圍堵辦案部門,或自傷自殘性地要挾辦案部門改變鑒定意見不同, 它在此處轉換成了碰觸而不危及穩定的賭注,以逼迫國家按照政治的邏輯——即穩定壓倒一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來思考和處理問題。
實踐中,當事人選擇上訪的時間是隨機的,各種策略手段也是綜合運用的,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實用哲學——有效就成。因此我們才看到以下情形:當事人不滿官方鑒定意見當即就上訪,勿需申請重新鑒定;當事人既申請重新鑒定,又不停上訪,還自行鑒定或大量發布網絡信息,各種策略交錯使用。
(二)作為抗爭策略的上訪
對當事人而言,上訪可被定位為一種策略行為:它呈現出當事人鮮明的抗爭姿態(態度),擺明對辦案部門強烈不滿,昭示地方“徇私枉法、顛倒黑白”,它是當事人為“權利救濟”而采取的一種實用戰略,盡管它常常帶有不純潔的動機。實際上,上訪亦確實對辦案部門產生了重要影響,哪怕是一種上訪的姿態,都在上級考核壓力下令基層難安,盡管其結果并非一定為當事人所預期。正是基于對他人上訪的耳聞目睹,或親身的參與體驗,上訪已由當事人從“自發”升格為“自覺”。
當事人選擇反復、越級上訪的抗爭姿態,其目的是讓上訪部門、包括社會民眾了解其冤屈,引起關注,以便給地方施壓,從而扭轉當事人與辦案部門的力量失衡。上訪給地方辦案部門的壓力,主要有兩種:一是當事人上訪成功,獲得上訪部門、主要是中央級信訪部門(特別是中央領導)的批文或批示后,地方部門一般會頂著壓力、快速解決問題。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超過60%的訪民都希望進京上訪,以引起中央領導重視,以便問題迎刃而解。二是上訪姿態(尤其是重復上訪、越級上訪)本身能給地方辦案部門施加壓力。直接向高層權力“訴怨”和“告狀”本身,有時恰恰是當事人要通過上訪的行為來對地方進行施壓性試探。他們相信,上訪的姿態會給基層政府和司法部門帶來壓力,讓他們感受到有可能因此而被置于高層“權力的眼睛”(福柯語)的監視與評判之下,以便期待地方作出相應讓步。故雖然大多數訪民都知道,通過上訪直接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到北京上訪,就能給地方施壓,而中央也確實采取了相應的應對之策,如要求將問題解決在基層,并對各省各地的信訪數量進行統計評比,并對解決信訪不力的省份提出批評。由此,在量化考核壓力下,各地紛紛派人到北京接訪,對訪民進行勸說,或者與訪民討價還價。
可見,當事人上訪,不僅反映程序救濟功能不足、官民信任失范,還是當事人理性的抗爭策略,它能夠借助上級尤其是中央,給基層辦案部門施壓,打破地方既定的利益格局。
五、刑事案件中涉鑒上訪的治理
多年來,在轉型中國的上訪潮中,刑事案件的涉鑒上訪異常醒目,且2005年司法鑒定體制改革,未能對此有所緩解,問題依然如故(2006年之后,涉鑒上訪同樣存在)。在制度層面,涉鑒上訪固然被塑造為當事人的法律政治權利,但它卻顛覆了程序自治,未能使訴訟成為社會糾紛的最終解決渠道,使部分案件被迫卷入依靠政治解決的途徑。隨之而來的后果是,人們削弱了對刑事程序定紛止爭功能的信任;而更惡劣的負面效應,卻因上訪救濟偶爾的“戲劇性”與“荒誕性”,鼓勵出無理上訪、纏訪的鬧劇,國家疲于應付。
就功能而言,上訪效果不佳。案件如潮水般涌入省城、京城,上級部門卻因時間、精力和資源限制,無法準確甄別信息真偽,也無足夠人力調查。故涉鑒上訪雖早已引起中央高層重視,但除少部分案件因中央信訪部門的批示,而發回地方重新處理外,大部分案件都只是或者事前要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或者采取量化考核措施,將赴京上訪推回地方。這一定程度上說,雖然上訪具有令中央觀察民情的政治功能,但過多的案件,也令其不堪重負。而且,因各種原因,即便最后上訪案在地方得到解決,其成本亦讓人望而生畏。個別案件尚且如此,那眾多的上訪案,地方辦案部門何以應對?如此繁瑣與超常的上訪治理,怎可能成為科層制辦案機構的日常運作模式?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辦案部門,譬如法院還采取定期院長、庭長、辦案法官共同接待涉鑒信訪,甚至為最大限度地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減少纏訪、鬧訪等社會不穩定因素,推出“院長下鄉接訪,法官攜卷下訪”的創新工作舉措,由群眾上訪反映問題轉變為院領導下訪解決問題,親自到當事人家中“家訪”,零距離辦理上訪案件。表面看來,上述部分地區推行的上訪化解方案似乎可行,且被作為典型被報道,顯示出國家治理上訪的靈活性與優越性,體現了司法為民的國家意識形態。
但毋庸置疑,地方相關部門解決涉鑒上訪成本高昂,且多數時候,需要當地黨政機關與司法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參與。故而此類實踐模式,只可能是超程序的“政治運動”的結果,它不可能成為一種常規的問題解決裝置,它僅是一種臨時的、機會型的政治治理術;它關注的是社會穩定,以及對上層考評的應付,它重視糾紛解決的社會功能——能干成事,即能讓當事人不再上訪,但忽略了規則之治——通過常規的程序普遍解決問題;它甚至附帶教唆效應,鼓勵當事人上訪,以追求不當利益。
面對上訪困境,論者提出改革上訪制度的建議之策。有人提出,應將散存各部門的信訪資源,整合于人大。還有人認為,在制定《信訪法》的同時,在全國人大建立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的“全國人大信訪監察委員會”,并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信訪局隸屬于這個委員會作為辦事機構接待信訪,使其成為中央信訪機構,上訪人員到省城上訪就等于到了首都。然而,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對此種疊床架屋式的制度改組持消極態度。“只要老百姓頭腦中的官本位意識、青天意識和政府萬能意識還存在,信訪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解決”。而目前大力推行的信訪責任追究制、領導干部親自接待制等措施,其實仍在強化上訪解決矛盾的能力,而忽視了刑事司法的定紛止爭功能,甚至刺激當事人偏好超訴訟的上訪渠道。因此,論者評論說,這些改革每自我強化一次,實際上都是往胡同里又走了一步,已經很難退出。
筆者認為,對于刑事案件中的涉鑒上訪必須采取分類治理,與其糾纏于上訪制度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如適當調整刑事鑒定程序,在訴訟框架內,吸納當事人對鑒定意見的不滿與爭議。如山東省檢察系統推行的“陽光鑒定”制度,在諸如死因鑒定程序中,邀請多方專家、當事人近親屬、律師參與或見證鑒定,保證了鑒定的科學性、準確性,同時打消了當事人對鑒定“官官相護”的疑慮。陜西省西安市檢察院自1990年試行刑事技術鑒定“臨場見證”制度以來,逐步形成一系列司法鑒定公開化制度——“鑒定公開”和“臨場見證法醫尸體解剖”。自2000年1月至2006 年7月,該院共受理案件2081起,全部實行公開鑒定,沒有一起上訴、纏訴。
由此看來,通過鑒定程序改革而實行事前預防,是治理當事人不滿鑒定而上訪的最有效措施。它確實在最易產生鑒定爭議的領域,賦予當事人(包括他們聘請的律師或專家)參與見證鑒定的權利,贏得了他們對辦案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的信任,即憑借過程公開導向結果信任;它針對的往往是被害人蹊蹺死亡、特別是死于看守所的特殊案件;它不僅在初次鑒定中使用,也在當事人不服而引發的重新鑒定中運用;它的成本,遠遠少于對當事人不服鑒定而上訪的治理成本。因此,實踐部門稱之為“陽光鑒定”的程序改革,可以說是當前通過刑事鑒定程序本身來預防涉鑒上訪的有效措施,它比簡單地借鑒國外制度更有效。它借助程序的自縛力與當事人充分參與從而必須接受程序的“作繭自縛”效果,而篩選出無理上訪。
當然,當前的“陽光鑒定”程序同樣存在修正的必要,諸如它僅僅在檢察機關運作,大多僅涉及死因不明的案件,當事人還較少參與鑒定人的選任,鑒定過程的公開程度還需細化等等,因此“陽光鑒定”程序的本土經驗需要進一步總結、提煉,并推廣于整個刑事程序階段(包括初查階段),運用容易引發爭議的更多鑒定領域,方能最大程度減少涉鑒上訪現象。
保留當事人適度的上訪權也是必要的妥協:因為在制度存在惰性的情況下,上訪可以刺激其改革。同時,針對地方辦案部門層出不窮的徇私枉法,上訪畢竟還是法律渠道內的較好解決方式,它至少避免了當事人更激進的私力救濟,如鬧事、暴力對抗、群體性事件。而且,針對刑事程序制度的剛性與辦案部門的冷漠,不滿鑒定意見的當事人還需要一個發泄怨恨與被人傾聽的愿望。何況,上千年歷史積淀而成的上訪心理結構,已經內化為民眾超穩定的潛意識,其被棄置也還需時間的淘洗。故而,鑒于中國建設法治社會還是一個漫長過程,當司法救濟導致實體正義失落時,當用盡司法救濟仍無法獲得權利保障時,當司法腐敗導致人們喪失對司法的信心時,我們仍然必須保留將信訪或上訪作為當事人的“底線救濟”的權利。
The Petition 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in Criminal Cases and Its Governance
CHEN Ru-chao
Abstrac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petitions 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ften occur in China, relatively focusing on cause of death, seriousness of injury and other matters in forensic fields. Such petitions are regarded as a non-litigation relief measure and resistance strategy when parties concerned dissatisfy with the appraisal opinions made by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and judicial organs. However, some petitions such as repeated petitions, rank-jumping petitions, and multiple petitions have done substantial damages to procedural autonomy, leading to prolonged resolution of controversies and a disastrous decline of judicial authority. Though petitions 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are rational to some extent in practice, they require a nationwide key governance to resolve current problems. And the core measure is to establish an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of “process oriented trust” and to rely on procedural openness and multiple parties participation so as to dissolve the parties dissatisfaction on appraisal process and results and to make the parties petition as an exception with the right to “bottom line relief”.
Key words:criminal cases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petition 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學2010年校級重點課題“重復鑒定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如超,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副教授,重慶高校物證技術工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法學博士。
① 關于中國古代的上訪現象,參見劉頂夫:《中國古代信訪源流考》,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107—109頁。
② 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上訪或信訪的發展階段分別是:大眾動員型、撥亂反正型、安定團結型等。參見應星:《作為特殊行政救濟的信訪救濟》,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第60—61頁。
③ 參見李連江、歐博文:《當代中國農民的依法抗爭》,載吳國光主編:《九七效應》,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版,轉引自吳毅:《“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與農民群體性利益的表達困境——對一起石場糾紛案例的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5期,第42—43頁;于建嶸:《當前農民維權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載《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55頁。
④ 參見前引②應星文;季衛東:《上訪潮與申訴制度的出路》,載《青年思想家》2005年第4期,第5—9頁。
⑤ 參見徐昕、盧榮榮:《暴力與不信任——轉型中國的醫療暴力研究:2000—2006》,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1期,第82—101頁。
⑥ 王進忠:《解讀公安涉法上訪(上)》,載《遼寧警專學報》2008年第2期,第48頁。
⑦ 例如王羚:《司法鑒定引發上訪的原因與對策》,載《中國司法鑒定》2003年第4期,第57—59頁;劉龍海:《輕傷害案件為什么易引發群眾上訪》,載《檢察日報》2009年11月1日第3版;劉永軍、翟志峰:《故意傷害案引發上訪多的原因分析》,載《中國信息報》2010年8月6日第7版。
⑧ 參見前引③于建嶸文。
⑨ 參見前引②應星文,第70頁。
⑩ 王亞新教授認為,糾紛解決功能是信訪/上訪制度的重要功能。參見王亞新:《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與民事審判的交織——以“涉法信訪”的處理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2期,第9—11頁。
關于“底限救濟”的概念,參見徐昕:《論私力救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頁。
王永等:《法醫臨床學鑒定中涉訪案件的分析》,載《中國法醫學會法醫臨床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版,第250頁。
如蘭樟彩:《41例命案上訪及原因分析》,載《刑事技術》2000年第3期,第42—43頁;前引⑦劉龍海文;前引⑦劉永軍、翟志峰文;劉瑛:《法醫鑒定引發上訪的原因及對策》,載《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25—27頁;姚桂法等:《人身傷亡案件上訪原因探討及對策》,載《中國法醫學會法醫臨床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版,第129—130頁。
趙芳芳等:《辦理刑事科學技術鑒定引發信訪案件的思考》,載《刑事技術》2005年第6期,第46頁。
前引⑦劉龍海文。
參見沈路濤:《公安部信訪辦:盡量不要越級上訪》,載《新華每日電訊》2005年5月21日第2版,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sina.com.cn/c/2005-05-21/09325948076s.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3年1月23日。
參見孫長永主編:《偵查程序與人權保障》,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6頁。
實踐中偶爾有之:妹妹“悲觀厭世”自縊身亡,妹夫被公安機關確定為兇手,死者的姐姐卻認為此案疑點重重,并歷經10余載艱難奔波,耗盡了 10 萬余元,寫下 150 多萬字申訴材料,上訪800余次,終于為妹夫昭雪。但這是小概率事件。參見蓄水:《當代“楊三姐”為“殺妹兇手”洗冤》,載《廉政瞭望》2010年第4期,第54—55頁。
參見《兩份傷情鑒定引發7次越級上訪》,載昭通在線:http://www.0870.ccoo.cn/news/local/770650.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2年10月14日。
前引⑥,第44—49頁。
參見汪建成:《中國刑事司法鑒定制度實證調研報告》,載《中外法學》2010年第2期,290—291頁。
早在2002年,一些研究者就指出,80%的上訪者具有一定的心理問題及精神異常。參見吳國娟:《司法鑒定中長期上訪者分析》,載《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02年第4期,第225頁。
[德]尼克拉斯·盧曼:《信任》,瞿鐵鵬、李強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30頁。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許章潤等:《法律信仰:中國語境及其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轉引自孫松濱:《執法者違法、法制如何維護——對司法的不信任是極其可怕的現象》,載《邊疆經濟與文化》2010年第4期,卷首語。
參見胡銘:《刑事司法的國民基礎之實證研究》,載《現代法學》2008年第3期,第39—45頁。
鄒明理:《合理控制重新鑒定和有效解決鑒定爭議措施探討》,載《中國司法》2008年第8期,第86頁。
據一些論者說,個別案件中司法鑒定意見居然可以達到33份之多。參見王松苗:《司法鑒定:成為“證據之王”尚需假以時日》,載《檢察日報》2005年12月14日第5版。
參見王和巖:《操縱司法鑒定:內蒙古窩案》,載《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2期,第86—91頁。
參見柴會群:《司法鑒定:從“證據之王”到“是非之王”》, 載《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第B8版。
前引,第17頁。
如2009年8月,某地公安機關抓獲一名販毒嫌疑人。審訊期間,該嫌疑人突然面色赤紅、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后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死者家屬懷疑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數十人圍堵政府部門。參見關仕新:《“陽光鑒定”:確保辦案質量提升司法公信力》,載《檢察日報》2011年3月3日第3版。
遼寧撫順小瓦村的一樁命案,上訪引發上訪者殺死截訪者。參見張千帆:《上訪的治理成本》,載《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23期,第83頁。
參見陳柏峰:《無理上訪與基層法制》,載《中外法學》2011年第2期,第227—247頁。
前引⑦王羚文,第58頁。
如2000年1月李某因對其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法醫鑒定結論不服引發上訪。四年來,李不接受法醫的科學鑒定,認為兒子是被其兒媳的相好所害。公安機關經過現場勘查及深入細致的走訪和調查,既沒有在現場發現任何可疑痕跡,也一直未發現李提供的所謂第三者。但李固執己見,以同一理由堅持上訪。參見前引劉瑛文,第25—27頁。
前引蘭樟彩文,第16頁。
參見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前引⑦劉龍海文。
如在李勝利死亡案件中,被害人家屬不信任檢察機關的三次鑒定,而申請第四次鑒定時,辦案機關要求被害人家屬拿3萬元錢,否則不給予鑒定,被害人家屬被迫放棄鑒定。參見杜濤欣、金明大:《河南周口“警察殺人”真相》,載《農業、農村、農民》(A版)2007年第6期,第22—24頁。
前引③吳毅文,第43頁。
參見紀念:《關于司法鑒定類信訪投訴的分析與思考》,載《中國司法鑒定》2009年第1期,第77—80頁。
如在浙江東陽的盧伯成案中,村民胡尚軍與村民盧伯成發生扭打,致盧口鼻出血,并仰面倒地昏迷。此案前后7年,歷經8次鑒定,直至盧因傷去世后,才被檢察院啟動立案監督程序。參見蔣少鋒、王嬰:《反復鑒定的表現形式、弊端、成因及解決問題的對策》,載宜昌法院網: http://yc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77,最后訪問時間:2012年10月14日。
參見王建勝:《我的當事人的鑒定歷程》,載《法律與生活》2008年第22期,第15—16頁。
參見前引③吳毅文,第37頁。
如山東省濟南市再生物資公司退休的商學珍,因一起感情糾紛被打傷。商學珍一直頭疼,大小便失禁,并伴有遺精現象。他到公安局報案后,公安機關經過法醫鑒定,認為構成輕微傷,屬于治安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但是多收了他60元鑒定費。為此,商學珍懷疑公安機關弄虛作假,隨后他向公安機關索取法醫鑒定結論書又遭拒絕。他選擇了上訪。參見王健:《北京“上訪村”調查》,載《民主與法制》2007年第9期,第10—12頁。
前引王健文。
參見侯猛:《最高法院訪民的心態及表達》,載《中外法學》2011年第3期,第648—659頁。
地方解決上訪所做的工作而花費的成本,遠遠超過訴訟。參見《南通通州督察上門20余次 上訪積案圓滿解決》,載公安警備督察局網:http://www.mps.gov.cn/n16/n1978875/n1978952/2794153.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2年10月14日;前引。
參見李輝:《會澤涉信零增長》, 載《云南日報》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
參見王健文,第10—12頁。
詹洪春:《“上訪族”探秘》,載《記者觀察》2003年第2期,第24頁。
石破:《進京上訪死結怎么樣化解》,載《南風窗》2010年第16期,第23頁。
參見孔繁平、盧金增:《陽光鑒定讓當事人口服心服》,載《檢察日報》2009年10月15日第1版。
張繼英、王瑩:《西安:刑事技術鑒定16年無誤》,載《檢察日報》2006年11月20日第2版。
“中國獲得成功的基本上都是司法實踐中自身自發的、民眾普遍滿意的改革,而那些直接引自西方的制度改革卻無一例外地遇到了挫折。”陳瑞華:《論法學研究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頁。
參見前引②應星文,第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