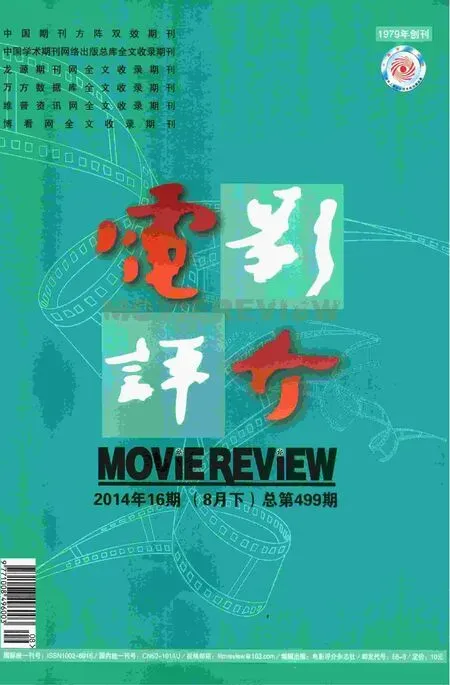青春題材電影的濫觴與主題呈現——談青春電影中夢想的缺席與情感訴求
龍明延
青春題材電影的濫觴與主題呈現
——談青春電影中夢想的缺席與情感訴求
龍明延

電影《十七歲的單車》劇照
一、擁抱與拒絕:擁抱之痛與拒絕之癢
都市繁華的背后,電影人懷揣著對于青春的理解,用影像來表達著自我構建的影像時空。無論是電影《十七歲的單車》里的現代的“駱駝祥子”,還是《青紅》、《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陽光燦爛的日子》、《青春派》、《同桌的你》里面雜糅的傷感歲月,抑或是都市繁華背后的青春解讀,都是對于夢想的無奈追逐,青春電影囊括了太多的主題,承受著過重的枷鎖。
青春電影不僅僅是消費市場繁榮后催化的結果,而事實上,青春電影一直是龐大的電影市場的參與者與建設者。原本簡短的青春電影已經在市場的繁榮與擴大化過程中變得主題的零散化,如果排除了觀影群體本身的年齡結構是在16歲到22之間,那么青春電影主題的擴大化顯然已經是創(chuàng)作者或者影視公司拍板人直接滲入的結果。無意從市場份額的多寡來分析為何青春電影的市場一片叫好聲中形成了一片創(chuàng)作氛圍,以及以此產生了青春電影四處開花卻少見碩果(不僅僅票房)的現實困境。
由此,造成了青春電影主題的泛濫與討好電影消費市場之間難以妥協(xié)的矛盾。直接的后果是對談青春片的失色與不斷的陷入創(chuàng)作陷阱。并非觀影群體獨愛青春片,對于觀影群體眾口難調的境遇,一味的迎合反而會失去電影市場本來的特色與規(guī)律,進而導致創(chuàng)作局面的舉足不前。一方面受到來自市場的不成熟所造就的盲目跟風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者本身的不夠沉淀的責任擔當。
二、繁榮背后:青春電影現象透視
近年來都市青春電影題材開畫后,各種以都市青年男女情感為線索、背景、主題等為陳說對象的題材開始直逼觀眾眼球。復制與抄襲的背后是大而不當的簡單建構與縫補,無疑暴露出眾多的都市青春電影的生存困境與過度泛濫的解讀青春。在面對好萊塢電影狂轟濫炸的間隙中,還能夠看到都市小清新青春片試水之作的努力與嘗試,這成就了電影市場空間難得的歡呼與喜悅,更認同了受眾對于當下優(yōu)質青春電影的渴望與急迫這一事實。
2011年11月11日當天,以失戀物語為特色的治愈型電影《失戀33天》席卷了3.4億票房,成為當年以小博大的黑馬。拋開電影的市場票房,從電影題材所觸及的青春話題——失戀。呈現當下都市里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以描繪女性黃小仙失戀中的33天的情感彌合為線索,呈現都市男女之間感情生活的現狀,這一線索原本是單調的,首開了“失戀物語”的形態(tài)來撲捉電影市場青春清新浪漫題材的空缺。只是簡單的低成本與大制作的博弈,抑或是與好萊塢電影大片的對抗,都市青春題材的窗口開始逐漸有觀眾愿意關注與接受(買票),由此產生了眾多的復制品的滋生與蔓延。營造了《失戀33天》孤軍奮戰(zhàn)抗擊好萊塢的票房高地戰(zhàn),以其獨到新穎的題材,病毒式的瘋狂傳播渠道,與觀眾(都市男女)產生了一個無縫對接。無論是治愈眼下都市男女的情感癥狀,還是彌補了都市男女情感路徑的空缺,都有意無意在2011年11月11日造就了一個電影奇觀——“光棍節(jié)”現象的青春都市題材的狂歡。
近年來電影市場多出現了以“懷舊”之名來書寫青春電影的節(jié)奏。大多電影冠以青春甚至懷舊的名義,企圖分享電影市場的一席之地。電影從青春開始,卻多半只是在敘述著與青春無關痛癢的故事。究竟誰是主要的敘事對象?青春,還是青春中的男男女女,或是只是青春中的一些噱頭,都似乎與青春無關緊要。那么,此時的青春,或者青春電影只不過是一些輔料,或者是企圖想拉攏觀影群體而創(chuàng)作出老少兼宜的跨年齡電影的手段了。
當下主要的觀影群體大致在14歲到27之間,這是比較契合青春電影的市場定位與價值追求的。以青春為主題的電影還有待市場觀眾的考驗與實際定位。然而,可預期的是,只要押中青春電影的故事情調,那么市場票房一定相當不錯。《小時代1》、《小時代2》、《小時代 3》三部電影再次刷寫一次“粉絲”電影的新浪潮;《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開創(chuàng)了單片青春主題的高票房紀錄;《后會無期》更是讓韓寒與郭敬明的票房爭奪戰(zhàn)打得有聲有色。國內青春電影沒有大多日本青春電影所呈現的寫實的“青春殘酷物語”,也沒有美國青春片在“性自由”、“暴力”等方面的青春緯度。青春片的創(chuàng)作群體大多是當下國內電影的新生代創(chuàng)作群體,他們對于青春乃至懷舊題材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以及與所處時代獨到的話語表達。更能夠充分的闡釋屬于同時代的青春故事與萌動的青春情結,這方面已經遠遠的拋開了第六代導演對于青春主題的另類表達。新生代導演更注重回歸現實生活的個體中來,開始關注自身,開始嘗試著以“成長”的禮儀式來審視著發(fā)生在周邊的一切。
三、青春電影主題的嬗變與歸因
(一)《青紅》:都市青春的缺席,混沌戀情的奢望;父輩的反思與期望,子一代的尷尬與不解
“早期的第六代電影多數為體制外制作,頑強地保留了青春反抗性、意識形態(tài)異端性和邊緣性色彩;雖然也不無時尚化的外觀,但其青春反抗性還是發(fā)自真誠的,更絕無喜劇性,從而成為轉型期中國青年文化生成的典型例證。”[1]脫離都市的話語表達,湮沒于鄉(xiāng)村知青的尋因價值與考究知青價值追尋,突出父與子這一代的情感的斷裂與癥結所在,探討父(老吳)子(青紅)之間難以名狀的對于鄉(xiāng)村與(上海)都市的回歸與第二故鄉(xiāng)的認同與質疑。青紅既非嚴格意義上的反叛者,也非現實生活的遵照者。這是歷史留給父的悲鳴,留給子(青紅、小根)的創(chuàng)傷,這是子一代(青紅、小珍、小根)無法理解父的苦痛與代際之間的隔閡。老吳作為知青支援三線貴州農村工廠,一心想回到上海,對十幾年知青生活的質疑。一臺被干擾的收音機是連接外界的獲取信息的唯一渠道。然而,當離開生活十幾年的“家”,遇上小根因為以“強奸罪”被槍決場景,而這一場景的被槍決者是缺席的,對兩代人的青春(父輩的青春,子女的青春)的捉摸不透,亦或是對于自我(老吳一代父輩)的質疑與反思。老吳寄托希望于下一代,脫離“歷史的悲鳴”從而走向新生,不希望歷史的痕跡留在兒子和女兒身上。老吳是敢于突破規(guī)則的一代,敢于勇敢地跳出困境的踐行者,但老吳卻因為方法過激而導致了女兒青紅遭到小根的“強奸”。如果說老吳一家搬家去上海壓過了小根被槍決的事實,那敢于逃出困境的老吳是徹底想與歷史的做的一次絕離,以企圖反思十幾年的歲月,只是這次行動給青紅和小根都留下了各自的殘酷青春歲月。
(二)《陽光燦爛的日子》:陽光般的少年,懵懂的戀想,缺夢的青春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闡述20世紀70年代,馬小軍整天閑著無事,打架,并偷偷進入別人家閑逛。看到了米蘭的照片,由此開始了荷爾蒙的純情青春期。“在中國電影的常規(guī)敘事中,愛情通常被表述為一種精神/心理現象,而非身體/生理現象,并且常常與政治、社會、道德、文化元素之間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愛情必須有附加值才能存在,或者說,愛情本身往往變成了附加值。”[2]電影中,馬小軍的愛情是奢侈的,愛情見證了馬小軍個人的成長狀態(tài)。馬小軍是沒有夢想的人,只是米蘭的形象改變了他,改變一個放蕩不羈的少年,一個只是知道閑逛、漫游、破壞的缺少管教的少年。“少年的成長需要特定的生死考驗甚至他人的生命獻祭,需要離棄母體和群體而獨自‘在路上’。”[3]然而,這個少年懂得戀情,垂青于米蘭,尤其正處于青春年少的他的愛戀,是情感懵懂的戀想讓馬小軍開始懂得。馬小軍知道懂得已經夠了。
(三)《十七歲的單車》:殘酷的青春,都市的弄影,現代的“祥子”
“中國電影人喜歡將北京描繪成一個美麗故鄉(xiāng),遠離現代文明污染,具有懷舊情調,而且能提供安全安逸的生活。”[4]第六代導演王小帥的作品《十七歲的單車》,表現了殘酷青春的同時,隱喻都市落寞的北京胡同文化里,生活在都市里的村莊中的邊緣人群,正是單車起到了連接著兩個青年的生活。小貴只有擁有了單車才有工作,小堅要靠單車才能和幾個朋友一起展示車技,最主要的是只有有了單車,才能和喜歡他的女孩瀟瀟“在一起”,小堅不知道其實瀟瀟希望擁有的不是單車,而是小堅這個人以及他的情感。但是,在小堅這個以男性身體來考慮問題的人來說,單車是他最基本的能力的體現,為此,他不惜和小貴為了一輛單車發(fā)生暴力沖突。小貴因為只有擁有了公司的單車,才能上班,才能送包裹。但是,車,沒有了,那就得失掉這份工作。小貴一向軟弱,但是,當有人企圖拿掉或者破壞他的單車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有力的回擊,以身體保護單車,以磚頭砸向破壞單車的人。“祥子是在20世紀初靠一輛租來的人力車沿著北京胡同辛苦討生活的‘經濟人’,他的愿望就是存夠錢買一輛自己的人力車。”[5]小貴扛著被毀壞的單車,行走在都市街道,沒人理解為何這個青年會有這么怪異的舉動。殘酷的青春,小貴、紅琴、小堅、瀟瀟,他們雖然生活在都市,卻只是都市里邊緣人群的縮影與個體展示。
“如果說,波德萊爾筆下的‘漫游者’可以看成是‘見證著現代性新狀況的知識分子形象’、‘現代性的公共場景的經驗的象征’。那么,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城市電影中,所謂‘漫游者’主要是并不是知識分子,而更多是一些處于社會底層、生活本身就充滿了流動性的人群,包括妓女、小偷、民工、自行車少年、同性戀者等等。”[6]對于小貴來說,北京是夢想中的城市,而非實現夢想的城市,看似繁華的都市背后,是游離于高樓大廈與古舊的胡同文化之間的落魄者形象。“現代城市,其空間形式,不是讓人確立家園感,而是不斷的毀掉家園感,不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fā)生體驗關系,而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fā)生錯置關系。”[7]小貴來到北京,他代表的僅僅是“現代的駱駝祥子”,更充當理解都市、理解胡同文化、理解胡同文化中的個體。然而,都市高樓大廈的背后卻是小貴落寞的扛著單車獨自穿梭在馬路中間。小貴依然延續(xù)并扮演著老舍在其著作《駱駝祥子》里面祥子的角色,這是再現,亦或是再建構,但卻依然逃不過命運的安排,命運不曾垂青于這個現代的“駱駝祥子”。都市繁華絲毫沒有悲憫過勤勞的小貴,公司的會計剝削他,公司的經理沒給予同情,小堅的朋友給予了暴力的打擊,唯獨只有小貴的朋友,那個小店里的大哥給予了巨大的認同與平等的關懷。
“只是在街道上,青少年初步確立了他們性方面的身份。在過去,脫離戀母階段的第一步是走上街道。但是,權威的監(jiān)督和大量的輿論制約這兩種力量的結合,照亮了黑暗頹萎的街道生活,產生了獨立的下層文化及其行為準則,把街道文化變?yōu)橐环N神話”[8],“當資本主義全球化再度浩浩蕩蕩勢不可擋,與此同時,其內在的危機的深化及話劇、能源危機的凸顯,已然現實了某種文明的盡頭(如果不說時候‘末日’)。當次之際,重新思考和確立文化的位置,以別樣文化開啟別樣的社會實踐空間,以別樣路徑去想象人類的未來,變得頗為急迫而重要。”[9]資本文化的席卷已經早已釀造了全球化過程中文化的沖突與妥協(xié)。《十七歲的單車》不斷展現北京古老的胡同文化,而這個文化的對比對象是都市高樓大廈,導演刻意營造了都市的繁華,以期展示胡同文化的在場性提醒大眾新世紀的到來,胡同文化即將消失的想象建構。熟悉的胡同景觀面臨著都市發(fā)展過程的無法回避的巨大災難——拆毀,小貴從鄉(xiāng)村來到都市夢想的破滅,小堅初開的戀情的終結,都已經昭示了一個令人失望的都市漫游者的命運。
(四)《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當現實照進青春,不朽青春只是記憶
他們(鄭薇、阮莞、朱小北、黎維娟、張開、許開陽、陳孝正)雖處青春年少,卻惟獨沒有對于夢想的強烈的、近乎取代一切的追逐與渴望,而是以“夢想的缺席”來取代了青春的悲情與疏離,取代了本該屬于他們的青春、陽光、溫暖。而“青春不朽”是她們共同發(fā)出的宣言。這就是他們的夢想,有著對青春強烈的憧憬與現實的理解,不需要過多的闡釋與奢望,只是簡單的讓青春“駐留”。這是向未來發(fā)出了幾聲孱弱的“吶喊”。他們生活在一個時空,但每個人都猶如行走在霧中,沒有退路,看不清方向,迷茫的生活在都市喧囂的一片寧靜的校園蔓延、游走。
(五)《觀音山》:漫游于都市與郊區(qū)之間,破碎的家,缺席的愛,孤寂的心,無目的的閑蕩
青春在此似乎預示著無法理解的混沌與撥不開的迷霧。三個青年共同的命運:家庭的破碎;高考的落榜;沒有家的歸屬。南風、丁波、肥皂分別指代著當下社會存在的多種家庭困境,無法逃離的現實造就了“閑游的一代”。他們沒有過激的反抗生活,只是在企圖逃離現狀而找到自我的地方。不斷的閑游,通過自我的“成長”來消磨著青春。常月琴(房主)選擇了跳崖,是想尋找兒子的世界,在孤獨的歲月中,她因為害怕,因為不安,因為記憶而消沉,觀音山讓她找到了一條通向尋找兒子的道路。
(六)《青春派》:成長的母題,失戀的物語,情感的力度
《青春派》里的男主角居然因為表白而復讀高三。當居然發(fā)現母親陷入離婚的困境中,母親詢問居然,如果離婚,是選擇跟父親還是母親?居然在回思自己的一個已經疏離的女神的“失望”來凝視隔壁房間的母親,這種凝視是伴隨著居然長大后的理解,一種自我認定的失望后的理解。圍繞著青春的校園里,電影企圖涵蓋高考、富二代、官二代、“拼爹”、家庭背景、戀愛(失戀——沒有開始的結束)、離婚(就算是假離婚)等等話題,雜糅并企圖呈現出在高考這個困擾千萬家庭的巨大命題。選擇在(2013年8月份)暑期檔上映,以“成長”的母題來敘說高考困境(既愛又恨)中的一群高中生,整合并迎合了剛剛從高考中脫離出來的高中生。“成長”的話題是雙向性的,一是父輩從不理解孩子到逐漸懂得孩子的內心想法;一是以居然為代表從不理解父輩到懂得溫暖,這種溫暖是建立在孩子的理解之上。青春的背后,是過多的反抗與追尋過程的痛楚,并非歌頌了青春的美好,而恰恰是在揭露青春的不安、躁動、無助、落寞等等以不完美的青春展示來期待著青春的美好的到來與價值訴求的啟迪。
四、逃脫的困境:青春難掩缺席的夢想
從“游戲的一代”指稱中,尋覓著青春寓言的種種蹤跡,青春的痕跡背后,眾多難以言表的青春歸望與個體展示中的內心訴求,青春的迷茫始終困擾著青春的激情,無語的困境難以傳達出一片屬于自我的天空,成長的命運式安排下,各自述說著本該擁有的青春話語。
(一)女性與男性身體的糾結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企圖與青春做一次別離,而這次別離所告別的,是那些與青春有關的人、事、以及時間,青春是用來懷舊的,青春終將別離,留下的只是記憶。四個女生,卻惟獨只有阮莞有著“不朽青春”,只是,阮莞不知道原來所謂不朽的只不過是生前有人愛著,死后還有人愛著。
《觀音山》以高考落榜后,南風(女)、丁波、肥皂三人整天閑游在鐵路的周圍,搭著免費的火車貨箱,來來回回穿梭。常月琴(房主)陷入失去兒子的痛苦中,當三人到來后,她的生活因此而改變,幾個青年以自己生活方式改變了她。當她縱身跳下懸崖的那刻,常月琴得到了解脫。但是,對于三個青年人來說,他們接下來的青春又該如何度過?沒有夢想的青春,破碎的家庭又該用何種情調來縫補,社會的誘惑該做如何流向,情感的溫度似乎能夠治愈家庭留下以及帶給他們的傷疤,“漫游者”如何回歸本該屬于的青春歲月。讓三個孩子過早的體驗意味著漫漫長路的無休止。家庭的負面影響讓他們生活在缺少關愛的邊緣,沒有夢想,沒有關愛,游蕩,漫游在都市與郊區(qū)之間,無法逃離。
(二)青春寓言:夢想中的城市與實現夢想的城市
電影《十七歲的單車》中小貴來到北京,是想從農村的環(huán)境中解脫出來。他夢想已久的都市卻只是讓他充當了現代的“駱駝祥子”,單車充當了穿行于都市之間的最基本工具,更是讓小貴得到工作的最基本前提,在夢想中的城市工作,這是小貴愿意花費任何代價來保護單車的原因。小貴可能知道什么是駱駝,但是卻不知道“駱駝祥子”是什么。這是一個單一的命運安排,只能是公司(都市)選擇小貴,而小貴卻不能選擇公司(社會)。命運絲毫不垂青一個年紀尚處于青春期的小青年。對于保姆紅琴的觀望也只是都市生活的一個窺視點,卻絲毫沒有猜測出紅琴是誰,讓人捉摸不透的不只紅琴,而是都市巨大的改變。胡同與高樓大廈的隔望相對,一個古舊與現代化的二元對立本來就是矛盾現象的并置。
(三)暗流涌動的關懷困境與捉摸不透的成長命題
《青紅》中父親老吳以“回上海”為主要的目標,妄圖阻止女兒早戀,大學的指向和回歸上海始終作為第一念想。老吳的關懷是青紅無法理解的,也是造成青紅最終作為青春的犧牲的指涉。老吳只能以作為父親的責任來關懷下一代,這份關懷是建立在對十幾年知青經歷的反思與覺醒上。然而,得到子一代的理解,最終傷害了子一代。《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馬小軍始終處于缺少父輩關愛的一代,閑蕩在都市之間,米蘭的出現,代替了父輩對馬小軍的關懷,但這樣的關懷是馬小軍懵懂戀情的端倪中呈現的,這是文革后的集體記憶和個性反思,這份關懷是處于難以取舍的困境中,而這份困境來自于自我的放逐與同年人的集體經歷。《十七歲的單車》現代的“駱駝祥子”小貴,以自己的身體來保護單車,把單車當著戀人一般的維護,當單車被偷(小偷的缺席),小貴漫游在都市的街道,只為尋找自己的伴侶般的單車。無論是面對暴力,還是面對剝削,還是面對精神困境的紅琴,小貴所得到的關懷是來自小貴的朋友抑或老鄉(xiāng)——小賣部兄弟。他充當了小貴的指路人和談話者角色,但是注定了這份關懷只是出于大致同年人的問候與對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鄭薇、阮莞、朱小北都沒有得到父輩的關愛。鄭薇陷入感情困境,得到了來自“午夜情感節(jié)目”紫鵑的話語幫助;阮莞陷入困境得到了張開的實物(金錢)的幫助;朱小北陷入困境得到了她姐姐的幫助;陳孝正父親的早逝,母親嚴厲的管教,這是造就了他對于人生大樓經不起半點的誤差的原因。《青春派》中的居然從反叛母親,反叛老師,到開始認識到母親的關愛,最終呈現給老師的是——既愛又恨。成長的母題,孕育著親情、友情、戀情,然認同和理解是懂得關愛的最直接體現。《觀音山》缺失的情感,三個破碎但依然存在的家庭,情感的寄托是建立在房東常月琴身上,換句話說,常月琴擔當了三個青年的“母親”這一缺失的形象,三個青年暫時“治愈”了常月琴的心理創(chuàng)傷,盡管是以他們青年人的方式。然而常月琴在觀音山懂得自己尋找的意義。縱身跳下成全了自己。
結語
青春電影在關注以“成長”為母題的語境建構中,游離于訴說著青春或者與“缺夢的一代人”的探索。當下電影市場借名青春電影或許只是為了完成漫游都市文化嫁接的文化拼貼主義與時尚尋根的人文價值關懷,都有意無意在充當了電影市場不自覺的快餐消費。在青春的歲月里,無關市場的種種窠臼與枷鎖,即使是難以名狀的現實困境的巨大誘惑與借助青春的符號編碼來進行自我的拯救與心靈的洗滌,都難掩飾青春缺夢的尷尬與沉思。霧中行走必定是一路迷茫,即便只是幾聲宣言式的吶喊,也只是對青春的一次告慰與表白,這是一次關于青春的拒絕與擁抱,或許只是因為青春不朽。
[1][3]陳旭光.影像當代中國—藝術批評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80,274.
[2][6]陳曉云.電影城市:中國電影與城市文化(1990—2007年)[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98,34.
[4][5]張英進.多元中國電影與文化論集[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63,65.
[7]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28-129.
[8]羅賽塔·布魯克,奈杰爾·科茨.街道的形象[M]//盧杰,朱國勤,譯.羅崗,顧錚.視覺文化讀本.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94.
[9]戴錦華.光影之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93.
龍明延,男,貴州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影視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影視文化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