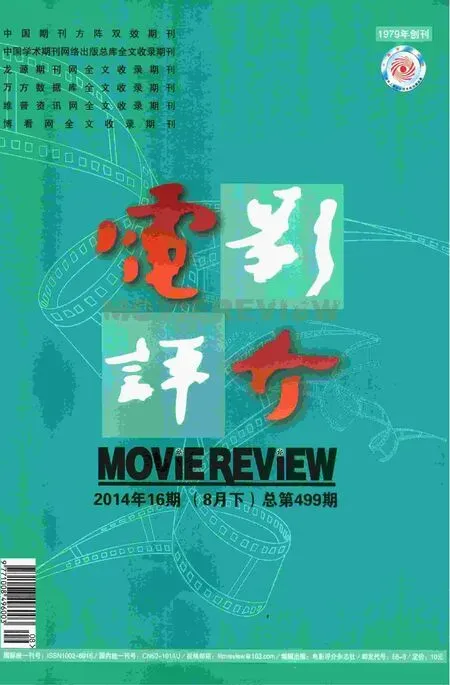論電影《歸來》對原著的解構主義改編
胡潔菲,王蘇君
論電影《歸來》對原著的解構主義改編
胡潔菲,王蘇君

電影《歸來》劇照
2014年由張藝謀執導的文藝大片《歸來》一經上映,就廣受好評,在商業價值和藝術表現上做到了雙贏。究其背后原因,優秀的小說原著和卓越的改編技巧無疑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張藝謀在文學改編上不僅能夠不忠實于原著的人物構成、故事情節、敘事線索等故事框架,更多地還能不忠實于原著的風格和靈魂,完成了從文字藝術到影像藝術的完美轉換,從而使電影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歸來》這部電影就是其優秀的典型代表。
對比電影《歸來》和原著小說《陸犯焉識》[1],發現電影對小說的刪改之大令人咋舌。原著作為一部長達三十萬字、占據四百多頁的長篇小說,將知識分子對人生的反思,對社會的關照,盡攬其中,而電影《歸來》則僅僅選取了主人公陸焉識逃出監獄和馮婉喻①電影《歸來》中將其改為“馮婉瑜”。*(小說為“喻”,電影為“瑜”)失憶的最后30頁情節進行拍攝,講述了與家人隔絕多年的勞改犯陸焉識在農場改造時偷跑回家及其平反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其親生女兒丹丹舉報父親,平反后回家妻子已經不認識任何人,陸焉識偽裝成陌生人照顧妻子馮婉瑜②小說中原名為“馮婉喻”。*等場景,旨在弘揚人性中的真善美,將知識分子精神救贖小說轉化成了充滿溫情的家庭倫理電影。
一、對原著復雜精神主題的消解
一部電影改編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眾的評價。接受美學認為,受眾必須參與文藝作品內在意義的構成,該作品只有得到受眾理解和接受,其最終價值才能夠實現。而受眾必須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人,其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必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發展,因而,在影視改編過程中如何既保留文本的歷史內涵又能為其注入新的時代精神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
受眾的審美經驗和期待視野對其理解作品有很大影響,這兩者綜合表現為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一般文化視野、藝術文化素養和文學能力層次四要素的有機結合。”[2]當前中國社會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影響深遠,對社會大眾而言,電影的符號學意義遠遠超出了其內在真實的思想意蘊。因而張藝謀在對小說改編的過程中,有意簡化其復雜的思想主題,著力表現愛情主題。小說《陸犯焉識》整個的結構主線是主人公陸焉識對于“自由”的求索和叩問,力求個體精神的獨立。此外,小說致力人性中自私、丑惡面的揭露,展現了文革給人帶來的精神創傷,敘述中無不充斥著對于人類生存意義的追尋和思考。電影所表現的故事則很簡單,即文革背景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聚散離合,旨在表現一對老夫妻對于愛情的忠貞和執著。它刪去了陸焉識在監獄中飽受饑餓、病痛的苦難和折磨,直接從逃離監獄展開敘事,將觀眾的目光聚焦在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上。
除此之外,由歷史積淀而產生的文化心理也決定了大眾的審美期待視野,表現為文藝作品若不符合觀眾期待視野,則會遭到排斥。自古以來,“才子佳人”的原型就深深根植于中國人民的心中,使得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雖歷經苦難但終須大團圓”的期待心理。在此基礎上,人們本質上追求的是一種心理、情感層面的刺激和沖動。張藝謀在這一點上也充分迎合了大眾心理,刪去了男女主人公如何相識,成為夫妻,在生活中日漸磨合的過程,直接呈現的是一對昔日琴瑟和諧的知識分子夫妻如何在苦難中掙扎相守的情景。小說中關于陸焉識婚外情的一段描寫,在電影中毫無體現,由此加強了陸焉識的人格無暇,這對于兩人愛情的圓滿度上又增添了有益的一筆。
電影人的主體精神在影視作品的塑造中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小說文本的意義留白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電影工作者的創作欲望,張藝謀本身作為一名有著強烈獨立意志的導演,歷來對于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十分徹底。電影和小說本身是有著各自的語言法則的,短短的一百多分鐘,想要將原著中所有的主旨意蘊、人物關系都表現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導演顯然也并不致力于將原著的內容面面俱到地展現出來。張藝謀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說道:“他有一個鋪墊,我們從結尾開始拍,就是‘帶戲上陣’,它潛移默化地發生作用”,體現了張藝謀獨特的藝術選擇。電影中的三個部分:男主人公潛逃回家、妻子失憶和丈夫陪伴,無一不展現了兩人之間的夫妻情深,尤其是電影開始呈現的陸焉識被抓捕的小高潮,感人至深。還有陸焉識為妻子讀信,修琴等一系列場景,深化了電影的愛情主題。
二、對原著人物形象的再造
(一)表現手法不同——邊緣人物的淡化
作為兩種不同的表現手法,文學文本旨在通過語言文字的組合傳達思想,電影則更多地通過聲畫組合敘述情節。從“講故事”這個層面來看,前者側重于通過故事發展的各個階段、細節傳達出一種精神和理念,后者則更多地注重“說故事”本身。受此影響,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說不受制于篇幅、時間、繁簡的限制,可以通過一系列細節和心理刻畫展現人物性格,而電影雖然有聲畫手段輔助,但在小說擅長的大量的心理活動等方面,還是相形見絀。另外,小說可以通過設置多個人物形象傳達多個聲音,每一個人物形象都能很立體,電影由于時長等因素的限制,刻畫人物形象相對平面化,并且只能專注數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
《陸犯焉識》除了精心塑造了陸焉識這樣一個主要人物形象,在其他人物形象上也是煞費苦心。馮婉喻作為一個有著雙重人格的人,其前期對于生活的隱忍和對于愛情的執著,失憶之后對于自由的狂熱,都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主體的迷失,成為小說主體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以鄧指為代表的徘徊在政治服從與理性判斷邊緣的官員形象,以梁葫蘆、劉國棟為代表的掙扎于時代悲劇之下渴望溫情又無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小人物形象,還有以陸子燁為代表的文革紅衛兵形象等,都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在電影中,這些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陸焉識”,被邊緣化了。即便是作為主要人物形象的馮婉瑜,性格也不再像小說中表現得那么豐富,張藝謀將馮婉瑜塑造成一個對愛情忠貞不二甚至不惜為此犯下政治錯誤的執著的女性。而其他人物形象則要么直接被刪除,要么被改編為無足輕重的人物形象。
刪去邊緣枝蔓人物,突出核心人物,電影在敘事上更加連貫,情節和構造上更加完整,因而其所講述的“故事”就顯得更加緊湊完善。這樣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擾,減輕了觀眾的觀影負擔,也適應了普通大眾的觀影習慣。
(二)戲以載道——核心人物的升華
小說和電影另一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更“文學”,后者更“市民”。小說的受眾面窄,因而它的創作也相對更加自由,作者大可以通過不同的文字組合盡情展現人物真實的性格,以傳達自己的價值和思考。而電影則不然,作為一種更加商業化的大眾媒介,無論是受眾的性別、年齡、職業,它的覆蓋面都遠遠高于小說,這就決定了電影人在表達自我價值的同時,必須兼顧到受眾的接受水平以及承擔社會教化的功能,也就是“戲以載道”。
作為第一主人公,陸焉識的形象十分值得關注。小說的作者嚴歌苓一方面將他塑造為一個出身貴族,崇尚自由,風流倜儻,精通四國語言的教授,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寫出了其人性之中卑劣的一面,突出了他在道德上的不完美。在監獄中,他無法接受別人的真誠以待,平反后回到家中,他也無法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永遠背著一個“老嫌犯”的帽子。由此可見,小說中的陸焉識是一個更加立體、豐滿的人物,他有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也有一個普通人在生存與死亡的邊緣所體現出來的道德異化和人性丑惡。
相比之下,電影中的陸焉識則更多地被“英雄化”了,在無形中塑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男主人公形象。他堅忍不拔,歷經折磨卻依然能夠堅守信念。他在文學和藝術上造詣極高,給妻子寫的信幾乎都是優美的散文和詩句,會彈鋼琴。另外,相對于小說中陸焉識平反后的唯唯諾諾,電影中的他則更加硬氣,充分展現了一家之主的風范。總之,無論是在專業學識上,還是人格修養上,電影中的陸焉識都可謂是近乎完美。
“現實的意識形態需要是某部影視作品產生的直接依據。”[3]電影將陸焉識的形象上升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的高度,這對于弘揚社會主旋律和正能量有著重要的意義。當代中國社會處于一個社會轉型期,各類政治經濟矛盾突出,文化差異尖銳,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之風盛行,人們的思想素質普遍不高,缺乏艱苦奮斗的精神。電影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有義務提供一系列正能量的文藝作品鼓舞人心。
三、由“歷史敘事”轉向“情感敘事”
《陸犯焉識》充分展現了嚴歌苓對于歷史敘事的偏愛,小說“將20世紀的中國百年歷史作為故事的發生背景”,“將知識分子陸焉識放置在中國20世紀嚴苛的政治環境中,將宏大的歷史敘事與傳奇的個人經歷熔于一爐”。[4]《陸犯焉識》首先是一部個人精神世界的成長史,其次是一部知識分子家庭的興衰史,更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政治發展史。嚴歌苓給小說設置了一個存在于小說內容中的“我”,即主人公的孫女,來敘述整個事件的發展,呈現的是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這部小說通過書寫歷史,嚴正地控訴了這一具有年代感和歷史感的政治運動,使小說更具有厚重感。
然而電影畢竟不同于小說,張藝謀在關于自己對電影的改編策略上曾說過:“鑒于電影是一次過的觀賞性藝術,它沒想負載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尋求與普通人最本質的情感溝通。生命的快樂與活力,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是作為生命主體的任何層次的人都可以感悟到的。”[5]所以《歸來》選取了大眾普遍有共鳴的情感描寫為主線。
事實上,電影中家庭中的夫妻情深也是深深打動了觀眾,引發了不小的“懷舊潮”。首先是電影拍攝上,選擇了中國當下最頂尖的演員來飾演主角,并且采用4K的高清鏡頭特寫演員表情、神態,多維度、深層次展現人物的情感變化。場景的選擇上,大量刪減那些有著傷痛記憶的歷史性描寫,將故事發生的年代、地點等虛化,主要通過讀信、修鋼琴、去火車站接人等幾個極具煽情效果的場景烘托男女主角的真摯愛情,使之成為電影的大賣點,尤其是電影虛構了“五號去接焉識”這一情節,更是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作為一個熱衷于色彩表現的大師級導演,張藝謀此次在《歸來》中,放棄使用絢麗和浮夸的色彩表現 ,而是以藍灰等冷色調為主打,烘托暮年相守的難能可貴。在歡樂的場景,比如丹丹為父母表演舞蹈時,又以鮮紅的緞帶和衣服奪人眼球,產生熱情、張揚的效果。這部電影的受眾不僅僅是有過文革經歷或體驗的人,因而導演需要講述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懂,且愿意看的故事,所以以“情感變化”作為敘事線索無疑是十分合適的。
四、對原著內在意蘊的解構與重建
(一)對“傷痕”的解構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凈化說”,指出悲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引起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之情,從而使人們飽受壓抑的情感得到一次集中的宣泄和釋放,因之心靈得以凈化。憐憫是由一個人遭受了不應該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恐懼則是由這個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作為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說,《陸犯焉識》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傷痕”這一話題。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這段歷史給人的創傷都是沉痛而不可磨滅的。嚴歌苓將筆觸延伸到人類最本能的親情上,對其進行解構,陸焉識偷跑回家時,小女兒在電話中告訴他不要再給家里添麻煩。平反后回到家中,兒子陸子燁也一直不肯接納父親,總在其頭上扣上逃犯的帽子。在這里,普遍意義上的親情已經被異化,完全不同于正常生活狀態下的家庭關系,極大程度地觸發了他們的感傷癖和哀憐癖。
然而與之相反,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批評悲劇是“壞藝術”,并同時指出了一味沉浸于感傷中的弊端,認為悲劇不僅使人動情傷感,而且使人在慟哭中失去理智,還使那些模仿各種人物角色的悲劇演員最終搞亂自己的心智,毀掉自己的性格。[6]倘若電影人一味的渲染悲情、苦情,為了感傷而感傷,則有消費悲劇的嫌疑,久而久之,也必然會讓人生厭。電影中盡管表現了陸焉識唯一的女兒為了能在舞蹈學校的演出中擔任主演而將自己父親舉報的劇情,卻在后期通過女兒的悔改,父親的寬容將父女親情重新建構起來。尤其是電影中女兒開口叫爸爸,過年父女一起吃餃子,父親將女兒接回家等一系列場景,都營造了溫馨的氛圍。小說描寫到馮婉喻為了挽回陸焉識的命,甘心做了方師傅的情婦,以至于后來盡管看到陸焉識偷跑回家也不愿意再見他。電影中卻將這一情節隱去,只暗示方師傅可能對馮婉瑜施加過某些傷害。由此可見,《歸來》對于“傷痕”點到即止,只留一小部分宣泄悲苦,情節銜接合理,節奏和程度把握得十分得當,恰是其高明之處。
(二)對“精神回歸”的建構
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必須在美學價值上有所突破。從之前的諸如《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電影看來,張藝謀極盡所能地展現了人性的丑惡和歷史的消沉,然而問題在于這一“反價值”的行為將真正良善、美好的東西也一并除掉了。《歸來》的成功之處在于他并沒有僅僅停留在自我的情感宣泄上,而是在“反價值”的同時樹立了自己正面的價值取向,重申了電影的美學精神。電影將原著名由《陸犯焉識》改為《歸來》,“犯”代表著禁錮、不幸和罪惡,而“歸來”則預示著溫暖、幸福和存在,這無形之中說明了現實的希望超越了過去的苦難,表明了活在當下的價值取向。小說中的陸焉識一輩子都在自由與不自由中苦苦掙扎,然而性格上的懦弱無能以及錯置的時空給他帶來一種存在上的虛無,使其最終沒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精神家園,因而他最后的結局是出走。電影則將大量精力投注于其平反后的生活上,描述陸焉識怎樣在身體自由的基礎上尋求精神領域的自由。對比小說,電影中他在被女兒接回家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照顧妻子,教育女兒,儼然一副家長的風范。這里的陸焉識是有著強烈的自我意志和獨立精神的,他明確知道自己在回歸之后應該以一副怎樣的姿態存在,因而更多地關注當下的希望,而選擇忘卻過去的傷痕。電影以陸焉識和馮婉瑜在風雪中佇立結尾,借主人公發聲,表明了對于生活的堅守和執著的價值取向,使精神得以回歸。
結語
《歸來》帶給我們的是超越苦難和創傷的溫暖,它表現了知識分子對于一個時代的寬容。正如陸焉識給妻子的信中所寫:“當我們看到小馬駒掙扎著站在滿是黃花的大地上的時候,我們感覺,春天真的來了。”春天,在這里無疑是光明未來的象征。總的來看,從小說到電影,除了由于藝術表達手段不同而造成差異之外,政治、商業因素,受眾偏好以及導演的審美取向等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當然,無論這兩者在藝術成就、商業價值或者社會影響上達到了怎樣的水平,都凝結著文藝工作者對于藝術的不同理解,都應當被尊重。
[1]嚴歌苓.陸犯焉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朱立元.接受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35.
[3]史可揚.影視批評方法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58.
[4]張亞麗.政治與歷史夾縫中的人性悲歌——關于嚴歌苓長篇新作《陸犯焉識》[N].文藝報,2011-12-07.
[5]班玉冰.張藝謀電影改編的主題策略[J].東南傳播,2006(11).
[6]王柯平.悲劇凈化說的淵源與反思[J].哲學研究,2012(5).
胡潔菲,女,安徽宣城人,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對外漢語專業學生;
王蘇君,女,浙江寧波人,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和文藝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