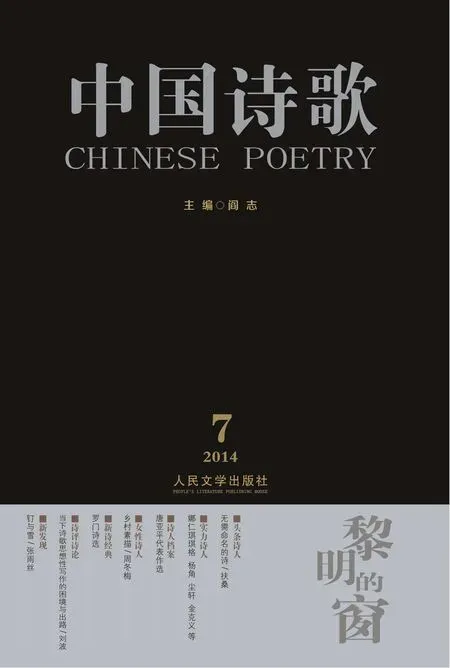女性的詩(shī)學(xué)
——唐亞平論
□張建建
女性的詩(shī)學(xué)——唐亞平論
□張建建
當(dāng)我準(zhǔn)備來(lái)談?wù)撎苼喥降脑?shī)歌時(shí),我意識(shí)到我就要談?wù)摰氖且环N已經(jīng)展開(kāi)在其詩(shī)章之中的“女性的詩(shī)學(xué)”。從唐亞平的詩(shī)篇來(lái)言說(shuō)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不是因?yàn)槲覀円呀?jīng)有了一個(gè)關(guān)于“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理念框架,然后再來(lái)尋章摘句為這個(gè)理念作例證,而是因?yàn)檫@樣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之理念,將從唐亞平的詩(shī)篇之中“涌現(xiàn)出來(lái)”。
這既是對(duì)其詩(shī)篇所作之領(lǐng)悟,亦是我們準(zhǔn)備談?wù)撘环N詩(shī)學(xué)時(shí)的謙遜態(tài)度。在我看來(lái),詩(shī)學(xué)的理念架構(gòu)在一切詩(shī)性言說(shuō)之上,如果說(shuō)理性的建立從物開(kāi)始,那么詩(shī)學(xué)的建立則從詩(shī)開(kāi)始,詩(shī)人的言說(shuō)呈現(xiàn)出一個(gè)詩(shī)意世界,詩(shī)學(xué)則是對(duì)于這個(gè)詩(shī)意世界的言說(shuō),在這個(gè)意義上,詩(shī)人的詩(shī)篇對(duì)于一種詩(shī)學(xué)而言,則是“無(wú)仿本的”(德里達(dá)語(yǔ))詩(shī)學(xué),也就是說(shuō),詩(shī)篇本身即開(kāi)展為一種詩(shī)學(xué),它是不能被一種詩(shī)學(xué)的成規(guī)所敘述的,也是不能夠被任何一種詩(shī)學(xué)之外的言說(shuō)(如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所敘述的。在“詩(shī)”的面前,任何“思想”都是蒼白無(wú)力的。在另外一方面,即詩(shī)人詩(shī)意地呈現(xiàn)世界這一方面,詩(shī)意世界的建立亦是詩(shī)人的詩(shī)學(xué)理性的建立,一詩(shī)篇即是一種詩(shī)學(xué),是詩(shī)人對(duì)于世界的詩(shī)性理念的展開(kāi)。詩(shī)的價(jià)值核心,即是詩(shī)人對(duì)于世界所進(jìn)行的詩(shī)學(xué)的價(jià)值評(píng)價(jià),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詩(shī)人的活動(dòng)即是一種詩(shī)學(xué)的活動(dòng),詩(shī)的意義即是詩(shī)人的一種詩(shī)學(xué)價(jià)值的展開(kāi),所謂“無(wú)仿本的”詩(shī)學(xué),正是指明了詩(shī)篇自身的詩(shī)學(xué)價(jià)值,指明詩(shī)篇自身必得是一種“無(wú)仿本的”詩(shī)學(xué)的展開(kāi)。當(dāng)我們準(zhǔn)備討論一個(gè)詩(shī)人之時(shí),我們必得討論這位詩(shī)人的詩(shī)學(xué)理念,正如卡勒所說(shuō):“如果詩(shī)歌能讀作對(duì)于詩(shī)本身問(wèn)題的思考或探索,那么,這種詩(shī)歌就是有意義的。”關(guān)于“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討論,我們的靈感來(lái)自于唐亞平的詩(shī)篇,我以為,唐亞平的詩(shī)篇已經(jīng)為有關(guān)“女性詩(shī)歌”的詩(shī)學(xué)作出了有效的概括,這是因?yàn)椋?dāng)我們展開(kāi)唐亞平的詩(shī)篇的理念架構(gòu)之時(shí),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已經(jīng)誦現(xiàn)出來(lái),這種詩(shī)學(xué)以其性別的經(jīng)驗(yàn)和詩(shī)性智慧啟動(dòng),為一種更為普遍的詩(shī)學(xué)提出了啟示,展開(kāi)了前景。
當(dāng)我們展示出這樣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之時(shí),也包涵了對(duì)于唐亞平的詩(shī)性經(jīng)驗(yàn)和詩(shī)性智慧的分析和評(píng)價(jià),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把“詩(shī)學(xué)”作為詩(shī)人之詩(shī)性智慧的一種評(píng)價(jià)的標(biāo)準(zhǔn),這亦是要強(qiáng)調(diào)指出的。
以下?lián)衿湟c(diǎn)展示唐亞平的“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理念架構(gòu)。
一切詩(shī)性的經(jīng)驗(yàn),首先便是對(duì)于存在的感悟的經(jīng)驗(yàn),“詩(shī)人的言辭不單只是一種賜給自由行動(dòng)的建立,并且又是堅(jiān)牢地把人存在建立在一個(gè)基礎(chǔ)上的建立”(《荷爾德林與詩(shī)之本質(zhì)》),海德格爾如此說(shuō)道。在此,唐亞平的詩(shī)學(xué)對(duì)于存在的感悟及其存在的經(jīng)驗(yàn)的樣態(tài)的展開(kāi),即是我們?cè)谶@里所說(shuō)的“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核心的內(nèi)容。依此我們亦可觀察到,唐亞平的詩(shī)篇所展開(kāi)出來(lái)的存在的感悟,皆是一種“懷腹”式的感悟,由此而建立起了她的詩(shī)學(xué)之“在一個(gè)基礎(chǔ)上的建立”的狀態(tài)。“懷腹”這個(gè)觀念,借自于里爾克的一首詩(shī),在這首詩(shī),里爾克說(shuō)道:“哦,小小生物的無(wú)上快樂(lè)/永遠(yuǎn)在懷腹中,生育它的懷腹/因?yàn)閼迅咕褪且磺兴?大地和我雙雙降雨,靜靜的,/四月的雨珠,飄灑進(jìn)我們的懷腹。/陽(yáng)剛男子氣度該自嘆不如!啊,誰(shuí)向你證明/我們感到的那孕育生命的一致和睦”。
如果說(shuō),里爾克反思性地揭示了世界存在的“懷腹”式的狀態(tài),建立起了他的關(guān)于存在的形而上學(xué),那么,唐亞平的詩(shī)學(xué)對(duì)于存在的“懷腹”式的感悟,則是直觀地,也就是詩(shī)意地呈現(xiàn)了出來(lái),其呈現(xiàn)方式亦是“懷腹”式的狀態(tài)。
“懷腹”是詩(shī)人詩(shī)意地孕護(hù)、孕藏、孕育世界的一種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中,“我抱著你的頭,太陽(yáng)和地球也/在我懷中,我的心變得熾熱凝重”(《田園曲》題辭,引自詩(shī)集《月亮的表情》),“像水擁抱雨/像雨擁抱水/彼此投入/讓兩個(gè)名字彼此誕生彼此鏤空/讓兩個(gè)名字川流不息”(《月亮的表情·愛(ài)是一場(chǎng)細(xì)雨》),在這種狀態(tài)中,“我是自己的憩園/一片孤獨(dú)的風(fēng)景”(《月亮的表情·孤獨(dú)的風(fēng)景》),這里面是山川河流,人物鳥(niǎo)獸,事物涌現(xiàn)如草木之生長(zhǎng),如海潮之涌動(dòng),唐亞平全部田園詩(shī)(主要收集在《荒蠻月亮》之中)的意象亦如此呈現(xiàn),如嬰兒駐足母腹一般,既沉穩(wěn),亦寧?kù)o。詩(shī)性的注視與詩(shī)意的展開(kāi),在詩(shī)人與世界之間形成了一個(gè)女性的“懷腹”式的關(guān)系,詩(shī)人主體與世界相互進(jìn)入,以詩(shī)意的方式,默默地推動(dòng)著世界的“自身開(kāi)放(如花的開(kāi)放)”(海德格爾語(yǔ)),由此展開(kāi)了一種主客間渾融不二的、無(wú)執(zhí)著的、未對(duì)象化的存在的境況,我這里稱其為“懷腹的詩(shī)學(xué)”的境況。
這是一個(gè)“無(wú)邪”的世界,一切人、物、事件,歡樂(lè)和痛苦,都展開(kāi)為物,人之世界亦被納入到世界的寂靜之中,是一“空言”世界的迷蒙景象:“田園上長(zhǎng)滿嫩芽和花蕾,從河上吹來(lái)的晚風(fēng)/也分不清天上和地下,我們也分不清田園和村落/我們風(fēng)一樣漫步田野,一切都是新綠”(《荒蠻月亮·我們的種子下了地》),這一切亦如唐亞平所言說(shuō):“我凝視的一切將化為空洞/水的空洞/光的空洞/石頭的空洞”(《月亮的表情·惆悵的風(fēng)景》)。這是一個(gè)具有一切“自在”的品質(zhì)的世界,這里面,沒(méi)有原因和結(jié)果,沒(méi)有任何的暗示和隱喻,亦沒(méi)有詩(shī)人,沒(méi)有敘述者,沒(méi)有反思,也就沒(méi)有任何詩(shī)人自我的表現(xiàn)。此時(shí)此刻,詩(shī)意世界塊然而立,大地向我們撲面而來(lái);此時(shí)此刻,存在的經(jīng)驗(yàn),展開(kāi)為澄明和廣大,“基礎(chǔ)”展開(kāi)為原初的原始性,“超人的莊嚴(yán)大起大落地經(jīng)受著原始的考驗(yàn)”(《月亮的表情·我信任夏天》);此時(shí)此刻,存在之詩(shī)亦深重地展開(kāi),展開(kāi)為“物物之生,物完成物之為物”(海德格爾語(yǔ))的廣大之詩(shī),其“生生不息”的廣大推動(dòng)之力,推動(dòng)著生命之孕育和孕護(hù)的存在之境況的展開(kāi)。唐亞平的詩(shī)意世界,在此成為生命存在的世界,因此建立起了唐亞平的“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基礎(chǔ)”。
“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歷史的人們?cè)谑澜缰械於似渚游弧保ê5赂駹枴端囆g(shù)作品的本源》),當(dāng)詩(shī)意作品被歸返于大地的本質(zhì)之時(shí),那就不僅僅是說(shuō),作品所承擔(dān)的那些題材內(nèi)容以及意象意境之類(lèi)被表現(xiàn)的對(duì)象必得具備大地的品質(zhì),它同時(shí)也是說(shuō),作品在注視或敘述大地的情形之時(shí),也就是大地性的。詩(shī)人的注視方式就是大地向人生成的秘密:“我赤裸著母性的溫柔/和波浪一起用胸膛擁抱岸”(《月亮的表情·五月的湖》),“岸就是波浪/永恒的岸就是永恒的波浪/岸是無(wú)始無(wú)終的宇宙/波浪是無(wú)始無(wú)終的宇宙/太陽(yáng)舉起一千只充血的手臂”(《月亮的表情·二月的湖》)。一種“擁抱的詩(shī)學(xué)”揭示了詩(shī)人與世界的深邃而平靜的關(guān)系,通過(guò)詩(shī)人的“擁抱”,大地與人得以共同展開(kāi)。唐亞平的詩(shī)學(xué)由此揭示了詩(shī)人投入存在的一種女性的方式——“擁抱”。
“懷腹”的狀態(tài)亦是一種“無(wú)我”的狀態(tài)。猶如女性之懷腹使嬰兒與母親渾融無(wú)間,女性的懷腹使得世界展開(kāi)為一“真純”的世界。“真純”即是“無(wú)為”,“天無(wú)為以為清,地?zé)o為以為寧,故兩無(wú)為相合,萬(wàn)物相化”(《老子》)。唐亞平的眾多詩(shī)篇,其敘述的氣氛多是平淡、收斂、寧?kù)o的方式,詩(shī)境中那些歡樂(lè)、傷心、難過(guò)、憂郁等等,都被籠罩在樸實(shí)沉靜的言說(shuō)之中,不論是言說(shuō)日常生活情景,還是言說(shuō)情緒、心境,抑或是存在之深思,人都會(huì)被融入到一種自然的解決之道。
在其田園詩(shī)中,她這樣來(lái)看人之沒(méi)入自然:“沒(méi)想到要躲藏,盡管知道該隱藏/讓人們看見(jiàn)吧,我們是到田野去”(《荒蠻月亮·沒(méi)想到要躲藏》),在這里,自然/田野,成為人的理由;在《意外的風(fēng)景》中,她如此來(lái)看待女人的自我意識(shí):“仰天而臥的女人/閑置的軀體一片荒地/在果實(shí)與果實(shí)之間/做荒涼的美夢(mèng)/天空這樣體貼我/我這樣體貼大地”(《月亮的表情》),在這里,“大地”成為女人的理由;在《二月的湖》里,她這樣表達(dá)人沒(méi)入自然的期望:“我來(lái)自山的高深處/我注定向最低矮的地方/尋求歸宿和平靜”(《月亮的表情》),在這里,“湖的瞳孔里沉淀著整個(gè)宇宙”,從而成為人的理由;在《黑色沙漠》里,她這樣言說(shuō)女人存在的神秘:“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流出黑夜使我無(wú)家可歸/在夜晚一切都會(huì)成為虛幻的影子/甚至皮膚血肉和骨骼都是黑色/天空和大海的影子成就了黑夜”(《黑夜序詩(shī)》),在這里,黑夜/神秘,成為人的理由,“所有色彩”皆“歸縮于黑夜”,這“虛幻的影子”。自然的解決之道,展開(kāi)在唐亞平全部詩(shī)篇之中,其坦白自在的心境,泯化了人世的一切緊張,從而將人的事物歸屬到大地之中,人與世界兩相化合,存在的景象亦展開(kāi)為“真純”,就像在女人的懷腹?fàn)顟B(tài)之下,嬰兒與母親同時(shí)呈現(xiàn)為懷腹時(shí)的真純,母親或詩(shī)人,亦成為“懷腹”時(shí)的“無(wú)我”的母親或詩(shī)人,所謂詩(shī)之“無(wú)我之境”,在此具備了存在的詩(shī)學(xué)的性質(zhì)。
“懷腹的詩(shī)學(xué)”也表示了一種“身體的形而上學(xué)”(梅洛·龐蒂語(yǔ))。就我所知,將身體作為詩(shī)意世界的主體,或者將身體作為存在的依據(jù),甚而將身體作為詩(shī)的書(shū)寫(xiě)來(lái)予以注視,在當(dāng)代詩(shī)人中非常少見(jiàn),同時(shí)將“身體”展開(kāi)在存在的領(lǐng)悟的多層面之中的詩(shī)篇,亦特別少見(jiàn)。可是這卻是唐亞平的詩(shī)篇的主要特色,亦是唐亞平的詩(shī)性經(jīng)驗(yàn)和性別經(jīng)驗(yàn)在其詩(shī)性智慧中展開(kāi)出來(lái)的主要特色。諸如下列詩(shī)句,在唐亞平的詩(shī)篇中比比皆是:“我身上陰云密布”(《斜依雨季》),“我身上的潮汐,為你興風(fēng)作浪/為你揮霍所有的時(shí)光”(《愛(ài)是一場(chǎng)細(xì)雨》),“我在身上設(shè)置天堂和地獄”(《眼下的情形》),“我身上的好風(fēng)水/被海涵養(yǎng)”(《老風(fēng)水》),等等。作為詩(shī)意言說(shuō)的“身體”,在唐亞平的詩(shī)性智慧燭照之下,成為“懷腹”式地召喚世界的一個(gè)方面:“懷腹”是將世界歸返于詩(shī)意世界,而“身體”則是將詩(shī)意世界歸返到世界之中去。詩(shī)學(xué)意義上的“身體”,既表明寫(xiě)詩(shī)的主體立場(chǎng),亦表明詩(shī)意方式與世界的親密,同時(shí)亦隱含著世界的“道成肉身”的存在景象。在此而言,詩(shī)人表達(dá)一個(gè)世界,也就是在“身體性”地進(jìn)入一個(gè)世界,“身體的形而上學(xué)”亦是一種主客圓融的存在的詩(shī)學(xué),正如梅洛·龐蒂所說(shuō)那樣:“由于身體在看和在活動(dòng),它便讓事物環(huán)繞在它周?chē)挛锍闪松眢w本身的一個(gè)附件或者一種延長(zhǎng),事物就鑲嵌在它的肌體上面,構(gòu)成它豐滿性的一部分”(《眼與心》)。
在唐亞平這里,雖然“我身上氣象萬(wàn)千”,但是,“惟我獨(dú)有的符號(hào)泄露天機(jī)”(《自白》),對(duì)于身體意象的詩(shī)意言說(shuō),在更深邃的意義上透露出了存在之詩(shī)的消息:由于以“身體”作為“基礎(chǔ)”,世界便成為詩(shī)人的世界。此時(shí),身體的經(jīng)驗(yàn),便是存在的經(jīng)驗(yàn),亦是詩(shī)性的經(jīng)驗(yàn),一切詩(shī)意表達(dá)的對(duì)象,如情緒、意識(shí)、意念、事物、事件等等,它們只是詩(shī)意本身的附屬物,在存在之詩(shī)面前,它們自然只是不能確指的,不能稱謂的,隨生隨滅之“物”,在詩(shī)的視野里,只能是詩(shī)之意義的派生物。以一種“身體的詩(shī)學(xué)”的立場(chǎng),唐亞平不僅全面地展開(kāi)其“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理念內(nèi)涵,而且亦表現(xiàn)出其對(duì)于存在的領(lǐng)悟的超邁的境界——一種“自己的肉體上的體驗(yàn)”(伍爾夫語(yǔ))的詩(shī)意展開(kāi),在存在領(lǐng)悟的境界上,有著比所謂“精神性的”詩(shī)意展開(kāi)和“意識(shí)性的”詩(shī)意展開(kāi)更超邁的氣度。
在唐亞平的詩(shī)學(xué)里,詩(shī)人寫(xiě)詩(shī),或者詩(shī)的語(yǔ)言,同樣被賦予了存在之詩(shī)的意義,亦同樣是以“身體”為“基礎(chǔ)”而一以貫之。她這樣寫(xiě)道:“一張紙漂進(jìn)河流/一張紙飄上天空/此時(shí)我亮出雙掌/十個(gè)指頭十個(gè)景致/我的皮膚是紙的皮膚/被山水書(shū)寫(xiě)”(《自白》),這首詩(shī),詩(shī)人解脫了寫(xiě)詩(shī)的意義:寫(xiě)詩(shī)是自己“身體性”的“亮出”——“十個(gè)指頭十個(gè)景致”,當(dāng)其“亮出”那“惟我獨(dú)有的符號(hào)”——即“身體性”,便說(shuō)明了這種詩(shī)意寫(xiě)作的一切秘密。在“身體性”的“基礎(chǔ)”之上,一切詩(shī)意的言說(shuō)皆是對(duì)于存在的“獻(xiàn)祭”:“我,身為祭壇”(《心境》),“我一身是名字的墓園/那最終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生所有的名字”(《一個(gè)名字的葬禮》),一切言說(shuō)皆是對(duì)于事物的“命名”,“彼此投入/讓兩個(gè)名字彼此誕生彼此鏤空/讓兩個(gè)名字川流不息”(《愛(ài)是一場(chǎng)細(xì)雨》),詩(shī)人已說(shuō)出的只是“名字”的“川流不息”,“就這樣——留下遺跡/被神廢棄”(《心境》),當(dāng)語(yǔ)言完成其獻(xiàn)祭,塊然而立的則是“身體”。
在唐亞平這里,詩(shī)語(yǔ)的寫(xiě)作,只能是存在的“泄露”,沒(méi)有“存在之外”的言說(shuō),尤其是沒(méi)有“命名”式的言說(shuō),寫(xiě)詩(shī)只有一項(xiàng)價(jià)值,便是與存在的“相遇”。寫(xiě)詩(shī)是一種“泄露”,在梅洛·龐蒂那里得到更多的強(qiáng)調(diào),他這樣說(shuō)道:“一個(gè)內(nèi)心的,或萌生在活的身體當(dāng)中的意義的這樣一種泄露,如我們將要看見(jiàn)的,延伸向整個(gè)可感覺(jué)的世界,而我們的目光,被身體本身的經(jīng)驗(yàn)所提醒,在所有其他‘對(duì)象’當(dāng)中,重新找到了表現(xiàn)的奇跡”。此處所謂“表現(xiàn)的奇跡”,是指明一切言說(shuō),皆是與存在的“相遇”,是通過(guò)存在的“泄露”而與存在境界一以貫通——不論詩(shī)人企求表現(xiàn)什么,它們都將是存在的“X”,是恒常不動(dòng)的世界的種種變相。唐亞平展開(kāi)這些“對(duì)象”,皆依循其詩(shī)學(xué)的理路而一以貫穿,如組詩(shī)《黑色沙漠》、《意外的風(fēng)景》、《月亮的表情》等詩(shī)篇,皆是其詩(shī)學(xué)的“表現(xiàn)的奇跡”的展開(kāi),是其一切“可感覺(jué)的世界”的存在性的展開(kāi)。這些“可感覺(jué)的世界”,唐亞平一如既往地予以了感官性的表述,如:“這蒙昧的天氣最容易引起狗的懷疑”(《黑色沼澤》),“是誰(shuí)懶洋洋地君臨又懶洋洋地離去/在破瓷碗的邊緣我沉思了一千個(gè)瞬間”(《黑色眼淚》),“這里到處是孕婦的面孔/蝴蝶斑躍躍欲飛/噩夢(mèng)的神秘充滿刺激/活著要痙攣一生”(《黑色石頭》)等等。這些表述指明其敘述的“身體性”的特征。另外,“身體”的某些狀態(tài),亦是展開(kāi)其“可感覺(jué)的世界”的重要方式,例如,“睡”與“慵懶”,不僅僅是某種情緒的表征,同時(shí)也是“身體”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被子在深夜發(fā)酵/不同的懶散同時(shí)膨脹/我身臨其境任酣睡表演死亡”(《死亡表演》)。
另外,如“觸摸”、“吊落”、“倦”、“軀體”、“撫摸”、“胖”、“懷孕”等等意念和意象,皆是其“身體性”經(jīng)驗(yàn)的詩(shī)意表達(dá)的“對(duì)象”,由此架構(gòu)起唐亞平詩(shī)篇中的一切“對(duì)象”的存在性的意義。在這些表達(dá)之中,風(fēng)景、自然、生活場(chǎng)景、意識(shí)、情緒,甚至“愛(ài)情”等等,更加富于“私人性”和“隱私性”,充分展現(xiàn)了如海德格爾所說(shuō)的“沉淪”.的樣態(tài)。“沉淪”這個(gè)樣態(tài),是從迷蒙浮向澄明的必由之路,是存在從世界的存在向人的存在降落的路徑,于是其中必定包含著存在的展開(kāi)的軌跡。其情其狀,正如唐亞平所寫(xiě)那樣:“洞穴之黑暗籠罩晝夜/蝙蝠成群盤(pán)旋于拱壁/翅膀煽動(dòng)陰森淫穢的魅力/女人在某一輝煌的瞬間/隱入失明的宇宙”(《黑色洞穴》)。在這里,“沉淪”不是存在的對(duì)立面,亦不是非存在,而是存在展開(kāi)的樣態(tài)。這些詩(shī)篇雖然表現(xiàn)出其向女性存在的歷史、社會(huì)、情感、性、男人等等維度延伸,亦有許多意識(shí)性的“反叛”在里面,但是,它們并不是如人們所意想的那樣,是一些“狂蕩的詩(shī)”,是一些“反叛的詩(shī)”,是一些“抗議男人”的詩(shī),是一些“女性自主意識(shí)的覺(jué)醒的詩(shī)”,等等。這些詩(shī)篇中最主要的意象和敘述提醒我們,“女性的身體”的自身經(jīng)驗(yàn)及其活動(dòng)的樣態(tài),仍然是這些種種維度的基礎(chǔ),是其詩(shī)性經(jīng)驗(yàn)所探索的重要的“可感覺(jué)到的世界”,是唐亞平的“身體詩(shī)學(xué)”的延伸。這當(dāng)中,并不特別表示某種“批判的意識(shí)”,更不特別表示某種“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就唐亞平的存在領(lǐng)悟來(lái)看,這不過(guò)是“某種儀式/被神排練/一場(chǎng)災(zāi)難被神預(yù)演”(《胎氣》),在世界的存在的“寂靜緩慢”(海德格爾語(yǔ))之中,存在便是“天地不仁以萬(wàn)物為芻狗”(老子語(yǔ))式的無(wú)善無(wú)惡,是“摸不準(zhǔn)陰晴”式的含混、迷蒙、沉淪。對(duì)于“身體”的沉淪,女人從來(lái)不作判斷,不然便喪失了其通往世界的道路,因此,一切有關(guān)于“身體性”的表述,在唐亞平這些詩(shī)篇里都占據(jù)重要地位,在其詩(shī)學(xué)視野里,這一切表述都依然閃爍出存在之詩(shī)的光輝。
在這里,我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沉淪”的樣態(tài)是具有悲劇性情調(diào)的狀態(tài),隱藏著對(duì)于存在的“宿命”式的接受和順從。縱觀《黑色沙漠》、《意外的風(fēng)景》、《月亮的表情》這些詩(shī)篇,其濃烈的憂郁氣氛架構(gòu)了它們的基本情感模式。這亦是唐亞平全部“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基本情調(diào),其中原因,自然與“身體”的速朽性有關(guān)聯(lián)。然而,正是這種情調(diào),構(gòu)成唐亞平詩(shī)學(xué)的隱蔽的生命意義和超越性價(jià)值的基礎(chǔ),我們亦可由此而感受到唐亞平全部“存在之詩(shī)”的內(nèi)在超越性的精神趨向。經(jīng)由“懷腹”和“身體”的觀念而啟發(fā)的詩(shī)學(xué),自然具備了對(duì)于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象征式表述。一如女權(quán)主義者愛(ài)說(shuō)的:“顯然,婦女不像男人那樣寫(xiě)作,因?yàn)樗蒙眢w說(shuō)話,作品來(lái)自于她的軀體”(埃蘇娜·西蘇),也如梅洛·龐蒂所說(shuō):“世界的問(wèn)題,也可以從身體的問(wèn)題開(kāi)始,就在于一切均現(xiàn)存地存在著”。這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在寫(xiě)作的方式和寫(xiě)作的意義上,都被置放到了存在的終極狀態(tài)之中,由此彰顯出“女性的詩(shī)學(xué)”對(duì)于普遍的詩(shī)學(xué)的啟明作用——一種最“無(wú)邪”與“無(wú)思”的詩(shī)學(xué),其精神,直溯至《詩(shī)經(jīng)》年代。
當(dāng)一種“女性的詩(shī)學(xué)”建立之時(shí),即是與其他詩(shī)學(xué)話語(yǔ)產(chǎn)生差異之時(shí)。此時(shí),性別的差異則具有了對(duì)立的性質(zhì),唐亞平對(duì)此具有自覺(jué)。當(dāng)她準(zhǔn)備敘述一個(gè)女性的“黎明前圖騰的夢(mèng)境”之時(shí),她立刻寫(xiě)道:“不能讓那只鷹在山頂上俯視這片田地,這片剛播種的田壩”,這是一種強(qiáng)烈的“身體”的警覺(jué),出自女性的身體的直接反應(yīng),正如其在《黑色洞穴》中所抗議的那樣:“那只手瘦骨嶙峋/要把女性的渾圓捏成棱角”,要“轉(zhuǎn)手為乾扭手為坤”。這種反應(yīng),無(wú)疑指向另一種詩(shī)學(xué)的話語(yǔ)——男人的、男性的、男性指向的話語(yǔ),文明、意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亦指示出這另一種話語(yǔ)的“迫害的”性質(zhì)。這是對(duì)于自己的詩(shī)學(xué)的一種自覺(jué),因此,唐亞平立刻又補(bǔ)充道:“雖然鷹的眼睛銳利刺骨/女人們卻有更加銳利的舌頭”,奇妙有趣的比喻和比較,不經(jīng)意間便揭示了“女性的詩(shī)學(xué)”的話語(yǔ)的力量。雖然“女性的詩(shī)學(xué)”具有對(duì)于普遍詩(shī)學(xué)的啟明作用,然而其話語(yǔ)的建立必定帶來(lái)批判的動(dòng)力,對(duì)于當(dāng)今有關(guān)“女性詩(shī)歌”討論中的濃重的“男性指向”,唐亞平的詩(shī)學(xué)或能作為建設(shè)性的意見(jiàn),而對(duì)這些“男性指向”的詩(shī)學(xué)予以有力的批判和有益的啟示?這亦是我們參與“女性詩(shī)歌”的研討的最初的想法,希望人們由此而能注視到“詩(shī)”之隱而不彰的局面,以及由此而能再次歸返到對(duì)于詩(shī)的本質(zhì)的期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