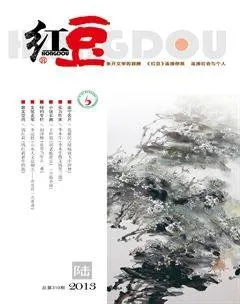苦難困境與人性之光(評論)
深潛在齊魯大地之中的李木生的散文,是與浮躁喧嘩的文壇保持著距離的一種獨特的聲音,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寫作是作家對自己和世界的一種言說。發表了百余萬字散文的濟寧作家李木生創作題材是寬闊的:山水氣象、歷史文化、現實人生、個人經歷,都在他的筆下以其獨特的個性生動豐富地呈現出來。《唐朝,那朵自由之花》、《妙響滌塵》、《夾在北宋和南宋之間的這個女子》、《去見阿炳》、《人之歌》、《天堂與煉獄之間》、《微山湖上靜悄悄》等作品進入多家散文選刊、選本,為許多散文讀者所喜愛。透過這些內容相去甚遠,但卻同樣情緒飽滿的文字,可以感覺到,作者內心深處有一種植根很深的東西,長久而執著地發揮著作用,成為他創作的動力,激情的源泉。這就是對于苦難和困境的執著表達和思索叩問,對于美好人性的深長而又詩意的呼喚,對于現實人生的洞察與沉思。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光鮮靚麗的浮華文字形成鮮明對照,顯示出一種深沉的力量。
米蘭·昆德拉說:“對小說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歷史狀況是一個人類學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問題:人類的生存是什么?”生存究竟是什么?這確實是每一位作家無可回避的問題。對于生存的理解和在作品中對于生存的表達,既決定一個作家的精神層位,又展現一個作家的人格力量。
在許多時候,生存就是困境和突破困境的努力,而這種努力,有時往往表現為對于人類苦難的再現與拷問——這也是文學永遠的題目。但是,關注苦難卻并非易事。近年來,很多作家已經漠視、忘記了真正的苦難。或者是為贏得自己的“好日子”而使盡渾身解數,并為已經獲得的各種收益而沾沾自喜,自我炫耀,文字也往往空洞無物,形式大于內容;也有的作家把游山玩水中獲得的一點小感覺加上導游書中的景點介紹,形成一些不咸不淡的文字;還有一些人雖然寫苦難,寫悲苦的命運和慘烈的人生,但作者只是隔岸觀火者,并未對自己表現的生活有更多思考,而僅僅是用苦戲換取眼淚和同情,不能不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媚俗。
李木生不是這樣,他是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在這種苦難與悲劇之中,并冷靜與勇敢地思索造成苦難與悲劇的根本原因。他的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的,正是這些表現人生的苦難和困境的作品,其中有普通人遭遇的生存苦難,也有因堅守人性理想而帶來的精神困境或人生悲劇。但是他所選擇的往往是那些未被困境打倒,堅守人性中美好的東西,即使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辭的人物。他筆下的人物既是真實的,又是作者精神追求的表達和延伸,從而顯示了一個底層知識分子的獨立與風骨。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的作品顯示了巨大的藝術張力和時空超越性。
李木生作品中那些命運坎坷的才女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李清照、薛濤、祝英臺、新嘉驛壁上題詩的那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女子、蕭紅以至那位殘疾青年的妻子……這些情感豐富的女子一個個都成了人類苦難與社會悲劇的犧牲者。在叩問“為什么”的同時,作者更將同情與贊賞獻給她們:“女人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難,女人注定能承受更多的苦難;女人因為承受苦難而美麗,女人也因為承受苦難而偉大。”(《圣地三女性》)與注重功名利祿、升官發財的男子相比,女人總是將情感看得高于一切,而這也就注定了她們的悲劇命運。“癡情就是苦海吧?在這個不人道的男權社會里,男人有著光宗耀祖、‘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他們甚至可以為了天下最為自私的皇帝‘舍生取義’,惟獨不會為了一個癡情的女子而燃燒而犧牲。他們可以是所謂的國家棟梁,卻總是情感的侏儒。他們不知羞恥地將自己的情感,偽善地分割成一個又一個的‘惟一’、一個又一個的‘階段’(實則始終圍繞著一個自私),惟獨不能像癡情的女子那樣,為了心愛的女人全身心地燃燒,直至成為灰燼。于是悲劇,也就總是落在美麗而又癡情的女子頭上。”(《蘇三離了洪洞縣》)通過這些抒情意味濃重的吟哦之聲,我們分明聽得到作者內心深處的鞭撻與呼喚。
李木生還寫了許多具有獨立精神又充沛著人味的知識分子,孔子、孔尚任、賈鳧西、李白、晏子、魯迅、食指、昌耀、林賢治、張中曉、陳我鴻……在漫長悠久的歷史中,總有許多思想者因為不媚俗、不阿世、不諛上而遭遇命運的種種打擊,承受種種磨難與艱辛。作者選擇了那些最觸動心靈又最能表達其人文理想的人物,在對人物命運的描述中,形成一種心靈對話。在人物的苦難感、壓抑感和美好人性的堅守中,既有潑辣的批判的筆觸,又滲透著作者對于生命的理解和表達。
“天真爛漫”的李白曾經“仰天大笑”接受天子召喚,但最終卻明白了“御用”的本質是“泯滅了一切個性追求與自由理想”,看清了中國知識分子宿命般的命運和可憐的愚忠、卑劣、虛偽與庸俗,最終把頹喪連同痛苦一起蕩滌凈盡,走向“一覽眾山小的自由精神的高度”。(《李白當年生活得好嗎?》)布衣本色的孔子,這個“與泗水一樣常流常新的年輕又挺拔的教師”在小小的杏壇傳播理想,主張平等仁愛,體現出生命的樂觀與幽默。雖飽嘗苦難挫折,卻始終不改對于國君、大臣和當世時事的批評的態度,與主流的聲音唱反調,大膽地說“不”。這樣一個孔子與歷代皇帝供奉著的“那個丑陋的老頭子”是“相距著十萬八千里的”。(《杏壇》)
如果說,在李白、孔子身上,作者把自由、平等、追求個性、反抗與批判等知識分子的基本品格用詩性的表達強調出來,讓我們看到其與現代意識的共通性,那么,對孔尚任的描寫則更復雜也更耐人尋味。孔尚任得到過皇帝的青睞,有著千百年來的文人的典型心態:渴求功名,對皇帝的知遇之恩有一份忠誠感激,即使已被罷官,也不甘心回家,而在京城苦苦支撐,渴望東山再起。但他心中卻有另一個聲音:崇尚自由,在心里堅守著一塊獨立的天地。《桃花扇》的創作使他“壓抑、郁積的心性得以抒展”,現實的苦惱化作劇中人物的悲歡離合,也使人性得以從現實的污泥濁水中超脫。(《山水與皇帝之間》)一個匍匐于天子腳下苦苦等待的被罷免的官員,一個在劇作中通過對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命運和悲劇性的愛情故事充分展開自己的人文理想的知識分子,就這樣以其復雜、多棱、豐富的內涵,表現出了知識分子內心的矛盾和掙扎,極具典型性,較之其前一類作品具有更多的內在精神含量。
對于現當代人物,作者最感興趣最有話要說的仍舊是那些身處逆境卻閃爍人性之光的人。食指、昌耀、孔孚等人是李木生用筆墨較多的,他們的人生中有諸多悲涼痛苦的經歷。詩歌都是源自苦難的歌唱,但又指向未來,渴求精神解放,唯其如此,他們始終不移的叩問和堅守才更有意義。
談到苦難,真正從生存到成長之路上都充塞著艱辛的還是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們。而這些人身上的高貴品格,才更有動人的力量。《天堂與煉獄之間——一個殘疾青年的文學人生》曾經感動過許多人。一個生長在農村,不能行走的殘疾人,為生計作難,為柴米油鹽奔走,受盡侮辱與損害,但卻始終揣著詩稿,揣著文學的夢想。當作者對于自己忙著各種事物,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卻未能伸手的深深懺悔,則顯示了一個作家的良知,也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共鳴。
總之,自覺的苦難意識使李木生作品中的古今人物身上,都滲透著一種超越個人具體命運的形而上意義。當我們跟隨著人物的命運前行時,就會穿透歷史塵埃,體會到一種帶有批判力量的現代性當下性,作品的獨特的價值也便從中凸顯出來。
如果我們把李木生作品放在文學發展的長河中,以更高的水準來衡量,就會發現其明顯的缺憾,而這些問題不僅是其個人的,也是當代散文必須認真面對的。如人物的單向度傾向:作者往往抓住人物身上那些符合作者理想的方面,充分發掘,不斷延伸,通過大量生動的情節向前推進。換言之,作者內心深處的人文理想比如平等、自由、不甘于命運的抗爭等等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但如果單向地表達這種東西,忽略了人性的復雜性,會使作品缺少立體感和更豐富的精神內容。又如過度抒情的問題。近年來歷史文化散文中引經據典,食而不化,作者本人精神不在場的弊病曾受到很多的批評。李木生能夠在廣泛讀書的基礎上,吃透并消化史料,形成人物與自我之間的自由對話,這是對同類散文的重大突破。但是,作者的情感過于強烈,抒情意味過濃,情緒過于激越,節奏上缺少舒緩平實,讀多了會造成審美疲勞。而且,這種強烈的判斷帶有一定的強制性,把話說完,說透,沒有給讀者留下空白,留下一個開放的可以自由延伸的思考空間,反而會減弱作品的韻味。再如缺少閑筆和幽默。這是當代歷史文化散文也是李木生散文所存在的缺憾。從李木生的作品中可見其盡量將文字宕開,以史證史的努力。但過于認真的態度中缺少一種從容,那些為豐富作品的內涵而加入的東西也就不是閑筆,和主體內容一樣給人一種緊張感,而缺少讓人暗暗發笑又拍案叫絕的輕松和幽默。重讀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歷史文化散文,這種體會更為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