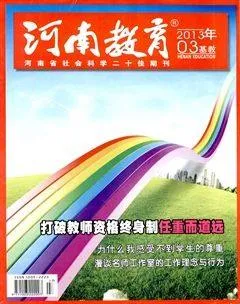尊重教育才能尊重教師
同事去南方一所學校開會,回來講這所學校的面貌:管理嚴格,校紀嚴明,成績出眾。有幾個細節讓我們印象深刻:作為寄宿制學校,學生兩周回家一次,住宿期間,全校沒有一名學生帶手機進校;課余,學生糾察隊排著整齊的兩列隊伍,在校園里執勤……
與此同時,《上海教育》卻報道了上海一所學校開辦“思維廣場”的新聞:學校每周安排三個班級在一個“集圖書館、電腦房信息查詢、同學自學、師生討論等功能于一體”的稱為“思維廣場”的教室里進行時長145分鐘的學習和討論,內容涉及歷史、地理、政治、科技、網絡、教育等各種主題,以培養學生“辯證思維的觀念、科學思維的方法”。
這是兩所完全不同的學校——我們習慣于認為前者“辦學成功”,又往往會為后者的創新突破而感到振奮。我則一直追問自己:學校原本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學校是不是應該像軍營那樣管束學生?課堂是不是應該完全由教師來主導?學生是不是應該以考試得高分為主要學習目的?如果答案是“否”,為什么我們離開教育的本源那么久那么遠,改革卻依舊那么艱難?
《南方日報》曾登載過一名10歲男孩馮邵一的退學申請書,其中寫道:“我申請退學,我不想把我的理想葬送在這無聊的考試中。”這孩子成績優異,連跳三級讀初一,卻對學校教育充滿失望。
同期,武漢則有七對父母放棄城市的優質教育,去鄉下找了一所廢棄的小學,自己教孩子誦讀經典、練習書法。這些家長對現行的教育體制做過努力,但最終失去信心。為了保護孩子們的天性,他們不得已走上這條“桃花源式”的教育之路。
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學校教育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問自己:學校教育是必需的嗎?未來的學校會衰亡與解體嗎?如果馮邵一真的不去學校,在家學習,結果會如何?會比在學校差嗎?我沒有答案。
但是對學校教育不滿的呼聲越來越多,卻是大家都看到的現實。學校教育正在扼殺學生的創造性、思辨力、好奇心以及興趣、特長等,用固定統一的標準化考試將所有人納入共同的評價體系。加上學校行政化、教育功利化、眼前利益至上,學校口碑與教師地位的下滑便不可避免。
我和栗瑞瑩老師思考的都是教育問題。栗老師思考的是“為什么我感受不到學生的尊重和愛”,我思考的則是,為什么我感覺到學校存在的價值已經不再是天經地義。這兩個問題表面上看不相干,實際上卻是一致的。如果學校教育沒有為學生的成長提供足夠的支持和幫助,學校教育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教師又怎么能夠得到學生的尊重?僅憑《教師法》的規定,對學生說:“我是老師,法律規定了你必須尊重我。”這種邏輯成立嗎?
這些年,我們必須注意到的事實是,每到教師節,總有人在網絡上質疑教師。一個典型的論調是:教師只是眾多職業中的一種,憑什么我們要單單尊重教師?如果教師的職業并不高人一等,教育行業從業者的道德水準與綜合素質并不明顯超過平均水平,我們又為什么單單強調尊重教師?
更何況,這些年來,某些學校已逐漸淪落為把學生培養成“計算機器”與“記憶機器”的工廠,成了“學生想干什么偏不讓學生干什么”的地方。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拔苗助長、竭澤而漁,學生的創造精神與思辨能力在題海與補課中喪失。這種學校教育不僅不能對社會發展起到引領作用,反而在社會各界的質疑聲中我行我素,僵化依舊。我們有什么資格要求得到別人的尊重?
學校教育一靠課程,二靠教師,歸根結底,還是教師。因此,尊重教師就是尊重教育,尊重教育就是尊重教師。其實,從我們做教師那天起,就不必指望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受人尊重,而應當依靠自身的努力贏得別人的尊重,為提升學校教育的形象進行不懈的努力。
(本欄責編 盧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