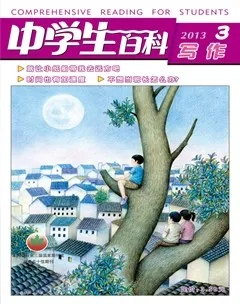數學啊數學
喜歡上三毛,并不是因為她的撒哈拉或者是她跟荷西的驚世愛情,而是因為某一篇文章里她說她的數學不好,總考零分,某一次憤而背上答案,結果考了滿分,老師疑惑,把題目順序換了換,可想而知,我們的才女三毛重新吃了鴨蛋。
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三毛,太可愛了吧?又怨恨那老師:干嗎要那么聰明呢?知道小詭計就行了唄,非得要揭穿嗎?
高中以前,我的數學是不錯的。至少,它沒有成為我的一個負擔。
悲慘的是上了高中。高中數學分了一支叫立體幾何。那是噩夢的開始。
從前,一張紙上,一條線跟另一條線只有相交或者平行兩種姿態吧,到了立體幾何這,還有種叫相離。噓,悄悄告訴你們,就是現在,我寫這篇文章,寫到這一點點的知道,我的心也是虛的,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是不是確切,或有錯誤,你們權當原諒一個被數學攪得一腦子糨糊的人吧。
我們被幾個面、幾條線啥關系搞得暈頭轉向時,那個頂著“地方支援中央”頭型的數學老師教我們一個妙招:看墻角。
期末考試最壯觀的是,一班的同學的目光齊齊地盯著某墻角。監考老師都給弄懵了,也盯著墻角看,那空空如也,沒發現燕子窩或者蜘蛛網,有同學揭曉謎底,看幾條線相交。
只可惜,能從墻角看出答案的題也就一道,其他的,還是糊涂著。一張白紙上,怎么也看不出來個紙盒兒來,哪條線與哪條線空中交匯,算了,還是糊亂猜個A、B、C、D來得爽快。
點背的時候喝涼水都塞牙,十個選擇題怎么猜的呢,一個都沒對。越是學得一團亂麻,就越是不喜歡學。惡性循環,讓數學老師頭發急得掉了很多也沒辦法。
文理分科時,因為可惡的數學去了文科班。文科班一幫子數學不好的人,五十步就別笑百步了,大家一個樣。可是矬子里總還有高個,數學總還是得考。
換了個眉心是“川”字的數學老師,愛自夸,這回是三角函數了。川字眉心老師畫拋物線和正弦余弦曲線,畫完總不忘自己夸一番:看我畫的這線,比木匠用砂紙打磨過的還光滑。我的心思不在那彎彎曲曲的曲線上,我想的是:干嗎川字眉老師一扯就扯木匠那去啊?上回畫橢圓時也說過一回,木匠師傅都得請教他。難不成在當數學老師前,他是木匠吧?
大概那么枯燥的數學課上,我的笑如蒙娜麗莎的微笑般不可思議吧,數學老師點了我的名字:“你來說說這題的解題思路!”
那一刻,我很想像動畫片里那樣一個長拳打得川字眉心老師眼冒金星,然后趁他沒反應過來時,我悄悄逃走。只是,我像只呆瓜一樣站起來,嚅嚅喏喏好半天,說,我不會。
川字眉心老師眉心的川字更深了,如刀刻的一般,然后我的目光碰上了他的目光,我的頭低了下去,我很為自己的智商不夠學好數學而懊悔萬分,我甚至很自卑地想:笨蛋這個標簽數學老師肯定牢牢地給我貼到額頭上了。
搞不懂數學不好為什么就被認定是不聰明呢?
我挺會寫作文的,我背英語單詞也很快,那些復雜的地理分析題我也手到擒來,只是數學,那些題個個都是個大陷阱,等著我往下跳。如果是選擇題也就算了,好歹不至于白卷。碰上填空題就很讓人費解了,到底要填些什么呢?有一度,“0”和“1”這兩個答案很吃香,但是十個八個空,總不能都填“0”和“1”吧,那樣也太過故意了。但你不都填,碰上的概率就小很多。這可真讓人頭疼。
那時班里有個挺丑的男生,眼睛小、鼻子大的那種,他很愛睡覺,上課就睡覺,尤其是數學課,但氣死人的是,一考數學,就幾乎都是滿分。倒是我們瞪著大眼睛聽滿45分鐘的人,考的那幾分都對不起那幾個哈欠。
于是很認命地說:看吧,這就是智商,真不是我不學,實在是腦子不好使,有本事找我爸我媽去啊!
川字眉心的數學老師指了指角落里的一胖胖女生說:“你們如她一樣努力,考零分我都不怪你!”
女生用的是笨功夫,每次下課都攔住川字眉心的數學老師問個沒完沒了。她的數學成績并不能算很高,但絕對是在中上水平。
不夠聰明又不努力,這兩大罪名讓我恨死了數學。
終于高考了,命運那個愛搞惡作劇的孩子讓我學了財會。還是要跟數學打交道。我簡直要呼天搶地質問蒼天。
但是,又能怎么樣呢?既來之則安之吧。
我擺弄起算盤,重新開始做那些復雜的計算。要知道,將來我真的做了一名財務人員,那可都是錢啊。
好在,不用立體幾何和三角函數,好多了。
再然后,畢業后,我把我的業余愛好發展成主業。我看書,寫字,不用每天跟數字打交道。生活里我能用到數學的地方就是數錢,極慢極慢地一張一張數的那種,老爸每每看到我這樣,總是笑話說:“這財會你是怎么學的?兩千塊錢你都要分堆數啊?”
我其實很高興這樣。我終于可以名正言順地數學不好。我終于可以無比同情地對那些仍然在學校里,仍然被數學折磨的同學說:熬吧,熬到有一天,你終于可以藐視它時,你就可以對數學大笑三聲了。
最后,我還想不明白,以三毛的聰明,干嗎只背答案啊?要我,肯定連題一起背下來了。如果那些考題不變的話。問題是,每張考卷上的數學題總是變啊變的,比變形金剛還能得瑟,變得我認不出來,不然的話,哼哼,憑我的好記性,我肯定能得滿分啊。
唉,三毛的老師我原諒他了。
其實,我想說的是,我數學不好,我也挺聰明的,是吧?
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