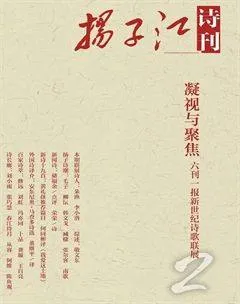(斯洛文尼亞)阿萊斯·施特格詩選
x阿萊斯·施特格,斯洛文尼亞最活躍的新生代詩人、作家,也是成功的譯者、編輯、策展人,1973年生于古城普?qǐng)D伊,畢業(yè)于盧布爾雅那大學(xué)德文系,現(xiàn)居盧布爾雅那。有詩集《時(shí)鐘棋盤》(1995)、《克什米爾》(1997)、《突出》(2002)、《名物書》(2005)、《身體書》(2010),散文集《仲夏的正月:秘魯游記》(1999)、《用手指和腳跟》(2009),短篇小說集《柏林》(2007)。
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你會(huì)看見一首詩。
它清空你私欲里的所有固著之物。
它提醒你還有個(gè)剛粉刷好的新房間
在夏天忘了關(guān)上那里的門和窗。
但這不過是關(guān)于物質(zhì)世界的形式的蹩腳比喻。
這首詩可沒有進(jìn)口和出口。
這首詩盛著騰騰的蒸汽。
形象們?cè)诶镞吰。[喻
掛滿了四壁而那乳白的氣流
消弭著重組著,其他的也是一樣。
有兩朵赤裸的云,正要做愛呢,
被星空驅(qū)散又再噴吐成一團(tuán)
屠宰過的野豬云并繚繞在灰霧中
冒出一位老爹的煙頭,此人
隱藏在詩歌的陰蔽角落,觀看一切。就好比
他是一切詩歌的真正作者。你看不見
暗處的他,除非他愿意現(xiàn)出身來,
悄悄地,從背后,惡作劇地用手蒙住你的眼睛,
問你:我是誰?你想干掉我是嗎?你是我的人嗎?
沙 洲
昨晚我被園子里的橡樹林吵醒。
就在那邊,頭戴冠冕的巨木,讓我又再聽見
我內(nèi)心世界里的悉索。
那是一幅神奇的顛倒圖景,
仿佛你突然就擦亮了銹蝕的物鏡。
那些長(zhǎng)久積壓在深處的模糊難辨的東西
都翻上了表面。成為了表面。
早晨,我剛打開門便踏進(jìn)了
齊踝深的枯黃落葉之中。
我輕輕撥開它們?nèi)缓笥肿哌^兩道門。
第一道門通向我一樣的世界
而第二道門通向我不一樣的世界。
譯注:沙洲(Sandwerder)是德國柏林的一條老街。
一個(gè)半
我很久沒說話了。落到我頭上的一切都
沒有反應(yīng),沒留下一點(diǎn)痕跡。在傍晚
我的語言是讓你夾在了陽臺(tái)上的我的衣服。
那件襯衫它擁抱過我,襪子
以及它的唇痕還印在我的腳踝——都空空的了
跟我長(zhǎng)褲的擺動(dòng)中那些消沒的足跡一樣。
我很久沒說話了,就連我的舌頭的
所愛也已遠(yuǎn)離。像你手中的名詞。
那雙手遮映著你前額的光彩,
繃直你長(zhǎng)發(fā)的卷綹,取下
你唇間的衣夾然后轉(zhuǎn)來把我夾緊。
我晾在我自己面前,那仿佛從不存在的。
而你是一片內(nèi)心熾熱的云
靜靜地在我衣服里飄過。
突 出
無聲的離子噴發(fā)。能量懸停成符號(hào)。
反重力。骨節(jié)中的電磁之舞。
突出。
裸眼可見的惟有當(dāng)身體蜷在暗處,
當(dāng)身體處在陰蔽和無助中,徹底投降,
就像病人向技師們的無情雙手投降
當(dāng)他們關(guān)上透視室的艙門
讓他獨(dú)自跟機(jī)器待在一起。
膠皮一樣的抽吸著他的胸腔。
輻射。或可致命。
突出。
億萬里遠(yuǎn)距著太陽的色球?qū)?/p>
白熱氣團(tuán)的運(yùn)動(dòng)毫無來由地
在虛空中蝕刻著龐然的圖景
然后又分離,急速撲進(jìn)宇宙。
輻光。難以覺察。
突出。
突出。
讓語言以光的波長(zhǎng)
穿行在記憶和肉體吧,
寫下患部,療救這個(gè)世界上
那些殘損的名字。
譯注:“突出”(protuberance)指人身體的突出,如骨突、腦突;又指太陽的日珥。
以上選自詩集《突出》。
蠟 燭
如果有人死了,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
沒人到場(chǎng)。不是在這兒也不是在那兒。
只有一朵火苗在煤氣爐上兀自撲閃。
毫不起眼。它不是活的它也不是死的,
你一只手就可以把秘密全部掩藏。
它不會(huì)提問,也不會(huì)做出回答。
它不站在善的一邊。它不站在惡的一邊
它不懂虛假,不懂真實(shí),不懂講道理或廢話。
它不是未來也不是過去。
它是同時(shí)又不是。不是它所是也非你所是。
它不會(huì)按自己的想法成為什么也不按別人的。
不是空氣不是火。不是光不是焰。
不是深淵不是天堂。不是是不是否。
如果有人死了,這人根本還沒死。
他只是順著他體內(nèi)的燈芯爬了下去。
而你從背后伸手,撲滅他。
石 頭
沒人聽說過石頭心里的秘密。
無關(guān)緊要,都是私事,比如被夾在
腳跟和鞋皮中間的一些苦惱。
要是你踢開它,在光禿的街面上打旋兒。
僅此一次,不可重復(fù);
而別的東西只是一堆堆腐爛的意義。
像隔壁診所的味道。沉默。那你繼續(xù)吧。
沒人聽說過你心里的秘密。
你是你自己那塊石頭的惟一的居民。
你剛把它給扔了。
耳 環(huán)
整日里他老是在說你該做什么該做什么。
他的聲音是一塊包著歇斯底里的巧克力。
他是個(gè)可愛的詐騙犯。一只瞎獨(dú)眼的貓頭鷹。
他老是看著這半邊世界去指揮另半邊世界。
他最喜歡對(duì)著鏡子欣賞自己,要是你在別人面前夸他
他就要發(fā)瘋了。他可不是你的財(cái)產(chǎn)。他不是你的裝飾品。
除非是你跟他跳舞的時(shí)候做愛的時(shí)候,他才殷勤。
然后放出籠子了。然后他就是諸神的報(bào)喜天使了。
漸漸地你便把他打發(fā)開,把他藏進(jìn)盒子,把他亂放。
但他在你耳垂上的那咬痕還老是對(duì)你嘀嘀咕咕。
仿佛是愛神用一具無形的金絲鉗子把你夾緊
又把罪孽的言語和背叛的沉默焊進(jìn)你的耳朵。
它里面鑲的是一枚采自西緒弗斯山頂?shù)氖^的復(fù)制品。
你滾著希望上山。然后你又頂著宿醉和沮喪,獨(dú)自地下來。
門 墊
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要找誰?
在她的眼中你總是到處亂跑。
所以她才原諒失足的腳印。
原諒了瘸子、冒失鬼和醉漢。
要是踩過她的面頰也不算侵犯。
她還可以用她的長(zhǎng)發(fā)給你擦鞋。
用她的名字擦你的名字。直到一切無法譯解。
她不是指引方向的。她也不是給人啟迪道路。
她接納你把你當(dāng)成你所來處的景致的一部分。
她又送走你就當(dāng)是你要去處的景致的一部分。
她的長(zhǎng)發(fā)有時(shí)會(huì)咯吱你醒來。
然后拍干凈你言語中的塵土。
一聲咳嗽在她嗓子里默默旅行。
但她迎上去:出入平安。出入平安。
她深愛著那些在問話之間的無形走道。
無論什么傷害都要走過。答案永遠(yuǎn)是愛。
A
A死了。又沒有死。就像他的爸爸
A,就像他的爺爺那樣他淹沒在村里的公墓。
淹沒了但又沒淹沒。他走進(jìn)了泥潭
走進(jìn)了泥潭走進(jìn)了泥潭里沉默的石頭之中。
這里都清靜了。遺忘。抹銷。是這里但又不是。
因?yàn)檫@里沒地方了。他沒有名字沒有姓氏。A-A-A。
有人死了。沒有人。他的名字——
忘了。就像他爸爸的名字和他爺爺?shù)拿帧?/p>
A有時(shí)吱吱咯咯。就像某人已經(jīng)上了床
有時(shí)又起來,某人整宿沒睡又繼續(xù)等死。
有時(shí)A-A-A是在太空搜索聲源的難耐恐懼。
有時(shí)A-A-A是雨點(diǎn)打在街道上的單調(diào)哀傷。
A-A-A流進(jìn)大海的時(shí)候咕嘟咕嘟。
A-A-A在鐘表里發(fā)出石英的嘆息。
惟一可確定的是——A死了。
無論誰要是還想聽到他就得用另一只耳朵,
無論誰要是聽不到他就應(yīng)該到虛空里去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