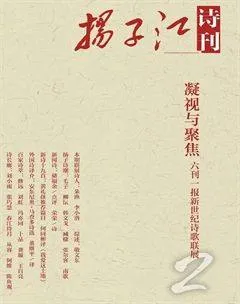南歌的詩
家 庭
我,變成了我們。
我們圍著這只木桌吃飯,幾個小菜,
升起一朵朵云。我們吃完了碗中的糧食,
不剩一顆米粒,也沒有
多說一句話。父親,我是飽含著愛
與孤獨,來完成這套動作。你認為
我想著這些,而我想到的卻是另外一些。
母親對我說:“在最親近的人面前,你也是
一個木頭人。”事實上,我說了這些,
想說的卻是另一些。作為小語種的
縉云話,傳到我這一代,早已銹跡斑斑。
我情愿我是那截木頭,無知無識,
簡單而果斷,在火中解決自己。
最后留下烏黑的炭塊,痛苦也好,
幸福也罷,埋在更多的灰中,
不奢求額外的理解。
甌江辭
他購置了一套地圖,
從街邊舊書店,領回一個故鄉。
現在可以準確地愛了,關上門,打開燈
按圖索驥,哦,他珍藏的思念
保存在第45頁。標尺換算出
時光與距離的多重關系。
“噢,甌江……”那條細細的小蚯蚓,
松動著浙江南部的一片丘陵。
“讓我再聽一聽,綿延八百里的呼吸,
以及江灘上童年刻下的腳印。”
他伸出腳,在淡藍的夢中,
抵達了此生溫柔的源頭。
四合院
墊腳的石頭磨出了閃人的光亮
五十年,奶奶的一生都儲存在這里
這里的每一塊石頭、每一片落葉都可以見證
時光的鋒利切割。有些人離去,移居
到泥土以下,把蚯蚓引為知己。
老房子為蜘蛛和爬蟲搭建樂園,老鼠們的聚會
一直延續到深夜。老鄰居五年前
入土為安,他栽種的葡萄結不出新的甜;
青草也搬過來了,在雨中瘋狂擴張自己的王朝。
每天都有坍塌之聲,從椽條的內心傳來。
這聲音只有奶奶聽得見,這個黑夜
比白天清醒的女人,分辨著靈魂的足音。
“烏梢蛇爬過的聲音”,她收集證據,
但苦于別人的遲鈍。去年大雪,一間空屋
色調黯淡的青瓦們從高處跳了下來。
泥墻兀自聳立一半,“老房子爛得快啊,
沒有人住,少了人氣”,人們發表時事評論。
這些來自后山的木頭與泥塊,終于累了。
塵歸塵,土歸土,它們懂得
葉落歸根,懂得駕駛一根朽木的時速。
“時間到了”,自然的律令布告天下,
時光之手,松開了攥緊多年的秘密。
仲 夏
光陰庇護滿手比喻的人
詞語一顆顆磨礪暗啞的燈。
不安的夜晚,美妙的時辰
密雨落下不留一絲縫隙
我摸到了感動的淚水,也摸到了
悔恨的淚水,
枯井里洶涌大江大河。
咸澀的夏天,再次站到了
我們的舌尖。
我們拿捏貨幣的脾氣,出售
一次愛情、一次理想、一次良心
這廉價的交易,每天發生
我們只剩口袋里的零錢
在叮當作響。
回鄉偶書
晚飯后,我混雜在他們中間,像一只
花間偷聽的蜜蜂。
老人仍然愛搖舊蒲扇,從屋內
搖到村口,落座的青石滲出薄薄的體溫。
談點什么呢?家事、作物、傳言、鬼影。
一句土話如劈空的閃電擊穿
我的肺腑,被樸素的痛苦依次照亮。
那些親切而生澀的詞匯
在喉嚨里滾動,我瞬間理解了
一只河蚌飽含的熱淚。
無論在哪兒,我都是異鄉人,被一只大手
連根拔起。這副舊身軀,漸漸失去葬身之處。
這個盛夏,我在山中閑居,
讀書,聽鳥,流淚
如一灘發炎的膿水,想爛在這里,
卻被傷口無情地擠出。
獨 坐
一個人坐出兩個人的呼吸,
幾只鳥,在陽光的撫摸中振動羽翅。
在下午,世界不胖不瘦,享用的那份孤獨
恰到好處。我不認識的幾株植物
也不認識我。只有身后的小樹,伸出
一條溫暖的舌頭。靜下心來,就能聽見
更多細小的悸動。比如那枝頭抖動的一滴喜悅
從風中慢慢傳遞過來。甚至把我這顆枯萎之心
埋入這片泥土之中,也能馬上
開出一朵淡黃色的香氣。
這里是人類未曾到達的世界,那么緩慢
有自己陶醉的速率,在草叢中埋下
運輸幸福的脈管。那些花,像開在時間之外
輕輕搖擺,不關心生死與凋零。
從人群中抹去的兩個小時,我領受了
一份羞愧。暮色四合,催促我重新做一次人。
我起身,木葉翻飛,光影涌動
小徑早已不是來時的小徑。
魂出竅
警覺于一個詞在我紙上
頻繁地滾動:“少女”,幾乎是
在反復磨一顆鵝卵石
光滑的皮:我又看見,
但不是昨日的那一個。
你靜靜地坐在一棵香樟樹下,
讀一冊時光書。
比風要慢,比樹葉的衰老要慢,
比兩只小蜜蜂的自帶引擎要慢,
很久才翻動一頁,頭頂的樹葉也跟著翻動。
慢得恰到好處,如果再慢一點,就有人
稱你為雕塑,就“到此一游”,
和你拍照留念。整個下午跑過去了,
你全身的彈性也沒有把你高高彈起。
青春有另一種美,另一種速度,
如同草莓有另外的甜。
你沒有察覺,也就沒有傷害。
我的靈魂像一只老狐貍,
從你身后驕傲地溜過去了。
我尊敬那些較真的書呆子
比如捧起一冊《論語》,不應該想到
于丹,而應該是另一些沉默的人,在紙的背面
像一棵棵倔強的玉米,終其一生,自愿釘在
某本典籍之中。他們白嫩的手
和尖尖的指甲,適合從事深夜的挖掘。
如豆小燈亮在乾隆某年、嘉慶某年
漢語的泥水匠,校訂著詞與詞夾縫中的倫理。
噢,這里少了一塊仁義,那個句子有
不為人知的險情,應該砌上一個典故保證
閱讀的安全性。這對詞,不過是一樁包辦婚姻,
但悲劇早已釀為喜劇,成為人們嘴邊的格言。
為了美觀,《孟子》需要換一種寫法,
要加高加厚,從背誦的大火中解救出來。
這些平日里的書呆子,在漢語的施工現場
揮舞考據的磚刀。整個夜晚,我坐在他們修葺的
空屋子里,那些較真的表情令人感激。
讀書記
進京的八股文簡直有些長甚至有些軟
國家正在施工,我們幾乎滑倒
古人的舌尖藏著蜜,但嘴巴貼了封條
現在需要的是我們年輕一點兒的針尖
噢,與傳統的野合就發生在紙上
和自己搏斗,靈與肉辯論出新意
下午已經汗流浹背。經典就是結在背部的
細鹽,抽一份教條的糕點,一寸苦,一寸甜
背誦給我當圣人的信心,也給我當無賴的勇氣。
我已經可以把影子臨摹得像一個人;
我可以憑空造出一個正人君子,只要你需要。
我確信,漢字說出了古人部分的狡黠
玩笑被不小心當作真理,被頌揚,被鐫刻。
名聲這么久遠,深入頑石三分;圣人已難以辟謠。
“教誨是危險的”,只有少部分人
深明此理:他們思考,但幾乎不寫作
只留微量筆記書于竹簡
深夜把玩一番,清晨送入火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