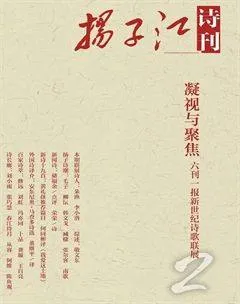張爾客的詩
在大地的邊緣漫步
當我推開若干種事物
在大地的邊緣漫步
并因為某一憂郁的顏色而欣喜
滾滾而來的時間和人
皆在我的陰影下尋找光明
像一個猴子穿過人群那樣
我行走在森林和石頭之中
并且與往事為伍
都是可靠而且血緣相近的親戚
并不顧忌于那些樹根和藤蘿
我還是朝向天空伸展臂膀
有種可以感觸的聲響轟然而鳴
不知是緣自于我的身體
還是地下三千米的深處
在一道矮墻上我坐下來
在必然為人追逐的逆境之中
我從一個遙遠走向另一個遙遠
如同在一面鏡子里奔突
四面都是透明的墻
那些石頭敲不開柴扉
陽光煮不沸雙手捧起的池塘
在我的軀殼之中,無數螞蟻結成方陣
它們的觸須比黑色的樹林還要廣袤
并且有種無法仿制的威儀
我以一根枯萎的野草探測其深度
并因為一次與風的約會
長出翅膀
大地的顛簸造就吶喊般的山巒
呻吟成為河流
我高高地飛舞猶如被擊碎的瓦礫
在一道矮墻上我終于坐下來
繽紛的落葉淹沒了我的雙腿
沒有后退
我只是望望尚可記取的遠方
將彎彎的刀子當作溫馨的月亮
再次有了攀登的欲望
墓園中的蒼蠅
那隊蒼蠅,盤桓于墳塋向每根骨頭
獻上黑色的吻和閃亮的頌歌
死亡,然后復活——
宛若總是被風翻閱的書籍
它們在輪回之中堅韌而幽雅
而那些手執鋤頭的人
以毛巾擦拭額頭之后癱坐于地的人
收獲嘆息和希望的人
在樹林里約會背負青草歸家的人
都曾聽過蒼蠅的贊美詩
牛的尾巴懸空
蚊子失去另一個陣地
蒼蠅以更加復雜的視角觀察
卻以更加純粹的思維生存
我看到蒼蠅用柔軟的爪子
撓著自己的睫毛
然后跳到掃墓人的背上
敲了敲早已關閉了的木門
為了一種遼闊
為了一種遼闊,我在黑色的句號里蹲坐
仿佛皮膚被撫摸之后裂開的傷口
這窗子將我和世界融為一體
必然會有一只鳥
其飛翔的路徑在你和我之間
太陽像一粒可以咀嚼的梅子
如果再有一把星星溫熱了的酒壺
我會安然于離你最遙遠的地方
我的姿勢
仿佛另一個人
棲居于我的軀殼
在自由的時刻
在沒有多少黏度的時刻
在失去重量的時刻
以一種輕煙的形式
表達未曾格式化的思想
并以高過自我意境的草葉
遮蔽身體
以透明的手指剝開結著厚繭的臉
如打開身體上所有的窗子
喊醒一個人或者神
更如在一張紙上筑造高塔
必然以一次稍微粗壯的毅力作為基石
用淚水黏結沙粒
在萎靡不振的隊列里我昂起頭顱
在頭顱的隊列里我是石頭
在石頭之中我是尖刺
在尖刺中我是必然的刺入
在刺入中我后退,退后十步
我站住,會有新的山巒出現
新的河流,新的樹,新的鹽和骨頭
新鮮如初乳般的呻吟
在站立之中我以被迫承認的方式
默契于自然的接觸
在綠色的和平之中我是紅色的戰爭
在灰色的演進過程之中我悲憫生命
此時有人敲門
香煙正好燃盡
孤獨的返回
在必然的境地里我種植
而于偶然中收藏
那些所能記憶的人一一被抹去
我還是從鏡子的背面
看到些殘存的身影
——記不起名字,卻依然親切
天際的返照比針更細,比網密集
捕撈的過程儼如垂釣一周
我總是不能拂拭自己
讓呼吸帶向遠方的沼澤
又如同鄰居般敲擊墻壁
釘上釘子,懸掛自己的影子
躺在那里,或者躺在這里
都是一樣的
總是有許多自己走來走去
互相握手
打招呼
那枚果實如果召喚我的名字
我猜不出
我會以怎樣的形式應和
以怎樣被別人最容易忽略的手勢
表達心底深處最真切的想法
也許捂住嘴唇是最可期許的
表達的選擇
我已經進入敘述性的語言
詩歌正漸漸離我而去,這使我惶惑
亦使我驚喜,如放棄一個枕頭
我推開窗子
小說如馬路般在我的眼前伸展
卻沒有更多的目光跟隨
而散文的翅膀飛掠即逝
如果有酒
如果酒后我坐在桌前
我仍然沒有惟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