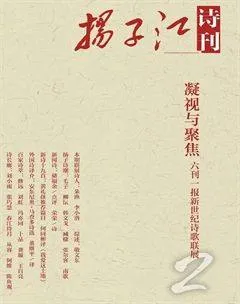毛子的詩
遷徙之詩
呆在家里,卻不停地遷徙
前不久,我跟隨契訶夫,搬到了薩哈林島
這個比我大104歲的老兄,不知道
我來自聊齋的國度,不知道
那里的鬼,像這里的囚犯一樣善良
他也不知道,與此同時
我前往了更多的地方。譬如畫家與瘋子集聚的巴黎酒吧
譬如中國古代的空山,那里盛產菊花、酒和長亭下
走來的故人
我喜歡這分身有術。喜歡靈魂
像一架運輸機,把無數的我
空投到不同的時代和生活之中
而我即將寫下的任何一首詩,都是它們
接頭會合的地點
它們像銀幕,一片空白
卻上演古往今來的波瀾和傳奇……
給薇依
夜讀薇依,其時窗外電閃雷鳴
我心緒平靜
想想她出生1909年,應是我的祖母
想想19歲的巴黎漂亮女生,應是我的戀人
想想34歲死于饑餓,應是我的姐妹
想想她一生都在貧賤中愛,應是我的母親
FSUbn3b8wDofTk+391nwIFLaM04Z4IhuAGVVC10XZZw=那一夜,驟雨不停
一道霹靂擊穿了附近的變電器
我在黑暗里哆嗦著,而火柴
在哪里?
整個世界漆黑。我低如屋檐
滾雷響過,仿佛如她所言:
——“偉大只能是孤獨的、無生息的、
無回音的……”
樹 木
它們不使用我們的語言,也不占用我們的智慧
它們在枯榮里開花、結果
它們各有其土,各有其名
它們跑到高山之上,平原之上
在夜里,它們會跑得更遠……
它們砍下做棟梁,就成了人間的部分
做十字架,成信仰的部分
做棺材,成死亡的部分
做桌子、椅子,成生活的部分
我們成不了這些,我們只能成灰,成泥土
在泥土里,我們碰到了一起
所以,那么多的樹,都是身體之樹
那么多的人,都是無用之人……
如 何
如何從詩學進入地質學。如何
從一個詞里,探測出歲月的儲藏量
如何在他者的經驗里,獲取
屬于我們個人的開采期
如何下到井里,做一名礦工
如何給內心裝上升降機,在頻繁的礦難里
把幸存和遇難的命運
分配給自己
如何面對這么多如何。像米沃什寫下
受用的詩歌
如何鉆探得更深,像一塊煤
對深淵和黑暗說出:我來自那里
我有足夠的
發言權
對一則報道的轉述
唐納爾,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
在911,他失去了懷孕6個月的女兒
時隔十一年后的一個五月
民眾涌上街頭,歡慶本·拉登被擊斃
只有唐納爾呆在家里,和家人一起
靜靜消化這個消息
他無法高興起來,他說
——“我們不是一個會慶祝死亡的家庭
不管死的是誰。”
我擁有的東西并不可靠
我坐著的這個下午,并不是我的
多年后,那些后來出生的人
也會像我一樣進入
但這個下午也不是他們的
它也不是祖先們的
哪怕他們比我早,比我年輕
有時候,我真的羨慕
街邊打雪仗的孩子
他們不必想我們的問題
他們把雪球拋得老高
要是沒有地球的引力
那些雪球就會在天上飄著、飄著
如果這樣我又會不會去想
——能落下來多好
能有個固定的地方,有個依靠
獨 處
河邊提水的人,把一條大河
飼養在水桶中
某些時刻,月亮也爬進來
他吃驚于這么容易
就養活了一個孤獨的物種
他享受這樣的獨處
像敲擊一臺老式打字機,他在樹林里
停頓或走動
但他有時也去想,那座逃離出來的城市
那里的人們睡了嗎
是否有一個不明飛行物
悄悄飛臨了它的上空
這樣想著,他睡了
他夢見自己變成深夜大街上
一個綠色的郵筒
——孤單,卻裝滿柔軟的,溫暖的
來自四面八方的道路……
懺 悔
我窮。
說過謊。
八歲時偷過父親的錢。
至于我拖欠的命,有青蛙、螞蟻、麻雀
和跟隨我多年的一條狗。
20歲進工廠,我嘲笑過一個喜歡我的女孩
原因是她丑。
95年在鄭州火車站,面對一個發高燒的農民工
我猶豫半天,但沒有掏出錢。
現在我已近耳順,尚在人世茍活。
我寫一種叫詩的東西,它們大多對不住漢語。
看來我遠不止七宗罪
但這首不算,它不是詩
它是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