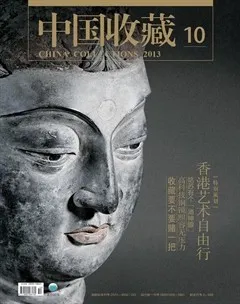侍女手中現神秘“丁字杖”










唐代墓葬壁中常見一類壁畫題材,表現侍女手持一件丁字形長杖的場景。日本學者原田淑人在《唐代的服飾》一書中曾提及丁字杖,并將其與正倉院所藏兩件玳瑁杖進行比較,然并未對其用途進行說明。齊東方、張靜兩位先生在《唐墓壁畫與高松冢古墳壁畫的比較研究》一文中亦有所論及,認為可能是尺,但亦未有定論。雖然前輩學者早已注意到這種丁字杖,但是對其名稱及用途尚未有明確的解釋和考證。
丁字杖怎么用
繪有丁字杖的唐代壁畫墓主要集中于關中和太原兩地,其他地區尚無發現。這些壁畫墓的年代絕大多數集中在高宗至武周時期,僅有關中地區陪葬昭陵的長樂公主墓年代較早,為貞觀十七年(643年)。長樂公主墓也是其中有明確紀年且年代最早的壁畫墓,墓葬甬道東壁所繪侍女群像,其中有一狀貌似“昆侖奴”的侍女,手持朱漆丁字杖,丁字杖頂端橫桿兩端似有對稱玉石或骨角類裝飾。此外,關中地區新城長公主墓(663年)、李震墓(665年)、韋貴妃墓(666年)中壁畫均可見手持丁字杖的侍女形象。山西太原唐墓共發現六座繪有手持丁字杖侍女的壁畫墓,分別為太原董茹莊趙澄墓(696年)、太原金勝村4號墓(M4)、金勝村6號墓(M6)、太原焦化廠唐墓以及太原金勝337號墓(M337),以及近年新發現的山西太原晉源鎮赤橋村唐墓(TC2001M1)。
整體觀察壁畫所繪丁字杖,從形制上看既不同于章懷太子墓、節愍太子墓壁畫上描繪的狀如彎月的馬球杖,從功能上看也不似安元壽墓壁畫中羸弱老者手持的拐杖。壁畫描繪的手持丁字杖者,皆為長身玉立的年輕侍女。同時,繪有丁字杖的壁畫皆位于象征內室的墓室中,手執丁字杖的侍女又往往與執拂塵、捧奩盒、執壺瓶等生活用品的侍女并出。即使壁畫描繪侍女人數較少,一般也會保留手持丁字杖侍女,并與執拂塵或是披帛籠袖的侍女兩人作并列狀出現。由此推測,丁字杖乃是屬于生活用具的范疇,且本身應該具有某種實用功能。然而,丁字杖到底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囿于材料所限,只能做一些合乎情理的推測:丁字杖的出現與唐代盛行的屏風畫有一定的關聯,與唐代日常生活起居方式的變革也有一定關系。此外,丁字杖很可能是借鑒了貴族出行時使用的行障。
畫障的風行
研究書畫史的學者大多認為立式卷軸畫即源于屏風畫。屏風畫,指的是裱貼于屏風面上的圖畫。唐代屏風主體結構為木制框架和紙質屏面,即白居易《素屏謠》所言:“木為骨兮紙為面。”屏風畫是唐代極為盛行的藝術形式,唐代著名的畫師皆擅繪屏風畫,如薛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張璪擅繪山水樹石,“樹石之狀,妙于韋鷃,窮于張通(張璪)”;更勿論“屏風周昉畫纖腰”——擅長仕女畫的周昉,據考證傳世《簪花侍女圖》并非一整幅手卷式作品,而是三幅相互獨立又有一定聯系的畫,其原貌正是類似日本正倉院所藏鳥毛立女屏風的屏風畫。
唐人對屏風畫推崇備至,促使屏風畫藝術大行其道,并逐漸脫離屏風而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屏風畫也稱為圖障,宋郭若虛《圖畫見聞錄》卷六“張氏圖畫”條載:“張侍郎(去華)典成都時,尚存孟氏有國日屏扆圖障,皆黃筌輩畫。一日清河患其暗舊損破,悉令換易。遂命畫工別為新制,以其換下屏面,迨公帑所有舊圖,呼牙儈高評其直以自售。”唐代屏風畫盛行,除了裱貼于屏風上外,也有脫離屏風單獨裝裱之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載晚唐進士及第者參與曲江大會之情景,曰:“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顯然,此畫障刻意沒有張貼于屏風之上,而是單獨盛之以袋囊,以供及第的進士隨身攜帶,乘興欣賞。
另一方面,“畫障”逐漸成為立軸畫之代稱,唐杜荀鶴《松窗雜記》載:“唐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此軟障(圖障)即是繪仕女圖的立軸畫。《歷代名畫記》卷二“論名價品第”條載:“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張彥遠自注曰:“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幛,故以屏風為準也。”可見,隋代之前,畫幛(障)尚未發展成為獨立的形式,而僅僅作為屏風畫附屬于屏風。及至唐代,畫障則逐漸脫離屏風,獨立發展。據此條文獻亦可一窺立軸畫(畫障)與屏風畫之間的淵源關系。揚之水先生《行障與掛軸》一文考證,所謂畫障即源自屏風畫,而后又發展成為獨立的立軸畫。
李唐皇族對書畫的收藏和鑒賞,無疑對屏風畫的風行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宮廷中設有專職人員對書畫進行裝裱,《唐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秘書省有裝潢匠十人,專職整理內府書畫。皇族對于書畫的熱忱也在墓葬壁畫中體現得淋漓盡致:1973年陜西三原焦村發掘的唐貞觀五年(631年)靜安王李壽墓,其石槨上線刻眾多侍女像,其中就有一名手捧卷軸的侍女;新城長公主墓壁畫亦有表現卷軸的圖像,墓葬第5過洞東壁中幅壁畫所繪男裝侍女手捧一捆卷軸,第4過道東壁北幅亦繪有捧持白色卷軸的侍女。線刻圖像及壁畫中所示卷軸究竟為橫幅的“卷”還是立式的“軸”,尚無從確定。但考慮到唐代屏風畫(畫障)的盛行,所以這些卷軸很可能正是畫障。同時也說明李唐皇族對書畫好尚之風。俗言“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唐代上層社會對書畫的收藏和鑒賞,逐漸成為體現高貴身份和非凡品位的風雅之事,但凡有一定藝術品位和經濟實力之人,自然會對此稱羨和效仿。
唐代日常起居方式的變革也與畫障的出現與盛行密不可分。人們由傳統的席地而坐逐漸演變為垂足高坐,同時伴隨著起居方式的變革,建筑物內部空間增大、各種家具相應增高。人們欣賞書畫作品的方式亦與其起居方式密切相關,在席地而坐的時代,人們的視線相對低矮,故狹長的手卷正是為適應這種生活方式而設,這也可以用來解釋前文所述隋代以前無畫障的原因。
此后,垂足高坐的生活方式逐漸盛行,人們的視線由于高坐而隨之上升。因此,畫障的大量出現也可視為是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源自屏風畫的畫障必須縱向張展,而不能如狹長的手卷可以沿水平方向平展;但是,考慮到唐代是由席地而坐漸變為垂足高坐的過渡期,室內陳設仍以臨時布置為主、隨宜安置為常,尚未形成在墻上固定懸掛畫障的習慣。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輔助工具方能觀賞,于是畫叉應運而生。唐李商隱《病中聞河東公營置酒口占》詩曰:“鎖門金了鳥,展障玉鴉叉。”障,即畫障;玉鴉叉,也作“玉丫叉”,曾一度被人誤認為是女子發簪,其實卻是張展畫障的畫叉。宋人因襲之,謝邁《玉茗花》詩曰:“憑杖邊鸞折枝手,應宜展障玉鴉(丫)叉。”唐宋時代畫叉展障的方式,可通過傳世文物及繪畫得以一覽究竟。傳世宋“仕女梅妝”銅鏡,鏡背后浮雕仕女人物群像,即表現眾人圍坐賞畫的場景。居左側的鴉髻仕女豎執畫叉挑起畫軸,另有一仕女手捧畫軸地桿,余人則圍而品鑒。至于挑畫的鴉(丫)叉,則是一根頂端分叉的細直長桿。
鴉叉展畫障
玉鴉叉,望文生義,想必是以玉石制成的畫叉。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六“玉畫叉”條曰:“張文懿性喜書畫……每張畫,必先施帟幕,畫叉以白玉為之,其畫可知也。”這種用料考究的玉畫叉顯然并非尋常物件。清人查慎行曾得一古物,經其考定即古所謂“玉鴉叉”,故作《畫叉》詩留念:“我有古玉器,裹諸片青氈。烱如一鉤月,映出初三天。纖纖銳兩頭,弓勢未扣弦。下連徑寸靶,中竅外規圜。愛惜徒手摩,致用無由緣。昨得桃竹杖,肌理細且堅。命工稍斵削,冠玉于其巔。呼之曰畫叉,古制想當然。”由此可知,所謂“玉鴉叉”,乃是以玉石制作畫叉頂端分叉的部分,其下連接竹桿而成。
通過對比不難看出,唐墓壁畫中的丁字杖與畫叉形制相類,惟畫叉頂端的分叉部分較為細小,與唐墓壁畫中的丁字杖頂端橫木略有區別。唐墓壁畫所繪丁字杖,形制上也有細微差別,有呈Y形或T形之分。前者多見于山西唐墓壁畫,杖桿頂端的橫木帶彎曲的弧度;后者則多見于關中唐墓壁畫,杖桿頂端的橫木較為平直。
丁字杖還與坐障、行障之間有一定關聯。坐障、行障,以布帛等織物為之,挑以長竿,供貴族出行時使用,起到遮風擋塵、隔離遮掩的作用。兩者形制類似,惟尺寸大小有別。《金史·輿服志》載:“行障六扇,各長八尺、高六尺,用紅羅表、朱里,畫云風……坐障三扇,各長七尺、高五尺,畫云風,紅羅表、朱里,余同行障。” 唐陸暢《坐障》詩曰:“碧玉為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云中語笑聲。”唐范據《云溪友議》卷中錄此詩則題為《詠行障》,說明唐代的行障與坐障不但形制相似,尺寸亦相差無幾。
唐墓壁畫中不乏表現侍從手執行障的場景,如李震墓(665年)所繪“出行圖”中,牛車之后緊隨侍女三人,居中袍服侍女,雙手持行障負于肩,障幔及繡帶自橫桿垂下,長寬足以遮蔽兩、三人。
壁畫上描繪的行障圖像,支撐障帷的長桿在形制上與丁字杖相類,而長桿挑掛行障的方式與畫叉展障的方式亦十分類似。通過與傳世繪畫進行比較,則更加直觀地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似性。現藏故宮博物院南宋《會昌九老圖》、現藏日本大德寺南宋周季常、林庭純《五百羅漢樹下觀畫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明《貞觀十八學士圖》以及清陳枚《月曼清游圖》系列之十一,所表現的均為眾人圍觀懸掛于畫叉上的立式卷軸畫的場景。
畫叉在宋代定型,并為后世因襲。其外形是一根細長直桿,頂端帶有分叉前頭,即李商隱詩中所謂“鴉叉”。揚之水先生認為立式畫軸的出現與唐代的行障密切相關,其展挑方式及裝裱形式都是從行障直接演變而來。因此,推測畫叉的出現可能也是受到行障的啟發。上文所引唐陸暢《坐障》詩“碧玉為桿丁字成”,即生動地描述了坐障(行障)呈“丁字”型的長桿,而唐代的畫叉很可能也呈丁字型,即唐墓壁畫中丁字杖的形制。
丁字杖現真身
日本正倉院中珍藏的兩件玳瑁杖,一件全長121.5厘米,橫木長32厘米,配有玳瑁制作的藤蔓,杖的末端鑲嵌著紅牙拔鏤(工藝類似于錯金銀,鑲嵌進去的是象牙,涂成紅色)。另一件全長133.5厘米,橫木長24.5厘米,杖體呈八角形,表面裝飾金箔,涂有綠彩,上面包有玳瑁,橫木的兩端鑲嵌象牙。
這兩件玳瑁杖與山西地區唐墓壁畫所繪的丁字杖如出一轍。太原金勝村M337唐墓壁畫侍女右手所執丁字杖,惟橫木兩端色白,應是刻意表現出的裝飾細節。這或許類似正倉院玳瑁杖鑲嵌之象牙。原田先生雖未深入探討玳瑁杖的用途,但指出其與山西地區唐墓壁畫所見丁字杖乃是同一物。
陪葬昭陵的韋貴妃墓,后墓室東壁北幅殘存的壁畫居中者垂足高坐于朱漆座椅,推測此人或為唐太宗本人;而同室東壁南幅壁畫則有一手持丁字杖的男裝侍女。可惜墓室內壁畫大多剝離,不見有卷軸。新城長公主墓葬壁畫則既有卷軸又有丁字杖,似乎也能說明兩者之間的關聯。墓葬第四、第五過洞東壁分別描繪了手捧卷軸的侍女,而在墓室北壁西幅和東壁南幅又描繪了分別持白色和朱色丁字杖的侍女。墓葬中的壁畫,完全可以作為現實生活場景的再現,因此從整體上考察可以看出壁畫所表達出這樣的意境:過洞中的眾侍女緩步走向墓室,準備將手中捧持之物(包括卷軸)進獻給墓室中長眠的新城長公主;新城長公主生前大概是雅重書畫之人,在墓室中侍女會接過畫軸,并用畫叉(丁字杖)懸掛起來,供公主鑒賞觀摩。
唐代上層社會對書畫的收藏和鑒賞,逐漸成為體現高貴身份和非凡品位的風雅之事。所以唐墓壁畫中常見手持丁字杖(畫叉)的侍女,便不足為奇了。筆者認為唐墓壁畫中所見丁字杖乃是畫叉,即唐宋史料中常見之“鴉(丫)叉”,其主要功能就是展挑畫障。丁字杖(畫叉)的出現既受到了行障(坐障)的啟發,也是為了適應唐代出現的垂足高坐的新型生活方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