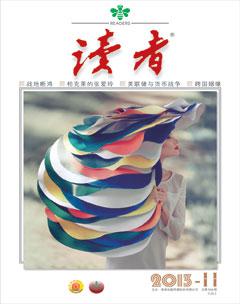文學回憶錄(節選)
2013-12-25 02:17:54木心,陳丹青
讀者 2013年11期
關鍵詞:小說
木心,陳丹青
要從中國古典文學汲取營養,借力借光,我認為尚有三個方面:諸子經典的詭辯和雄辯,今天可用;史家敘事的筆力和氣量,今天可用;詩經、樂府、陶詩的遣詞造句,今天可用!
《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欣賞古典作品,要有兩重身份,一是現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賞,則進進退退,看到后來,一只眼是現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在我看來,古代小說是敘事性的散文,嚴格說來不能算小說。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說才上場,即所謂“傳奇”。唐人傳奇精美、奇妙、純正,技巧一下子就達到極高的程度。契訶夫、莫泊桑、歐·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說家若能讀中文,一定吃醋。
整個明文學,只有金圣嘆是大批評家,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評他,是因為他將人家原文肢解鱗割,遷就己意,使讀者沒有余地。拿現代俗話說,還是把讀者看得太低。
有人一看書就賣弄。多看幾遍再賣弄吧——多看幾遍就不賣弄了。
文學的最高意義和最低意義,都是人想了解自己。這僅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覺、自識、自評。
世界上的書可分兩大類,一類宜深讀,一類宜淺讀。宜淺讀的書如果深讀,那就已給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書宜深讀,你淺讀,驕傲,自大狂;深讀,讀出一個自己來……《道德經》若淺讀,就會講謀略,老奸巨猾;深讀,會練成思想上的內家功夫。《離騷》若深讀,就愛國、殉情、殉國;淺讀,則唯美,好得很。《韓非子》,也宜淺讀。
(坎坎伐檀摘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文學回憶錄》一書,蔡志忠圖)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