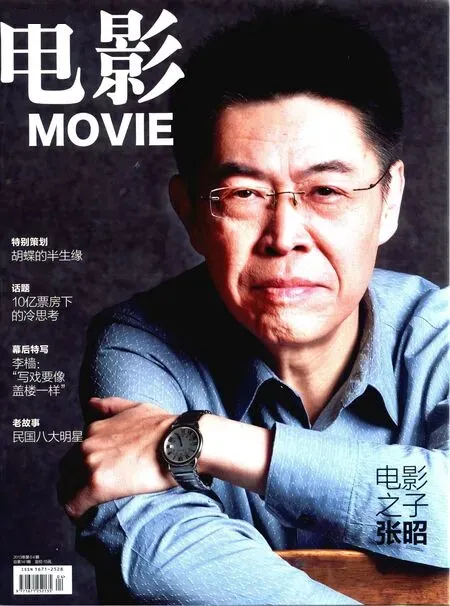電影,是一時一地的一個我
文/木夕
32年前,我出生在東北的一個小縣城。縣城里全部的文化設施就是一個電影院+一個劇院。
小時候,看電影和去公園一樣是一種福利。那時候爸爸單位偶爾會發票,每個大人可以帶一個小孩兒,我就坐在爸爸的腿上,抱著媽媽給我準備的紅黑格子小包吃零食。后來,媽媽調動工作,新單位就在電影院對面。媽媽偶爾帶我一起上班,跟電影院看門的叔叔打個招呼,我就能在里面看一下午。今天回想起來,演員、故事、情節都不記得了,只記得有一次電影院畫海報的那個叔叔指著滿地的油彩問我畫的像不像?我搖搖頭說不像不像。
后來上小學,看電影變成一種集體活動,出發前老師會反復強調紀律:走路要手拉手、隊形不能亂、看電影不許說話、回來要交觀后感……我天生好動,這些都是挑戰。那時候我總是很羨慕五年級的姐姐,因為她看完電影還能記住董存瑞炸的是哪一場戰役、哪個中學、哪一個碉堡,寫的作文也總能得獎。
初中、高中,班主任把體育課都換成了數學課,看電影成了一種奢侈。終于上了大學,我看的第一場電影是在學校后面小街上的一個地下錄像廳。錄像廳門外有一塊黑板,上面寫著每天要放的片子,每天下午四點是一元錢一場的精品場,回放一些經典的外國電影。那時候文科班的哲學課安排在周一下午一點,我總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夏天,風吹著窗簾蓋在身上,一覺醒來,正好能趕上小電影院的精品場。《羅馬假日》《金色的池塘》《廊橋遺夢》《克萊默夫婦》《魂斷藍橋》……都是從那里開始的。也算是做產業鏈吧,錄像廳旁邊有一個簡易的報刊廳,里面常常有各種各樣撕去版權頁的便宜電影雜志,買回來一起翻,茱莉亞·羅伯茨的嘴、凱瑟琳·澤塔瓊斯的婚姻、黛米·摩爾是否吸毒都是女生宿舍的熱門話題。那時候,骨子里有一點小叛逆,最喜歡的明星是蘇菲·瑪索。那時候宿舍還沒有電視,周末回家會追電影頻道的佳片有約。
后來學校的新圖書館竣工,增加了多媒體廳,門口一本厚厚的目錄本,辦張卡就可以點播自己想看的片子。一個學期,我從《西雅圖不眠夜》看到《兩個人的車站》,還記得我說要看《周漁的火車》的時候,看機房的老師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義正詞嚴地說:“這個片子剛來,我還沒審過,你們不能看!”
當時,系里有一個女孩兒看片海量,有一次在多媒體室遇到,她給我推薦了《藍色大門》。初見,以為是一個鬧鬧的偶像劇,于是放下。朋友再三催促,才交差式地揀起,誰知一發而不可收拾。那一年,也是在一個有海的城市里,我看完了張世豪和孟克柔的故事:沒有結局,但是有一個秘密、一個約定。漸漸地,電影對我而言成為一種除文字之外全新的語言,每秒24格,迎面而來,拂袖而去。幀與幀的排列組合讓我想起《紅樓夢》里的“丁香結子芙蓉絳、不系明珠系寶刀”,干凈利落。
畢業、求職、輾轉、無果。幾經反復,心頭那點關于電影的念想再次浮出水面——要一個跟電影有關的身份。碰過壁,夢想這個詞便不再輕易提起,但心里會偷偷憧憬,憧憬有一個機會像《藍色大門》一樣錯而不過、失而復得。偶爾也會學孟克柔,把心愿寫在紙上,一遍一遍,想著墨水用完它就能實現。之后有將近大半年的時間不再看電影,朋友問起我會開玩笑,“今天不看,為了將來每天都能看。”
2005年,我如愿來到北京。北師大藝術樓101、北國劇場、敬文講壇、藝術影院……勁頭足的時候一天能看四、五個片子,晚上一群人天南地北、指點江山。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慢慢地,初到北京的新鮮感逐漸淡去。生活像一部事先沒有走場、事后來不及剪輯的電影,現實、瑣碎,甚至是沮喪。人也會本能地懶惰、倦怠、健忘,不再想將來會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大人。一天收拾DVD,重新翻出《藍色大門》。再看已然不是當年的心境,但是臺北的陽光、海灘讓我瞬間回到了曾經的大連,瞬間,呼吸里也有了海水的味道。
工作四年,做著跟電影有關的工作,有一個跟電影多少有點關系的身份。把喜好變成工作,常常也會厭倦、沮喪、挫敗。這時候,偶爾會再翻出《藍色大門》,對著電腦屏幕吹吹海風。
2012年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報道,傳媒大獎的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問每個評委電影是什么?每個人,每時每刻總有不同的答案。在我,電影是一種可能,它意味著千千萬萬我不曾、不能經歷的角色、人生;電影,也是一時一地的一個我,時而在路上,時而已經抵達。它提醒我,低谷時自信,膨脹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