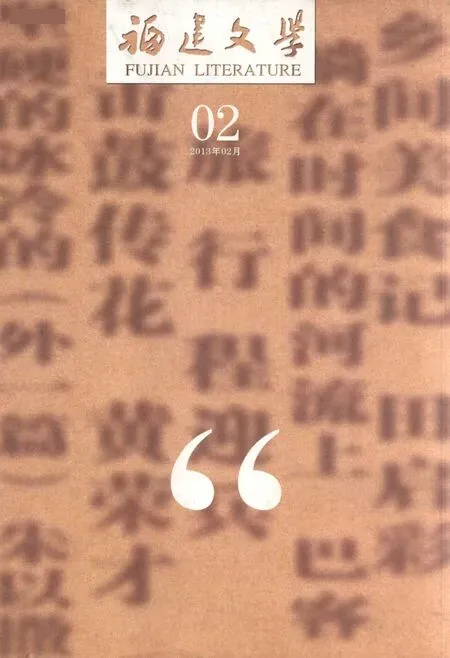斯文人的談吐——讀朱以撒散文
□黃加芳
英國作家毛姆說過:“要把散文寫好,有賴于好的教養。散文和詩不同,原是一種文雅的藝術。有人說過,好的散文應該像斯文人的談吐。”這里指出了一種理想散文的存在形態,那就是要“文雅”,要“像斯文人的談吐”。然而,由于散文文體自身外延的廣闊和自由、不拘一格的表達方式,也常常使得散文淪為一種毫無節制的話語的垃圾場,枯燥乏味的公文、雞零狗碎的絮語、空洞惡俗的說教,甚至搞笑低級的段子,都可以籠而統之地納入散文的范疇。隨著互聯網的發達,現代傳媒的普及在使“全民寫作”的口號完全落實的同時,也更加助長了散文的虛假繁榮。這時候,想必有人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傳統散文寫作的那種精神關懷的敬畏感,那種生命直覺的神圣性,怕是已經失落了;在眾聲喧嘩的話語狂歡中,散文似乎已經不再是“斯文人的談吐”了。
但我想,這樣的擔憂恐怕是有些過于悲觀了。盡管散文的世界不乏以次充好的贗鼎和魚目混珠的胡鬧,還是有一批懷抱利器的清醒的作者,在精心營構著各自的藝術王國,為散文這一“文雅”的藝術的復興而努力著。這中間的一位杰出者,是朱以撒。
朱以撒先生的散文寫作從一開始就顯露出了別樣的品格。從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古典幽夢》,到其后的《俯仰之間》、《紙上思量》,直至新近面世的第四部散文集《腕下消息》,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典雅而厚實的精神脈絡在其間貫穿著。這使朱先生的散文就是在諸多筆耕不輟的嚴肅散文家中間,也顯得十分卓爾不群。梁實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曾在其撰就的《論散文》一文中提出過“文調”這一影響深遠的概念,并指出:“文調就是那個人。”現在看來,同樣可以把這一論斷用在陳說朱以撒先生的散文藝術上,朱先生的散文,在初讀之下便可辨出是出自他的手筆,這種鮮明的藝術個性反映了一位作家的真正成熟。凡接觸到朱先生散文文本的讀者,無不能切實領受到一種久違的文雅氣息的感染,這感染必是深刻的。因為在朱先生文字的背后,是一位富有精神魅力的斯文人的形象。
其實,“文雅”也好,“斯文”也罷,均逃脫不了對生活地基的發現和對存在本身的洞察。在此基礎上發出寫作者自身屬己的獨特識見,方可能是有價值的。很難想象被冠之以“斯文人的談吐”的文字會是膚淺的常識和空洞的抒情的簡單疊加。一個明顯的例子也許是,保羅在《新約·提摩太后書》的結尾曾這樣囑咐提摩太:“我在特羅亞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正是建立在對日用常行觀照的本根之上的精神事實才顯示出它的可信度。同樣,朱以撒先生筆端所涉全是由自己日常生活中來,并不凌空蹈虛,最終又回歸到一己敏感而深沉的本心中去。這就使得朱先生的文本素材或許是平凡無奇的,而精神內蘊卻異常豐盈。這是考驗作家的表意能力和精神厚度的。針對一次再普通不過的飛行,他有這樣的思考:“一個人為即將到來的危險買單,真有前途未卜的無奈。”(《風中之翼》)面對外出開會的住宿問題,他想到:“文人就像刺猬,一個刺猬一個空間會好一些,兩只刺猬擠在一個空間里,身上又有隱形的刺,肯定會相互伸展。”(《城市流水》)更多的時候,朱先生將他的目光轉向生生不息的自然界,那時他的思索就更加素樸而動人:“獨立不行,也就使每一棵樹都充滿深深的宿命”;“那種生也簡單死也簡單,日子過得粗糙、樸實,是與山野的環境分不開的。”(《幽深的潮濕》)在《隔岸的花樹》中,朱先生由對岸難以企及的花樹生發開去,想到自己遠逝的二姨:“現在二姨已是隔岸的一名成員了,如果她是天河上的一顆星,那么是哪一顆呢?”——常常,在這樣的表達中間,朱先生筆下蘊蓄著的柔軟和溫情的內里就清晰起來。
朱先生由實實在在的生活出發,發抒襟抱,寫下了諸如《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被注視的時光》、《閑筆》等一系列直抵性靈的作品,展現了一位當代儒者的文化情懷和深邃思考。而朱先生另一類寫人憶舊的文字,如寫插隊生活中施工員老余的《悄然浸潤》、懷李萬鈞先生的《李先生》,尤其是那篇回憶導師俞元桂先生的《像潮水一樣漫過》,筆調沉郁,凡落墨處盡是一番深情貫注期間,使人掩卷之際,唏噓不已。然而,盡管筆涉過往,卻能哀而不傷,由此愈見其情之厚而大,絕非浮淺的小兒女之情所能比擬。朱先生向來是推崇魏晉風度的,浸淫既久,涵養亦深,一腔熱情、深情就從筆下自然流露了。
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于生活思考既深,于人事感懷又切,既有獨到的生命直覺,又不乏深摯的精神關懷,從而在智性上啟迪讀者,在感性上又打動讀者,使讀者得以在今天這個文化快餐充斥的環境中領略散文這一文體的健康成長狀態;更加之以醇厚優雅的語言,便使得朱以撒先生的散文有一種文雅的精神氣息流蕩其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斯文人的談吐”——這一點,我以為是朱以撒先生散文的獨特之處,是它可以傳之久遠的籌碼,也應該成為散文寫作的正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