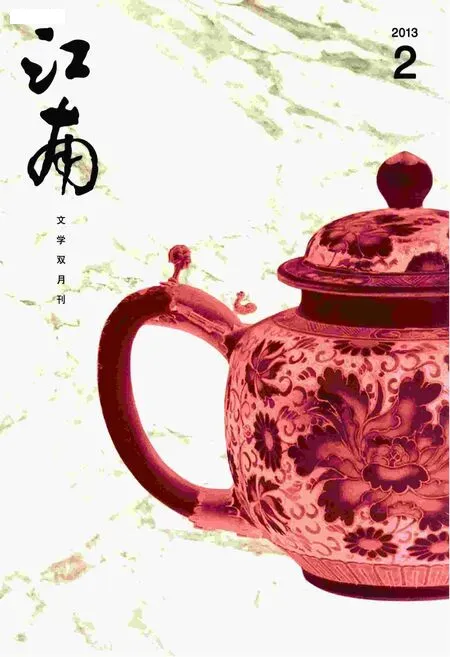水母潮
2013-11-16 18:39:20楊怡芬
江南
2013年2期
楊怡芬
我們坐在防波堤上。1985年的防波堤不是如今這般水泥鋼筋的堅硬模樣,只有一些些鋼筋一些些水泥隱藏在敦厚的水泥和青石之下,柔軟的防波堤上青草叢生,潔白的劍麻花開得熱熱鬧鬧。它不像是一道頂風抗浪的防線,更像是一條開滿劍麻花的小路。有事沒事,我們一撥人就愛到這堤上,悶悶坐著,看看海,吹吹風,心事就散了——多多少少,我們總有些心事的。
劍麻花和海水都在我們的腳下,海面平靜無波。一只漁船正朝外海開去,船眼睛遠遠地瞪著我們。前天剛刮過風暴,現在風停雨歇,正是啟航的好時候。船會開到福建啊山東啊那些地方的港口,船員們就下船到岸上去玩了。好多男同學長大了就是這樣生活,我們是不行的,島上從來沒有過女人去外海捕魚的,就是海島女民兵、女老大最流行的時候,我們島上也沒有哪個女人真去頂那半爿天,她們心甘情愿呆在島上織網補網。
“干女兒,到底是什么意思?”林英問我:“怎么大人們都那么眼紅阿虹呢?清林老師又干嗎要把阿虹當干女兒呢?”
“就像真的女兒那樣,可又不是真的。”林英的問題就是多。這有什么好問的啊,無非是能得些“實惠”唄。大人們是把“實惠”掛在嘴邊的。
“屁話。”
“那你倒說說看啊!”
可林英也說不出什么別的。
這個阿虹,她一直想跟我們好呢。前幾天她送了我一支藍色圓珠筆,送了林英一支紅的,可我們當著她的面就互換了一下。我說,我喜歡紅的。林英說,我知道。我們一起謝了阿虹。……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