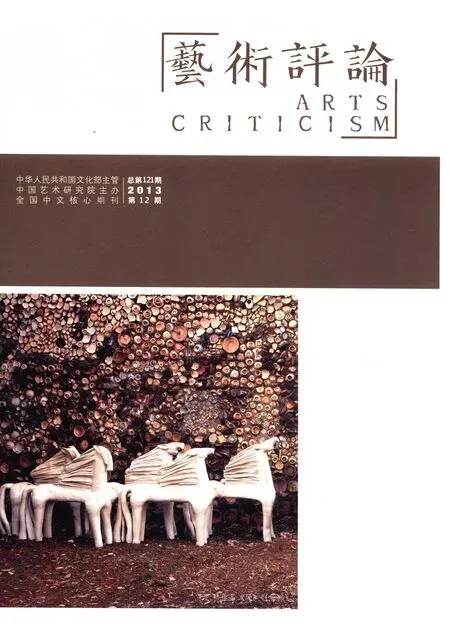以心靈為界
彭 俐
以心靈為界
彭 俐
對于文藝作品,文藝批評家們各有各的評價標準,各持一桿秤。以政治為標準看重立場,以經濟為標準盯著票房,以社會為標準膜拜觀眾,以藝術為標準技藝至上。因此,一個符合學術學理的藝術評價體系的建立成為必要。
以心靈為界,是本人揣摩的一個藝術作品評判準則,曾經屢試不爽。這是自己通過多年、多種門類藝術欣賞經驗的積累,以及從事藝術創作(詩歌、散文寫作)所悟出的一個藝術批評的真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心靈做砝碼來權衡藝術作品境界之高下,以心靈為界來劃定藝術作品情感之真偽,常常給我帶來意外的驚喜,頓覺耳聰目明。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大凡不出自作者心靈,且不為受眾心靈所動者,偽藝術也。無論是閱讀文學作品,還是傾聽音樂、觀看影視、戲劇、歌舞、繪畫、雕塑……每遇不能觸動自己心靈的作品,我會自覺不自覺地將其價值忽略,以匠人之器物視之,非我藝術族類之“成員”也。在此,藝術作品的創作者與觀賞者,二者動不動心,成為關鍵。
古人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心之為物,性靈所鐘,可做檢驗藝術作品的試金石。因為,藝術(創作)以心靈為始,藝術(欣賞)以心靈為終。藝術是始于心靈、抵達心靈的一個完滿過程。技藝可以迷惑感官,惟有藝術才能觸動心靈。在藝術評價體系中給心靈應有的位置,就是給藝術本身、給藝術家和受眾以應有的尊嚴。
以心靈為界,作為藝術評價的標準之一的理由,可以追溯到時間與空間上很遠的國度。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一書中,借其老師蘇格拉底之口,談到藝術作品潛移默化地熏陶心靈。他特別強調:“兒童階段文藝教育最關緊要。一個兒童從小受了好的教育,節奏與和諧浸入他的心靈深處,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有禮。”
亞里士多德與其老師柏拉圖一樣,在他的文藝批評著作《詩學》中,同樣強調心靈觀照現實與超越現實的主體意識與能動作用。他的模仿理論的核心主旨是:“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寫可能發生的事。”而這樣的事只能是作者心靈的產物。他說:“音樂的旋律和節奏同人心息息相通,會產生比普通快感更為崇高的體驗。”
同樣,中國古代文化先賢孔子關于文藝批評的發言,似乎只有三個字最為著名:“思無邪”。這是針對詩歌所言,也可以理解為對更寬泛意義上的文藝作品的評價尺度。后人又將“思無邪”分別解釋為“歸于正”或“不虛假”,而無論正與邪、真與假,都發乎心靈,亦關乎心靈。
與孔子同時代的莊子,其文藝美學觀念一如他天馬行空的美文風格,關鍵詞語是兩個字:“天籟”。他在《齊物論》中描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天籟”是“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發生于己,息止于己,發動者還有誰呢)?”我們今人不妨將“天籟”視為心聲。惟有發自心靈的聲音可與天地之響呼應。
世界上沒有比心靈天地更寬廣的一門藝術,也沒有比一門藝術更輕微的心靈。如果說人類的心靈是一個小宇宙的話,那么恐怕沒有比一顆心靈分量更重的藝術作品。倘若超出了心靈的邊界,那也就同時逾越了藝術的范圍,勢必會成為非心靈、非藝術之偽作。藝術與心靈之關系的重要性,是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的。
以心靈為界的批評觀點的支撐點,證據充足。明代文學家李贄,曾提出一種在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上振聾發聵的文學觀念,即“童心說”。他所言“童心”,非自然人的童心,乃社會人的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
再有,清代著有文藝批評集《隨園詩話》的詩人袁枚,在詩界倡導“性靈說”。他說:“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他是在說,心靈之外無詩。后代學人,認為袁枚的“性靈說”與南北朝時期劉勰文藝觀念一脈相承。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中說:“無識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清末民初國學大師、文學批評家王國維,曾創立詞界的“境界說”。他在其著述《人間詞話》中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而“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本人以為,其所謂“境界”,實乃心靈境界也。
世間一切事物都有界限,科學以頭腦為界,藝術以心靈為界。我們用頭腦分析科學問題,叫做動腦;我們用心靈感受藝術作品,叫做動心。這也是科學與藝術之間最大的區別。動腦的科學家相對理性、冷靜一些,而動心的藝術家則相對感性、熱情一些。以心靈為界,作為一種文藝批評的學術觀點,其理論根據有三:
首先,它是由藝術本身的屬性所決定;其次,它是由藝術家品性的重要性所決定;再其次,它是由藝術作品的特性和藝術作品受眾的天性所決定(即由他們的審美需要、情感需要與精神需要所決定)。
什么是藝術的屬性?打個比喻:藝術是“屬靈”之物。“屬靈”雖然是一個基督教名詞,但在這里卻非常適用。“屬靈”原是針對“屬肉體”而言,兩者形成對立關系,前者正可以引申為精神、意志、情感和思想所屬,引申為人類的“小宇宙(即心靈)”所屬。
進一步解釋,我們之所以說藝術是“屬靈”之物,還因為藝術的本質在于:它區別于“屬物”的一切物質。它雖然以“物”的形態出現,卻顯示“靈”的特征。它絕不局限或羈絆于物體本身,從而能從低層次的“欲界”上升到高層次的“靈界”,上升到情感與精神的層面,有時還能升華至形而上的境界。
“屬靈”之物不必高高在上,卻與人類的社會生活同行。但它的尊嚴與格調不容忽視。它可以用金錢兌換,卻不可用金錢衡量;它可以被權力利用,卻不可被權力驅遣;它可以讓受眾愉悅,卻不可讓受眾左右。
藝術家品性的重要性,系于藝術是“屬靈”之物。
藝術家品性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響藝術作品的品質。并由此,凸顯了藝術與心靈關系之密切。
“文如其人”,誠哉斯言!通常,我們考量一位藝術家的心性,也就是在考量這位藝術家的才能。法國雕塑家羅丹說:“藝術是教給人們真誠的一門功課。”中國有氣節的文人江天一說:“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恐怕沒有比從事藝術更要求從業者具有高尚人格與健全品性的職業了。對于藝術家來說,其心靈質地常常就是其作品質量,有什么樣的心靈質地,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藝術——優質或劣質一目了然。
正如劉勰所言:“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自古代屈子以降,司馬遷、陶淵明、阮籍、王羲之、杜甫、李白、白居易、蘇軾、歐陽修……直到近現代的梁啟超和魯迅……錦繡文章總伴以磊落胸懷,絕妙詩篇皆出自赤子肝膽,非至情至性之人不足以言翰墨,無光風霽月之情操更遑論藝術才華?人品與藝品互為表里,天性與天賦并駕齊驅。所謂“舞弄文墨,高下在心。”
倘若我們的藝術家、藝術工作者們個個品性端方,格調高雅,志趣不俗,社會上就不會出現那么多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藝術產品,不會被所謂“娛樂至死”的風潮所席卷。世界著名的美國的媒體文化研究者、批評家尼爾·波茲曼所著《娛樂至死》(及《童年的消逝》),指出一個觸目驚心的現象:“由于電視過分強調娛樂,使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娛樂至死的物種。”
波茲曼的主要觀點值得復述一下:“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讓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將文化變成一個娛樂至死的舞臺。”
正是如此,如果我們在文化傳播和文藝創作領域不呼吁以心靈為界,那么,我們就很有可能淪為監獄的囚徒,或娛樂至死的物種。這樣的結果,想想就讓人不寒而栗。
前面已經談到支撐以心靈為界的批評觀點的兩個依據:即藝術本身的屬性和藝術家品性的重要性,下面說說第三個依據——藝術作品的特性和藝術作品受眾的天性。
不難發現,藝術作品的特性和藝術作品受眾的天性兩者之間,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神交與默契。它們共同的特點,主要體現于三個要素或三個向度:
一是求真,二是向善,三是愛美。
目前,人類對于心靈的科學研究和解釋未見得完備,但是,還是認識到一個基本事實:心靈,是一個生命場,也是一個能量場。它蘊含著一個人的氣質、欲望和本能,也包含一個人的經驗、思考和判斷,同時,還兼具一個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
不可否認,人類較為健康、完善的心靈特性是——在信念上求真,在意志上向善,在情感上愛美,這一點,恰與追求真、善、美的藝術作品的特性保持一致。
我們相信,以心靈為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作品的評價標準和尺度,更是意在強調人類心靈生活的必要與重要。萬物之靈長的人類總不能舍棄心靈而做到“詩意的棲息”。
面對今天的一些文藝創作、文藝傳播領域的負面現象,我們深感憂慮,這也是提出“以心靈為界”批評準則的一個原因。我們親眼所見,市場上流行的許多文藝產品是沒有靈魂的制作,沒有靈魂的制作只能算作器物,不能稱其為作品。這樣的“產品”沒有血色,沒有靈魂,雖然能夠順利地進入商品流通領域,甚至賺得缽滿盆盈,卻最終不能進入人們的情感生活與精神世界。
事實上,任何成功的藝術作品的傳播過程,必由兩個部分組成:作用感官,深入心靈。作用感官容易,深入心靈很難。只完成前一部分,即“作用感官”的工程,是半截子工程,不算完工,只有同時將“深入心靈”的工程做好,才配稱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以心靈為界,千古有同調,且讀唐朝詩人常建《江上琴興》:“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讓我們以心靈為界吧,在藝術上如此,在生活中亦然。以心靈為界,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的內在情感、意志、精神和思想為本。
讓我們以心靈為界吧,讓心靈照耀的藝術永遠閃爍心靈之光!
彭 俐:北京日報高級記者、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