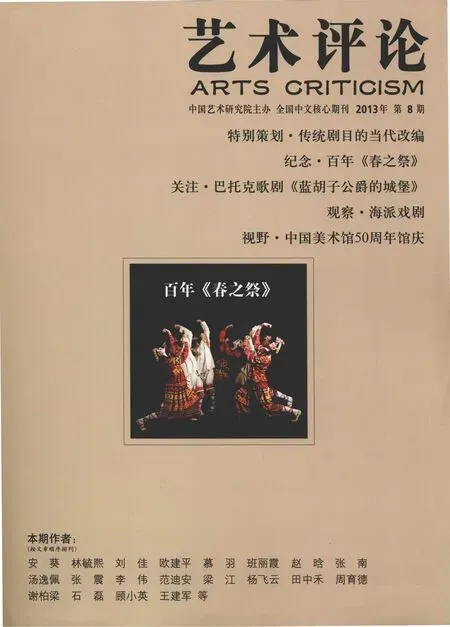目識心記:水墨創(chuàng)作談
佘 松
我的目光時常徘徊在物的表層,閱讀表層所能傳達的能指與所指,將主體納入缺席之境。表層的圖像化扭曲了具體的經驗,使我改變了原本來自生活的假想,轉而以一種缺乏鮮活的亢奮來體驗表層的意味。目光在此意味裹脅下,開始幻造各種場景,于是,繪畫成為一種游戲,或許就是貢布里希所指的那種嚴肅的游戲。
在圖像中把握玩味現(xiàn)實生活是我長期的志趣,利用材料自身的張力或缺陷來生發(fā)一種意象,營造主觀臆測的真實,不具體卻很能說明問題,就像南唐山水(董源、巨然、衛(wèi)賢之流)充分利用水墨的變幻表現(xiàn)真實意象。用寧靜的單純的手法(勾線的、賦色的)表現(xiàn)動態(tài)的日常記憶,將動著的一切靜于畫中。
我比較愿意從傳統(tǒng)水墨的角度來談論自己作品的意義,盡管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我的畫同水墨的關系問題。水墨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而我的畫是要放在大寫的水墨范疇中來討論的,我自知自己的畫有著濃厚的水墨情結,而且我也一直采用水墨思維來指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不僅如此,水墨方式作為一種文化思路已然成為我考慮問題的一種固有模式。眼下,我更愿意從材質的角度來對待傳統(tǒng)的筆墨紙硯,就像對待其他畫材一樣,不同的材質技法最終通過人的崇高的精神訴求是完全可以到達內心期望的彼岸的,所謂技進乎道吧。
我努力回避強勢筆墨所苛求的格式化的技法程式,轉而遷就一種個人意義上的語言方式。在尊重手繪快感的同時,強調畫面的制作效果。用色上仿效了敦煌壁畫的敷色特點,造型上經歷了一番中西結合式的拿捏揉搓,弱化了以線為主導的傳統(tǒng)架構模式,嘗試以重彩的方式應照與演繹隱含在日常生活表面之中的耐人尋味的“韻”,試圖打造一份洋涇浜式的文化場景中的純粹與荒唐。我就這樣長時間以一種不太劃算的方式呈現(xiàn)這些隨機拼湊的簡單而真實的生活,并以此與生活發(fā)生著或許同樣隨機的構合。這個舉動本身是刻意的,卻讓我感受到了某種異樣而尷尬的美麗,就像我們周遭隨處可見、觸手可得的生活那樣,充斥著有序又無序、簡單親切而又空虛乏味的圖像化的表面,置身其間,會產生一種不明真相時的不折不扣的快樂,有時候它甚至催發(fā)了意料之外且不可理喻的亢奮!我迷戀這些直觀的生活表面,喜歡它們莫名其妙的沖突,不厭其煩地渲染一種流于表面的意義,別無選擇地成為圖像世界的幸運看客和新鮮意義的杜撰人。
近期,我重又找回了在生活表面的體察中展開對自我內省的興趣,開始了某種自我表達的沖動,無可無不可的隨意性布局使我感受到“我自有我法”的慶幸,從而對石濤提出的“一畫論”產生適意的解讀。所謂“一”乃指統(tǒng)一協(xié)調,貫穿物我,思行合聚的繪畫狀態(tài)。從主觀感受經驗出發(fā),成就我法,以我法貫通眾法。這里包括兩個方向上的領悟,其一是對傳統(tǒng)經驗的領會,其二是自我對周遭日常經驗的把握,并經驗化,后者無疑是成就我法的重要基礎。這些感受不太可能直接來自日常生活,而是像從前那樣,多發(fā)自于對圖像文本的幻化處理。因為這些文本中已設置了足夠的情緒,我所要做的只是用我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情緒,將其中隱藏的不切實際的自慰的滿足感放大,令其虛幻化而變得不再可靠,然而,當你徜徉于美麗間,一切又歸于平常,畢竟,城市讓生活更美麗。
中國畫的筆墨是一個大的技法與文化體系。一幅畫內,山水樹石,花草人畜,屋宇亭閣,無不訴諸于筆墨,以筆墨的符號化狀態(tài),互為依存的展現(xiàn)。我以為,今日國畫,應將筆墨拓展至筆墨之外加以研究。其實,古人雖苛求于筆墨,然并非僅限于此,而古人似乎唯以筆墨論英雄的表象被歷史誤傳至今,卻忽視了由筆墨所傳達的至美境界才是真正經典,這一點可從元代經典作品中充分獲知。今人由于仍處在虛弱的筆墨現(xiàn)狀中,多通過古人遺留的經典筆墨去暢神筆墨之外的至美境界,由是觀今日諸多畫手喜將話語局限在談筆論墨的小圈子里實為一憾事,吳冠中先生曾提出“筆墨等于零”,恐怕也是出于此緣由,殊不知,文人精神也是與時俱進的!
關于材料的物質化。材料本就是一種物質,也就不應存在所謂物質化的材料,而對于顏色這樣一種供畫家描繪作品時必須使用的媒介來說,畫家往往容易忽略其存在的物質屬性,即顏色在作品中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客觀事實。我們似乎更愿意將顏色作為構成繪畫的元素之一加以接受,我們習慣于賞玩色彩構建的“樂章”。礦物色(現(xiàn)在流行叫巖彩)是繪制中國畫的一種畫材。礦物色具備其他種類顏色的功能,同時還彰顯了材料物質化的特性:材料自身的粗質感直接參與作品意蘊的構建。巖彩的繪制過程保留了傳統(tǒng)繪畫賦色的心平氣和的心理狀態(tài),三日一山,五日一水,平靜地觀想日常與無常,靜以制動,于動靜間傳達出文化在人心中的沖突,當沖突被呈現(xiàn)于畫面時,便形成了一種不同一般的務實的文化樣式,此即是關注材料物質化的意義所在,顧左右而言它,及他人所不及。其賦色過程使我們較好地避開了先入為主的具有歷史延續(xù)價值的主觀性,以一種通俗的近乎膚淺的手段營造富有新意而又不失文脈的個人語境。
盡管我花費相當精力在材質技法研究上,但我還是主張對于材質的發(fā)揮應是適可而止的,作品的立意與造型上的經營才是重要的。只有當我們將材質的意義化解為作品的意義時,那種技法上的炫耀才是可靠的,而材質確實具有魔法化的功能,比如中國畫千百年來的筆墨情結。其實,中國畫在材質上的理解與運用,從未脫離傳統(tǒng)筆墨精神的牽引,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束縛了材質效果的發(fā)揮,而換個角度看,任何一種材質,其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屬性,只有被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加以運用,才具有了相應的文化內涵,同理,不同的人對于材質的使用與理解也不盡相同。因此,在這里我仍要對材質的運用做些陳述。特定材質表達特殊意境,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而對于材質的認知方式,即所謂方法論的不同,直接影響我們對材質的運用與發(fā)揮,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材質不再只是一種惰性物質,而是積極參與到作品意義的構建中來。這就使我們無可避免地,要么按照大多數(shù)人的認識模式加以利用,要么以自己獨到的理解進行發(fā)揮。當我不止一次地發(fā)覺,礦物色這一媒材能在我的作品中協(xié)助我達成某種意境時,我便認識到材質對于繪畫的意義。這種極富張力和感染力的質料正好迎合了我對事物表面的關注。一旦它們被賦飾于作品表面,你便只能為它所動了。整個畫面的氣息會被瞬間拔起,進入另一個境界,而原先為作品鋪設的造型格局仍舊起著支撐的作用。
其實到后來畫著畫著,就畫成了一種概念,繪畫也就演變成了此種概念的物化,并在物化過程里實現(xiàn)著能指與所指的最佳銜接。所謂概念的物化,被我解讀為特定技術的形成,此種技術從不排除特定專業(yè)培訓而成的基本技能,但更側重于由于個人化的探索而產生的特定意義下的技術性話語。它是生發(fā)個人語境的必要條件,有時候,甚至技術本身就足以說明觀點,因為什么樣的態(tài)度最終導出什么樣的技術。技術的形成并不取決于神秘的發(fā)現(xiàn),更多時候是在一種歷史條件延續(xù)下的主動或被動的選擇,就像一個人堅定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一手炮制了自己的或喜或悲的命運一樣。
作為視覺的身體,只是由不同膚色傳遞出的某種身體幻象。在對這些幻象的讀取中產生了多重意義,我們衷情于這些意義繁雜的幻象,甚或忘卻身體自身。身體自身成為可資利用的修辭,一個可任意讀取的象征物,被隨意粘貼在任何我們需要的情境里。由各種意義組建起來的身體意象已然超越身體,取代身體。其帶有欺騙性的真實感從不間斷地干擾我們的判斷,致使原本無辜的身體已無法獲得清白,而我們只能經由一種不靠譜的意象化的身體認知經驗來把握自我,理解他人。如今,都市人都在努力學習一種分身術,為了將自己隨時從身體分離出去,過往的身體行為被鎖定在了過去那個自我意象符號中,此刻我已抽身出來,脫胎換骨,我還是我而又不再是我。就這樣,我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是否能叫做類似無痛分娩的過程。我們甚至喜歡上了這種迷幻式的自我認知途徑,它應該不疼且很舒服,盡管不靠譜。我們看似并不在意這物質的身體,卻反而更加依賴它。我們沉醉在各種身體寓言中,玩味著各式各樣的身體意象,人的或非人的,非人的,終究還是人的。繪畫似乎也從中找到了一種表現(xiàn)方式,集體的或個人的,終歸也還是身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