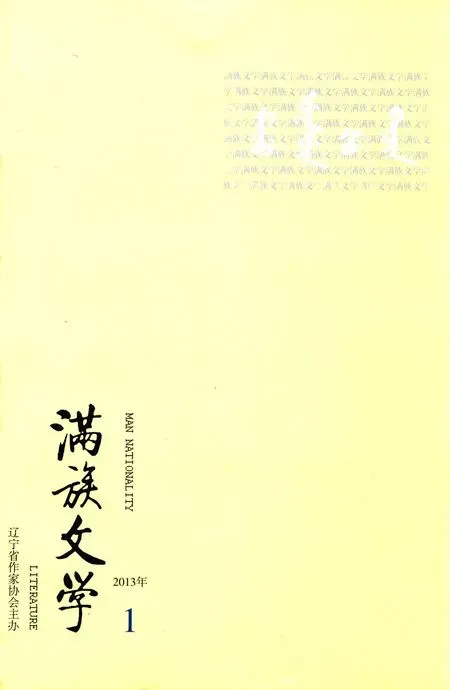書 后(外一篇)
〔滿族〕路 地
《夕陽秋葉》書后
一、自述編輯工作歷程
《我是文學編輯》,這是此前我的一篇文題。由此文題可見:我一生之從業是適意的。
我曾做過地工人員、文工團員、政府職員、部隊參謀等。一路走來,自覺做文學編輯,最足以發揮個人的才力。從業無憾,即志趣與職業相契合,決非輕易事。
為此,我感念幾位恩公。
1943年(14歲),在岫巖讀“國高”二年級時,有幸參加由愛國作家西琦(軍需中尉)主持的文學小組。在奴化教育苦境中,有良師忠言慈和入心,初收茅塞頓開之效。他曾嚴言告誡:“同學們,別忘了咱們是中國人!”偽滿時說這話是要殺頭的。老師的一句警語,終生銘刻于心。
1946年夏,從故鄉逃亡沈陽。但求學無門,大失所望。遂流浪街頭,以賣報維生。幸遇族叔傅茵波教授為我安排公費學校。昨日之盲流,今日之高中文科生,叔父之功也。
1947年,在沈陽讀高中時,幸遇作家鐵漢(郁其文),經他指點,遂有詩文初次發表。尤其在人生處于岔路口時,經他引導(與好友姜濤)參加我黨地下學聯,從此走上了革命路。
1956年,我在東北教育部工作時的一位處長張斐軍,調省文聯主事,我(業余作者)愿去,他愿留,遂調入《遼寧文藝》,從此踏上了可心順意的文學編輯之路。
1958年,在省作協《文學青年》(后為《鴨綠江》)當編輯,幸遇名作家、名主編柯夫,經他悉心調教,使自己逐步掌握了做省刊編輯的技能(見后文)。
1986年,創辦全國唯一的《滿族文學》時,幸遇國家高檢院原副檢察長關山復,是他第一個向我伸出援手,他又同邀名作家端木蕻良聯袂,立足北京,高屋建瓴地對刊物給予多方籌措;在遼寧又幸遇老領導、名作家馬加的關注,在省內上下悉心疏導;由這三位滿族尊長在京、沈通力指引,遂使《滿族文學》如日初升,且引起了廣泛的矚目。作為新刊物的第一任主編,得遇這“三老”為我辟路,實乃我此生之幸。
在省刊時期
1、刊物一般是“吃現成飯”,即邀作家的作品拿來發表。《文學青年》是“生米煮飯”,即從全國青年作者來稿中選優,致信提出意見,跟蹤修改,改成為止。主編柯夫的這一創舉,對提高編輯能力最為有效,我自感受益良多。我曾責編黑龍江作者的小說《一幅畫》,竟被茅盾選入全國青年小說選,東北只此一篇。1980年省作代會上,我是受表揚的四名編輯之一。
2、曾請遼寧大學中文系主任冉欲達好友助我制定“十年讀書規劃”,對中外古今名著、文論、文學史等較為系統閱讀,并做大量筆記。結合編輯實踐讀書,深得挑燈照路般的體悟。此規劃“文革”前基本完成。
3、一點教訓。當時政治運動較多,時常應邀寫詩配合,大約寫了幾十首詩。待編詩集時能收入的只有幾首,余者皆已枯萎,思之痛心。在新時期首次省作家座談會上,我說了“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存在弊端的話,當場受到了批判,也遭受一個時期有形無形的冷遇。我就這么硬挺著。1979年10月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致《說辭》中宣稱:取消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口號。我深感減壓之悅。新時期伊始,“我是從痛楚地總結教訓起步的,從揣摩文學規律起步的,從尋找真誠的‘自我’起步的。”(見拙文)頭腦清醒了許多。
在丹東時期
我有《關于丹東新時期文學起飛的記憶》一文發表。茲簡言之。
新時期伊始,廣大青年作者思文若渴、且在不辯方向之時,我們抓了三個字:“早”、“ 破”、“ 立”。 抓“ 早”字喻之為“ 搶墑播種”( 即抓住“最佳機遇期”)。抓“破”字即首先批判“四人幫”的幫風幫論,在“破”中求“立”。
1、1978年5月9日于省內率先創辦了《鴨綠江》文藝報,得以及時發表作者的新作,這是一種對迷蒙中學步者的引導。
2、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率先舉辦讀書創作班,批判“假大空”,倡導“創作從生活出發”,“請現實主義回來”。效果顯著。遼報曾給予報道。
3、上海《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發表小說《傷痕》,傷痕文學思潮從此興起。我們《鴨綠江》報于1978年6月6日發表小說《爆發》比前者早2個月。相繼發表:否定“文革”的《媽媽石》,質疑階級斗爭口號的《五更分二年》、《血染的紐扣》、《傻子與小姐》等,在省內外均為率先之舉。這是需要膽識的。
4、盡快健全編輯部。倡導3條:A做好本職工作;B多讀書多寫作品;C造就個人的正直人格。藝術上要逐步形成“重思想、重藝術、重探索、重韻味”的統一選稿標準。受到省內同行的鼓勵。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抓住關鍵的“最佳機遇期”,措施與方法得當,順應了文學發展規律,于80年代中,丹東文學出現騰飛的大好勢頭。省評論家李作祥撰文《丹東文學風景素描》,內言“令人刮目的丹東文學風景”,“居于全省文壇的顯要位置”。
在省、市委宣傳部通力領導下,經過6進沈陽、3進北京,將市級刊物《杜鵑》,改為省級刊物《滿族文學》,國內外公開發行。這是我國民族文學界的一件大事,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那時我已58歲,確有那么一股勁。1988年有人主張“承包”《滿族文學》。我未與茍同,遂于1988年8月離休。
我做編輯工作,已逾半個世紀。深知欲做好編輯工作要有文學理論的較深學養,要有敢于創新的膽識;要有愿為“做嫁”的奉獻精神。“我任主編,憑知識與業務能力工作,憑公心、正氣工作,多彎腰做事,少沾名利,注重團結,發揮大家的積極性。”(見拙文)文學編輯工作,是一種高尚的創造性的勞動,其成果有眼能見到的(書、刊),也有諸多用眼見不到的,但卻鑿實地參與了作家的創作。喜見作家成長,喜見文學繁榮,這是編輯的心愿。身為編輯確有值得終生珍記和回味的東西。曾獲丹東市政府首屆“園丁獎”,省作協首屆優秀會員獎“勤耕獎”,中國作協的“老編輯”榮譽獎,中國作協、中國文聯分別授予從文60年的榮譽證書和證章。1987年1月,被省第一批評定為編審(共25名)。對此我感到光榮。此前我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做編輯終生不悔》。確然。
謹以此書與同出的《鴨綠江吟(續)》為此生之文緣作結。
此文未了得詩一首《良朋》:
和煦風吹老樹搖,
春來望蕾夢迢迢。
良朋幸舀一瓢水,
果見枝頭結二桃。
二、簡言自己
我生有馬背上民族的性格,有了目標,即不避艱險,勇于奮斗。解放前,在沈陽讀書時,甘冒白色恐怖,參加了地下斗爭。建國后,申請參加朝鮮戰爭,誓為保衛祖國而戰,心存大愛。曾立功受獎。
我鐘愛我的民族。深知有清一代三百年,武功文治均達歷史上的新高度。(晚清因腐朽而滅亡,自是規律。封建王朝誰個不滅亡!)滿族是一個有作為的民族,作為其后裔,尤當自厲自強。
青年時代參加革命,頭十年換了五次工作,有如隨船執漿,涉水未深,少有體悟。五十年代中,有幸擇業成功,走上了稱心的編輯崗位。但因文藝政策存在“左”的束縛,有束手束腳之感。
新時期伊始,中央施行改革開放政策,如開一扇天窗,云散日出。經過對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之冥思苦索,喚來了頭腦之清醒。拙詩云:我是一棵“晚熟的稻子。”雖年近五十,晚熟畢竟“熟”了——
我曾直言“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存在弊端;曾率先發表否定“文革”、置疑階級斗爭口號的作品;曾率先以“我”為題寫詩沖破詩中無“我”的禁區;曾借故未參加“評《苦戀》”、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于是招來了有形無形的壓力,就這么硬頂著。后來一位前市級領導說:“看來路地那些主張還是對的。”謝啦!
新時期十年,是我在崗最后的十年,是檢驗我獨立能力的十年,是發揮個人才智的十年。自己既當船長又當水手,勉勵同事即當編輯又當作家,同舟共濟,將地處邊陲的刊物打造出一番大氣象。盡管國務院規定的干部休假一次未休,但自己收獲的是一種成就感。這是我生命自主的十年。
1988年離休。20余年來離休未離崗,共主編書籍16種,600余萬字,出版個人(業余作者)著作10種,200余萬字。這份成績在同齡者中當屬負重者。
我愿以誠交友,省內外有至友(文友、族友、戰友)幾十位,一生互不相忘,見面無話不談。拙詩云:“友情遠近如梅綻,時有暗香拂吾心”。
有真愛常存于心。愛寡母、愛姊妹、愛發妻、愛子孫、愛各種膚色的逆境中的兒童,也愛花草。喜古人詩句:“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
我一生拒穿西裝,不趕時尚,不羨豐財高位,不厭布衣素食。以84歲(屬龍)高齡仍在讀書、編寫中度日,自覺充實。
《鴨綠江吟(續)》書后——自說自詩
我愿說:“我是文學編輯。”從1956年起,一直做編輯工作。若說詩人,我是“業余”作者。共出詩集6種,詩集《淡淡的紫霧》獲國家級獎勵。但總體說:屬中等水平。茲簡述之。
一點詩緣。我的故鄉是四面環山的偏僻山村。接觸文化較難,我曾稱之為“故鄉的瘦文化”。卻有幸較早接觸了詩。讀小學二年級時,叔叔從外地帶回一本封面已殘的雜志,內有一首詩使我童蒙之心有點開竅,詩題《思念》:“你我天各一方,思念也長長。歲月悲涼,故人愁斷腸。但你我為何分手,也已說不清了……”詞語雖未全懂,卻有一絲苦味的詩思,叩敲著我幼小的心扉——既然彼此苦苦思念,為何不重新聚首?既然相愛深深,為何說不清分手原因?淺淺的詩愁,總懸于小小心頭長久不散。如此首結詩緣。
1943年在岫巖讀“國高”二年級時,我參加了愛國作家西琦(軍需中尉)主持的文學小組,學習寫詩,經他親切導引,似有初尋詩徑之感。他還為我取個筆名“嘯岫”,我雖未用,但卻是一種激勵。
1947年在沈陽讀高中時,幸遇作家鐵漢(郁其文),經他耐心點撥,遂有第一首詩《東方明》(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在報上發表。從此遂成為業余作者。
一點教訓。解放后,也試著寫了些個性化的詩,如《 筆》、《 兩只小船》、《 第三扇藍窗》等探索性的詩發表。經“反右”一沖,頓時化為烏有。從此迫使自己順應革命需求,以配合政治任務為榮,強自為詩。結果發表了不少詩,能收入詩集的只幾首,其余都已枯萎了。痛心不已!
文革十年,一首詩未寫。
新時期伊始,在一文中說:“我是從痛楚地總結教訓起步的,從揣摩文學規律起步的,從尋找真誠的‘自我’起步的。”
一次突破。建國后文壇已見繁榮。但也存在“左”的束縛。如:只能寫十七年,不能寫歷史;只能寫工農兵,不能寫知識分子;只能寫重大題材,不能寫家務事兒女情。而在詩壇,只能寫“大我”,不能寫“小我”。身居高位的著名詩人郭小川在《向困難進軍》、《致青年公民》等詩中,因為寫了“我”而受到批判。于是,“我”在詩壇“出缺”了,遂形成了一個禁區。
丙辰(1976)清明節為悼念周總理萬眾自發掀起“天安門詩抄”活動;新時期伊始,又掀起傷痕文學思潮、反思文學思潮,以此種種為先導,以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全國四次文代會鄧小平《祝辭》(取消文藝從屬于政治口號)為動力,逐步掀起全國性的思想解放熱潮。說“逐步掀起”,是說這過程不是輕易的。
我于1983年1月27日率先寫出一首詩《我》,作了一次勇者的突破:
《我》全詩103行,內有37個“我”出現(非刻意求多),而且有“硬分什么‘大我’‘小我’/我自始存在于統一里”的直言不諱詩句出現。
“我是文學編輯”,“為他人縫制嫁衣”,“人間有人需要我”,首唱知識分子的贊美詩。
“我是一個村一個屯/一個縣一個區……”,張揚了詩人的創造精神,張揚了共和國公民的主人翁意識。
“我決不卑鄙/依仗權勢營私舞弊……”先期鞭笞了社會的腐敗現象。
“我也并不圣潔”,“曾求過人情/送過薄禮……”對詩人自我靈魂的詰問,首見于詩。
當然,對抒情主人公——一個忠誠愛國者形象也予以贊揚:“可以向祖國訴說”:我“曾向心地環繞著你/曾以生命歌吟著你/一旦燃盡了應逝即逝/仍愿還你一塊小小的隕石”。
這首詩發表后,在遼寧詩壇掀起了一陣波瀾,贊聲不絕于耳,省外也有詩人來信贊許,可見詩人們都是人同此心的。
一個主張。我曾在一文中說:“要以文人的良心和勇氣”,“向人類思維的隙縫去尋覓小詩”,這主張是自己覓得的,即注重自我,注重多思(深思、哲思),注重寫小詩(9行短章)。
對此,多位詩友給予了諸多勉勵。阿紅說路地詩中“巍然聳立著‘我’”、張立群說:“路地在歷史的慣性尚未殆盡時率先張揚自我”;王科說:“他的純情都皴染了一層哲理的光環”;李萬慶說:“他的詩是一種精短凝煉的新唐人絕句”等,催我前行。
我一生寫詩700余首,無論成敗如何,我是這么踐行的。
我之所以成為“中不溜兒”詩人,是因為詩才不及;是因為對唐詩(世界詩歌史上的一個巔峰)精研不力,對漢語(世界語林中的一個奇妙語種)精研不力,自知其失也。
報載:1987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2010年中國作協舉辦的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向古體詩詞開門;2011年北京成立中華詩詞研究院,隸屬于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館,納入政府序列。中華詩詞有了座次,幸事。祝中國詩壇百花齊放,萬紫千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