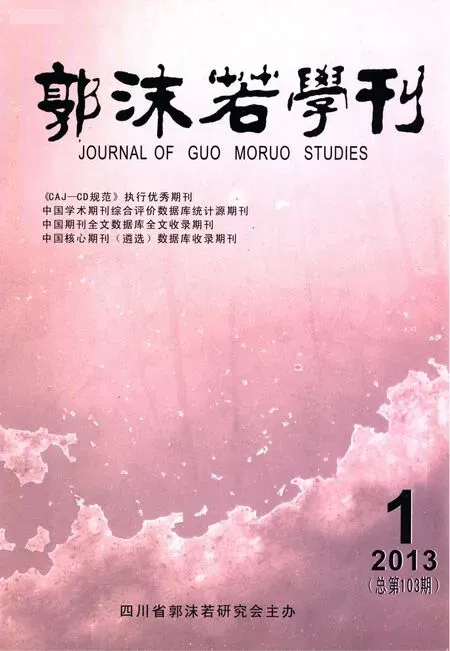郭沫若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述論
邱少明
(中共鐵道部黨校,北京 100088)
1938年11月,言行出版社初版發行了郭沫若于20年代末譯就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時的書名即《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當年翻譯時是用蘇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長李亞山諾夫(今譯為梁贊諾夫)主編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做底本的。郭沫若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內容涵蓋《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序言及第一章《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與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這為中國首次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德文原文做藍本的節譯之單行本。郭沫若版單行本的面世,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界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當時宣講普及唯物史觀起到了強力助推作用。要知道,我國至1960年以阿多拉茨基版為藍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翻譯出版發行之前,在這20多年的歷史階段中,郭沫若版單行本始終為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主導版本,中間歷經許多次的再版及翻印,比如,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47年3月將其再版發行,又分別于1949年4月、1950年7月和1950年9月出版發行第二、三、四版。
一、郭沫若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摘譯情況
(一)最早倡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開展文獻學研究
前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26年在梁贊諾夫的領導下,正式開始編輯著名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他們首次用德文原文登載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他們編輯原則和方法是把馬恩手稿的修改過程原封不動地排成鉛字,如實地回歸當初原貌。換言之,他們是將馬恩的每次修改、每次刪除的內容亦直切印于正文里。他們的該種編輯原則和方法對后世《費爾巴哈》章的編輯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郭沫若摘譯了《德意志觀念體系》的第一章(即《馬克思恩格斯論費爾巴哈》),他非常認同李亞山諾夫(今譯是梁贊諾夫)的編輯原則。郭沫若主張勘校學上的功夫,如果不去探究原稿本身則意義全無。他倡導以影印的形式發布原稿,用原稿做最終范本,把對功用、意蘊的決定權奉送原著者。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深知,編譯者的每個判讀均“不可能保其必無千慮之一失”。根據本人考證,郭沫若乃中國最早的開展《德意志意識形態》文獻學研究的專家。令人遺憾的是,他所竭力主張的把文本受眾帶回文本的編譯原則并未激起多大的社會回應。這的確與當時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不成熟和不科學關聯,與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元化闡釋模式關聯,與當時盛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分體系化關聯。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之文獻學研究,表現出“跟著走”傾向,即尾隨同一階段的世界主導版本亦步亦趨,但是自身并沒有建構“一種有獨立意義的重要版本”。上述狀況的深層誘因乃在于:我國根本無馬列主義原始文本,亦并沒有狠下大決心,投入大氣力,將所有文獻全都拷貝(copy),以獲得獨立而不依賴的文獻資料來源。在現代科技背景下,要實現這個目標,或許不是難于上青天,尤其是當下則更可實現。早于70多年之前,郭沫若便竭力主張讓讀者回歸原文本的文獻學研究路徑,今天看來,不能不說他具有的非凡的學術先覺力、前瞻力和預見性。
(二)對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之研究,郭沫若是集中凸顯于注釋之中
據我考證,郭沫若是用注釋之路徑首開中國《德意志意識形態》理論研究之先河。下面,本人就郭沫若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些注釋進行研究、考證和闡釋。
首先,郭沫若關于馬恩意識、觀念和物質關系的注釋,其原文為:
意識不外是意識著的存在,而人之存在即其實際的生活過程。假如在全部的觀念體系中人類與其諸關系就如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現著的,那嗎這個現象是從他們的歷史的生活過程發生出來,剛好就像網膜上的物像之顛轉是由于他們的直接的物理的生活過程。
經過自己的體悟,郭沫若版本的注解為:
物像在眼底本是倒立的,然由人之實際的經驗在腦識中復顛轉之而成正立。此處所說之“顛轉”(Umdrehung)即是腦識中之顛轉。以喻觀念本立足于物質之上,然由歷來的習慣反看成倒立。
自某種維度考量,馬克思上述論斷是其實踐生存論之經典話語。我們知道,傳統形而上學存在論是抽象存在論(即為超驗性的和實體性的),而馬克思實踐生存論目標為具體的人之實際生活過程,重視的、高揚的為生活過程之經驗直觀,其本真精神和理論特質是感性現實性。郭沫若指出,觀念原本是基于物質的上面,觀念于這里已經非擺脫人的現實生存之抽象性的“自我意識”,而應該為基于物質上方的“真正的知識”。毋庸置疑,傳統之習慣即指習慣的觀念論者的概念、范疇、宗教、思想等等實體意識。這些傳統的習慣不過為人之實際存在的顛轉或異在表征罷了。從一定維度考量,郭沫若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實踐生存論學說的析論,深度關聯于他早期翻譯之經典作品代表作《查拉圖司屈拉鈔》(現譯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作者為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正是尼采《查拉圖司屈拉鈔》里的存在論之精神,讓郭沫若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實踐生存論的領會更全面、更系統、更深刻。這種闡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實踐生存論之智慧之光,被后來鋪天蓋地的認識論詮釋所阻擋,即便在當下,也還是沒有被也些學者深刻體悟,這的確是一件歷史之缺憾。
其次,郭沫若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偶然性的闡釋,原文為:
人性的個人對于階級個人之差別,諸生活條件對于個人之偶然性,是隨著一個階級之出現才現出,那一個階級,其本身便是布爾佐亞汜之一生產品的。個人們相互間之競爭與戰斗把這種偶然性才作為偶然性而產出,而發展。所以在觀念中,個人們在布爾佐亞汜統治之下比以前更要自由,因為他們的諸生活條件是偶然的,而在實際上不消說他們是更不自由,因為更是隸屬于客體的勢力之下。
關于“偶然性”,郭沫若的注解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相反,在此可理解為不受制馭性。”本人認為,這是比較中肯的。在郭沫若的視閾里,在人類的文明史中,不管于奴隸社會抑或于封建社會,眾所周知,有一種情形是不靠個體人意志管控的必然性,該種情形為:世代相襲的個人身份地位及生活條件。于這個歷史時期,必然是這個面相:人處在人之束縛之中。時至資本主義統治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上升,導致前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帶有必然性的事物,此時又帶有了偶然性,換言之,人自人之約束下得以解放而實現自由。然而,收獲該種自由的代價和學費卻是致人落進物的桎梏里。因此,郭沫若主張,我們人類惟有于真正的共同體之環境里,每一名個體借助彼此幫扶和互相聯合,而且憑借這種幫扶和聯合重新管控和規整眾多“物的力量”,從而真正讓人類自己獲得發展之偶然性。
再次,郭沫若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對“向來的革命中營為之種別”的闡釋:
在一切向來的革命中營為之種別總是絲毫不減,所變的只是求這種營為之另一種分配,求把勞動從新另行分配于別人,共產主義的革命則不然,它是變革向來的營為之種別,要把勞動撤廢,要把階級之統治和著階級的本身一并揚棄,因為它是由一個階級所執行出來的,那在這個社會里面再說不上階級,不被認為階級,它是現社會內所有一切的階級,國民性等,之解消之表現。
在郭沫若看來,“即勞心勞力之別”。在這里,郭沫若用我國古代傳統文化里的思維方式、語言風格及精神資源來綜合與闡述馬克思恩格斯之階級思想,換言之,他是把馬克思恩格斯階級斗爭學說參照、比對和契合于我國生生不息的階級抗爭之光榮實踐傳統。在本人看來,嚴格說來,比對于馬克思恩格斯階級斗爭理論,我國傳統文化和古代思想里的“階級斗爭”話語,本質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假如我們尚沒有對二者開展嚴謹、深入、細致的學理探討與理論透析,便把雙方加以簡單地牽強附合地對照,非常容易導致誤解、曲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歷史事實亦反復證明了這個道理。
最后,《德意志意識形態》關于唯物主義論述為:
這種自我活動之基本形態自然是物質上的,而與其他一切精神上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緊相關聯。物質的生活之種種不同的形成,自然是始終依存于已發展了的諸多欲望,而且這些欲望之產生與其滿足本來便是一種歷史的過程,這種過程在羊犬之類是絕對沒有——斯迭訥(今譯為施蒂納)之反對人類的偏頗的主要論證——,不過羊犬在其現在的姿態之內不消說,但不是它們的本意,是一種歷史過程之產物。
郭沫若的注釋指出:
Stirmer于其所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論及人類向來標榜著理想,使命,當為等等以求精神的文化的欲望之滿足,乃沒卻自性,乃人類之墮落,反不如毫無理想之羊犬等之不失其本然云云。故此即針對其說而馭斥之。[1](P128)
在當時的歷史時期(即于上世紀30年代),不管是鮑亦爾(現譯成鮑威爾)抑或費爾巴哈還是斯迭訥(現譯成施蒂納),他們的文章作品均還沒有踏進國門,當時中國思想界、理論界關于所謂唯心之個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如何對立以及怎樣辨正“并不是很明了”。難能可貴的是,郭沫若將斯迭訥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序言翻譯出來,替當時思想界、理論界廓清唯心的個人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之邊界奉獻了文本依據和理論支撐。在注解中,郭沫若深刻而又鮮明地解讀了斯迭訥“唯一者”哲學抨擊所有普遍性范疇的錯誤性和迷惑性。換言之,郭沫若點明:斯迭訥用獨一無二的“唯一者”置換費爾巴哈的作為人抽象概念的“類”,從而亮出了他自己的所謂思想體系(即“唯一者”哲學)。然而,斯迭訥的所謂“唯一者”本質上仍舊為一類抽象之本體,因為,他的“唯一者”乃不受所有羈絆的、凌駕一切的、絕對自由之主體,乃世界之主宰、萬物之核心及真理之標則。概言之,在斯迭訥的視閾里,“唯一者”乃最高、最大、最全、最透之存在。郭沫若強調,在馬克思看來,惟有依據事物的具體實際面相以及變化、發展之狀況,方可真正做到認知和把握事物。所以,馬克思拒斥空談,竭力把哲學問題自思辨領域移轉至經驗的歷史領域。
二、郭沫若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摘譯之關涉因素
(一)密切關聯于當時文藝界關于文學新現實主義的論爭
眾所周知,馬恩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再強調必須基于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將人的意識視為無論何時都只能為被意識到了的存在,可是人們的存在卻是他們自身實際的現實生活歷程。郭沫若在論及文藝之現實主義時,尤其呼吁文藝之真實性。他一再聲明,現實主義并非單純的寫實主義,藝術的真實并非等同于現實的真實,必須深刻體悟到藝術之真實,其實較“現實的真實有時還要真實”。正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郭沫若深刻解讀了文藝的新現實主義,他竭力倡導文藝工作者,須自省,須自審,須改造,須沉入鄉村,須邁進工場,須契合億萬百姓,須體悟他們實際的生活、希冀、語言、習俗、內心、外形等,用來改造重塑自我的生活,將自我回歸至人民之本位。事實上確實如此,正是《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克思新哲學世界觀對郭沫若深度的浸潤、影響和引領,使他實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貫通,從而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事業作出了非常重大的歷史功獻。
同時,郭沫若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摘譯,密切關聯于那時文藝界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大討論。《德意志意識形態》指出,人們對現實的描述的真正知識只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流變的審視中提取出來的最一般結論的濃縮,我們根本無法寫出能夠解答每一歷史時代的通用藥方或萬能公式,并且假如其脫離了具體現實的歷史則無一點功用,其僅僅可對每一時代的個人現實生活之過程及活動中生發顯現。在文章里,郭沫若則主張世界萬物無不是進化的,世界各國的歷史均不原貌再現。每—時代無不具每—時代之樣式,所有已逝時代之樣式盡管為永不磨滅的典型亦不可能原貌再現。其原因就是由于產生其的“那個時代的一切條件是消失了”。郭沫若認為應該從中國現實的具體實際起步,大步邁進火熱現實生活的洪爐里,要自中國文藝遺產、“五四”新文藝遺產、外國文藝精華里萃取優良營養,可是一定要進行很好地消化,將眾多養分轉成自身的血、肉、骨等,進而新造出一種嶄新的新事物,正像蠶吃桑葉而吐絲,盡管同屬纖維,但是經歷了一道產生新東西的過程。從上可見,郭沫若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辯證唯物論的闡釋是十分精當的,他將辯證唯物論的真精神用之于民族形式的理論思考亦是非常成功的。實事求是地說,假如郭沫若沒有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研讀、摘譯、闡釋和宣講,就沒有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民族形式的深廣體悟,更沒有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現實實踐所達到的非凡成績。
(二)密切關聯于當時文藝界對馬克思主義人民大眾的文藝觀之學術辯論
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認為人為能動的有理想旨趣的“現實的個人”,并且強調,恰是這樣的“個人”書寫了人類自身的歷史,恰是這樣的“個人”建構了“市民社會”,恰是“市民社會”所進行的“現實的運動”,才把人類社會體現為一段自然的、歷史的發展嬗變進程。馬恩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主張,一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它既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亦為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盡管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愈發帶有普遍性樣態,而且將它本身形容為唯一的合理性、具普遍價值之思想。然而,實際上,一個社會中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只不過為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于觀念上的表征體露罷了,只不過為用思想的樣態展示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罷了。
郭沫若當時認為,伴隨階級的產生,人類社會產生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每個階級社會里,統治者的思想肯定要統領當時社會。每個階級社會里的統治者肯定要借助涵蓋文藝于內的每個抓手來服務自身實際利益。毋庸置疑,人民的文藝本歸于人民,然而統治者卻經常借助它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使其改變了性質”。非常清楚,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文藝觀鮮明展示了辯證唯物論之哲學精神特質。完全能夠這么說,正是郭沫若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研讀、翻譯和把握,體悟了辯證唯物論的真精神,進而精準地解讀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即他所倡導的人民為本位思想)。
本人認為,郭沫若借助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更加豐富、充實及提升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素養。全民抗戰時期,郭沫若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用歷史劇及史論做載體,高舉起一面抗戰文化的燦爛大旗而聲名顯赫。在當時,立于時代思想巔峰之上的郭沫若,靈活應用他于翻譯馬列文獻時所掌握的唯物史觀之理論、方法和原則,并與抗戰具體現實相契合,先后創作了6部著名的歷史劇(即《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膽》《高漸離》《南冠草》)。這6部著名的歷史劇,不僅為郭沫若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上的一個巔峰,而且時至今日,大家于歷史劇的創作上,就創作量之多、現實性之強、知名度之廣和技巧性之高來講,“還沒有出其右者”。抗戰之中,郭沫若又重新拾筆來繼續一度暫停的學術研究,繼他于東瀛10年創造性地用唯物史觀探究我國古代社會性質及古文字學之后,又以其深透把握的唯物史觀進一步專心研讀我國古代歷史及先秦諸子百家。他陸續撰就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銅時代》《歷史人物》與《十批判書》等名篇佳作……這既為馬列史學的豐碩成果,亦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碩成果。
(三)深度契合當時如火如荼的抗戰現實社會實際
郭沫若當時基于抗戰的具體現實的迫切訴求,應對、解決了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新期待、新目標及新任務。我們深知,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社會實情的深廣劇變,中華民族被逼到了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因此,從文化維度考量,之前全部的本位文化或一律歐化的那些空洞論爭和抽象言辭,必須立即將它們拋到九霄云外。當時文化領域里,深受歡迎和震撼人心的,乃抗日言論、抗日電影、抗日詩歌、抗日書籍、抗日歌曲、抗日戲劇、抗日評書、抗日漫畫、抗日木刻等所有于抗日斗爭過程激發人心之精神活動。于當時歷史階段,最受拒斥、最遭唾棄的乃抗戰之前風靡一世的搞笑情趣及庸俗媚俗之“‘反差不多’運動的那種潮流”。這一時期,激情四射的郭沫若竭力倡導,抗戰文化的目標指向和實踐,要求不一定須高深、復雜、卓越和陽春白雪,但一定須深具感染力、親和力、戰斗力和通俗易懂。換言之,抗戰文化工作亟需充分的大眾化、通俗化、群眾化,特別要做到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這里,我們清晰可見,郭沫若之抗戰文化闡釋即對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告誡讀者應立足于社會現實而不是“由觀念去說明現實,是由物質的現實去說明觀念構成”的精準實踐詮釋。毋庸置疑,抗戰文化深植于當時具體的對日斗爭現實,抗戰救亡圖存之急切實踐訴求。而且我國傳統文化心理中強調實際、實用、現實而鄙視空談、抽象、無用的特質,建構了我國抗戰文化的群眾性、實用性、通俗性、感染性與鼓動性。正像馬克思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所告誡的,一個國家中理論的實現之程度,從來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郭沫若關于抗戰文化的思想原則絕非脫離具體實際的虛無縹緲的玄思妙想,而是深深根植于當時國情實際之“真正的知識”。完全可以說,抗戰文化確為抗日戰爭時期“時代精神的精華”。本人大膽假設,郭沫若假如沒有研讀、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而透徹體悟馬恩歷史唯物主義之精神內蘊,那么他一定不可能變成歷史時代之弄潮兒,進而為助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重要歷史功獻。
三、郭沫若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歷史評價
必須強調,在我國長達22年(自1938年11月至1960年11月)的歷史時期之內,郭沫若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摘譯本始終為我國各地《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主導性權威性版本。應該承認,這對我國唯物史觀的認知、宣傳和普及起到了有力促進的積極作用。不過,囿于時代條件、歷史因素等,郭沫若版本亦具有若干局限性。第一,郭沫若節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摘譯本在我國承受了和其底本梁贊諾夫所輯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在前蘇聯一樣待遇,即一直未被列進經典著作領域,一直未獲取和自身所含思想相稱的青睞。應該指出,郭沫若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摘譯本,作為學術性特別嚴謹的經典范本,于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思想群眾化和哲學大眾化的時代主旋律,億萬工人群眾的特定受眾目標,這就必然決定了要被束之高閣而備受冷落的歷史必然性。憑心而論,與其講郭沫若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生不逢時,倒不如講是國家、歷史和人民交付承接者以更重、更多的學術求索及學術使命。第二,郭沫若摘譯《德意志意識形態》,其本初動因乃替現實的、急切的馬列主義在我國的具體實踐提供行動指南和理論支撐。所以,郭沫若摘譯時,缺乏時間、來不急對文獻進行仔細研讀、消化、汲取及內化,因而,不管是于原著體悟抑或于詞句考證還是于本真精神的闡釋上均存有若干謬誤。不過,話說回來,大家不可苛求前人,因為,對于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樣一部晦澀深奧的經典著作,欲真正做到全面、完整、系統、深入和精準的體悟,確實非常之艱難。第三,我們知道,郭沫若的版本并非前蘇聯梁贊諾夫《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之全譯本。郭沫若不但沒有翻譯出梁贊諾夫原先于導言之后撰寫的特別關鍵的一文(即“原始手稿與文本編輯工作”),而且又非常隨意、自拿主意地刪除了若干他以為的“無關宏旨的文字和注釋”。必須指出,在翻譯工作中這樣的不全面、不完整性及隨意性,非常不利于當時讀者乃至后人全面、準確地領會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流變和心路歷程之真實歷史軌跡,容易引起大家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內蘊藏闡釋的簡單化和相對性。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譯介進國門,馬上便被應用至當時具體的各項實踐中去,來彰顯發揮其“改造世界”之重要威力,卻缺乏一個必要的較長時間的咀嚼、消化、汲取和內化的研究歷程。不過,郭沫若此時翻譯《德意志意識形態》,不是僅僅地就翻譯來翻譯,而是把翻譯和研究相交融、相貫通。
[1]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譯)[M].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
[2]王東.馬克思學新奠基:馬克思哲學新解讀的方法論導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4]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J].王訓昭,盧正言.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5]文天行.郭沫若抗戰時期的文藝思想[J].郭沫若研究學會(樂山),重慶地區中國抗戰文藝研究會.抗戰時期的郭沫若[C].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6]譚洛非.抗戰時期的郭沫若[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7]郭沫若.抗戰與文化[J].王訓昭,盧正言.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8]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譯)[M].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大衛·梁贊諾夫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夏凡譯)[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