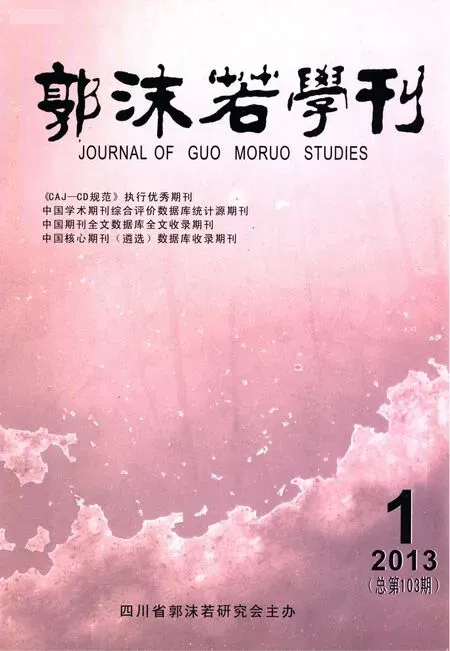關于郭沫若對呂不韋的評價問題
楊勝寬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郭沫若對呂不韋產生研究興趣,完全出于偶然的因素。他在《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中引述了1943年9月13日的一段日記:
讀《呂氏春秋》,初意欲收集關于惠施之材料,忽爾意動,欲寫《呂不韋與秦始皇》,寫二人之斗爭。呂不韋當為一非凡人物,漢人名之為“雜家”,其實彼具有集大成之野心,儒、道、墨、法,冶于一爐。細心考之,必有所得。
接下來的幾天,他反復閱讀了《呂氏春秋》,分門別類摘錄相關資料,從9月25日開始撰寫《呂不韋與秦始皇》(后名《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至10月13日完成,得4萬余字,用了半個多月時間,算是寫得比較順手的。
在《后記》中,郭沫若還提及10月13日讀到時人程憬的《秦代政治之研究》,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評語:“程文歌頌嬴政,有意阿世,意見與余正反,毫無新鮮資料。”因為嚴詞批評《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存“阿世”之意,遂留給人們郭沫若作《呂不韋與秦始皇》是為了“刺世”的印象,即認為他罵秦始皇,是為了罵蔣介石,反對秦始皇的獨裁專制,意在諷刺批判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如果按照郭沫若《后記》的敘述,他研究《呂氏春秋》出于偶然,他評說呂不韋與秦始皇的斗爭的思路,原在閱讀《秦代政治之研究》之前,郭沫若在研究中體現反對獨裁專制的思想,那也不是因一時一事、一人一文而起,而是與他一貫的思想原則和歷史評價準則相一致的。
一、關于對呂不韋其人其書的評價
關于呂不韋其人,郭沫若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的第一、二兩個部分作了介紹和辨析。從他的日記看,郭沫若對呂不韋了解和評價的切入點,是他與秦王贏政的斗爭,《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開篇明義即言:“呂不韋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是一位有數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殺,在他死后又為一些莫須有的事跡所掩蓋。”“被迫害”“莫須有”云云,這些定性言辭已經清楚透露了郭沫若對呂不韋和秦始皇的愛憎傾向。
從郭沫若的史料辨析中更可以清楚看出這種評價傾向。關于呂不韋生平的記載,現在可見的正史主要是司馬遷的《史記》,但郭沫若認為《史記》的說法“自相矛盾”,“信筆敷衍”,其間的故事敘述幾乎類似于明清時代“蹩腳的小說”情節,總之是相當不可信的。特別是關于嬴政的出生問題,《史記·呂不韋列傳》云:
呂不韋取(娶)邯鄲諸姬絕好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子楚是在趙國作人質的秦公子)從不韋飲,見而說(悅)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為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對于這段史料,郭沫若羅列了三條反駁的理由,否定嬴政是呂不韋私生子的說法,包括未見其他史籍有類似記載,故事與春生君和女環的故事情節類似,以及《史記》記載本身的矛盾。關于最后一點,郭沫若舉出了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司馬遷既說嬴政的母親是邯鄲歌姬,下文又說子楚夫人為趙豪家女,兩說顯得自相矛盾;二是子楚夫人“大期”生子,是正常的,不存在與呂不韋“先有身”的問題。郭沫若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不可信的傳說是從哪里產生,以及炮制這種傳說的動機所在。在列舉了明清時代學者的觀點之后,他提出,傳說產生于西漢呂后“稱制”時的呂產、呂祿輩,目的是為呂氏篡劉尋找合理依據。對于這一說法,郭沫若自己也承認,僅是沒有史料根據的“一種揣測”。
嬴政是不是呂不韋的私生子,由于史料的缺乏,不管是相信者還是否定者,都沒有十分堅實有力的證據加以證明。早在司馬遷時代就難以搞清楚的歷史問題,二千多年以后的研究者還想搞清楚,事實上是幾乎不可能的。況且秦始皇是不是呂不韋的私生子,并不影響人們對兩人歷史功過得失的應有評價。只是如果要衡量郭沫若否定《史記》的論據,其實并不很有力,子楚的夫人是趙豪家女,跟他在呂不韋的家宴上看上邯鄲歌姬,兩者不存在根本矛盾,歷史上已有家室而在外面與歌姬廝混的人和事不勝枚舉,況且司馬遷還記載了嬴政即位以后呂不韋與太后“時時竊私通”,似乎兩人私情由來已久,且一直未斷;說子楚與邯鄲歌姬“大期”生子,也難以根本否定嬴政是呂不韋私生子的說法,“大期”而生的時限,古人就有十二個月和十個月等種種說法,司馬遷特別說明嬴政的母親及“大期”乃生,意在提示其非正常孕育,以印證“姬先有身”的事實,故司馬貞《史記索引》引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逾常期也。”
呂不韋早年生平的許多經歷已經沒有記錄,讓后人印象深刻的典型事例是他對為質于趙的秦庶公子子楚的一連串成功運作,留下了“奇貨可居”的著名典故,這充分反映了作為商人的呂不韋,超出常人的政治眼光、經營頭腦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價值理念。《戰國策·秦策四》:
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何?”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愿往事之。”
經過與父親的商量權衡和仔細盤算,呂不韋決心著手實施他的冒險計劃,投入巨資,精心策劃,在趙國和秦國兩方游說,特別是說服后來成為孝文王皇后的華陽夫人,由于她沒有生育,呂不韋曉之以利害,讓她收子楚為子,孝文王繼位后又成功將之立為太子,一年多后,子楚即位為秦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由質子得登帝位,自然對呂不韋感激不盡,于是任命他作了秦國的相國,封文信侯,食邑十萬戶,呂不韋最初的目標到此圓滿實現。
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呂不韋身上的許多性格特征,既可以說他是有眼光和遠見的政治家,也可以說他為了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既可以說他是為實現政治謀略而堅韌不拔、運籌帷幄的戰略家,也可以他是為了實現政治野心而處心積慮、手腕高明的陰謀家……總之,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復雜的多面人。郭沫若則更多地看到了體現在他身上的進步、積極的正面。無論其與嫪毐的權力之爭,還是其與秦始皇的政治紛爭(詳后),都體現了郭沫若的這種評價態度。
關于《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郭沫若根據該書的《序意》所言“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認為其成書時間為秦始皇八年(前239),“草創當在六七年時”。但關于此書撰成的時間問題,歷來有不同說法,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撰成于秦始皇即位六年,所謂秦八年,乃是從莊襄王滅東周之年起計算,比如長期研究《呂氏春秋》的現代學者陳奇猷即主此說,他在《〈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一文中說:“依太歲紀年,‘涒灘’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戌’,不是‘申’,所以太歲紀年與干支紀年不一致,則‘秦八年’認為是始皇即位八年之說有必要重新考慮。清孫星衍就此作過考訂,‘考秦莊襄王滅周后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為涒灘,呂不韋指為是年。’這就是說,所謂秦八年,應該從莊襄王滅東周的第二年癸丑(前248)起算。’孫氏此說極正確。”并且從《呂氏春秋》一書體現的陰陽五行觀念來解釋秦從滅周算起的理由,似有相當說服力。
呂不韋撰述《呂氏春秋》的動機是什么?《呂氏春秋·序意》述呂不韋之言曰: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其意圖十分清楚,就是要為剛剛建立起來的統一政權提供理論指導與合理依據,希望“為民父母”的統治者,要法天地、審人事,遵循客觀規律,認真吸取治亂存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明辨是非,順應人心,實現“清世”的治理目標。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為此書的撰述動機提供的解釋則云: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生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遍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司馬遷的上述記載,說明了此書集眾人之手而成的論著性質,和匯集各種思想歸于一書的“雜家”性質,揭示了當時天下辯士爭相著書立說、為新生統治政權提供理論支持的思想背景。郭沫若批評司馬遷把呂不韋撰述此書的目的部分地庸俗化了,認為呂不韋不只是為了與列國公子比拼,滿足虛榮心理,實際上呂不韋的創作意圖要深刻高遠得多。他對《呂氏春秋》作了如下總體評價:
你可以發覺著它并不“雜”,它是有一定的權衡,有嚴正的去取。在大體上它是折衷著道家與儒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尊重理性,而對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棄的。它采取著道家的衛生的教條,遵守著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理論,行夏時,重德政,隆禮樂,敦詩書,而反對著墨家的非樂非攻,法家的嚴刑峻罰,名家的詭辯茍察。它主張君主無為,并鼓吹著儒家的禪讓說,和“傳子孫,業萬世”的觀念根本不相容。
《呂氏春秋》“雜取”百家之說,以儒、道思想為主導,反對墨、法,提倡德政、禮樂、詩書那一套儒家道德人倫學說,與秦始皇的推崇法家的思想觀念和施政綱領迥然有異。依照郭沫若的說法,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就出現了:照理說,作為很有政治謀略、經商起家的呂不韋,又被秦始皇尊為“仲父”,他應該遵循當代皇帝的治國理念來著書立說,這樣于國于己都是最有利的選擇。顯然,《呂氏春秋》的思想主旨與編撰意圖并非如此。那么,呂不韋為什么要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初撰述此書,其用意究竟何在?它的出現對呂不韋的命運,以及中國以后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什么影響?就是值得深究并作出解答的問題了。
二、呂不韋的思想傾向與《呂氏春秋》的思想內容
呂不韋的主要思想傾向是什么?這是學術界較少注意的問題。歷來評說《呂氏春秋》一書者,幾乎沒有單獨考察過呂氏個人的思想傾向,而簡單地把《呂氏春秋》的思想當作呂不韋本人的思想。眾所周知,《呂氏春秋》乃呂不韋集眾門客撰述而成,其思想內容之“龐雜”,正因此故。顯然,《呂氏春秋》的思想內容,不能簡單等同于呂不韋個人的思想,因為此書是集眾說而成,反映了戰國末年匯集于呂氏門下諸子百家學者的復雜思想觀念;同時,呂不韋作為此書的策劃者與編撰者,他有著非常明確的編撰意圖和主導思想,弄清呂不韋的思想傾向,對于研究《呂氏春秋》意義重大。
由于資料匱乏,呂不韋的思想觀念與相秦的施政舉措,難知其詳,幸《呂氏春秋·序意》保存的一段話,可以大略了解其主要思想傾向。所謂“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四句,據清代學者俞樾說,為黃帝誨顓頊之言,意謂能夠上法天,下法地的人,才能君臨天下,為民父母。呂不韋說:“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說明其撰述《十二紀》,希望包括秦始皇在內的讀者,通過此書可以了解歷史的治亂興衰,命運的壽夭吉兇,只有遵循天地、人倫的規律,才能使世間道理明白、是非昭彰。其不稱《呂氏春秋》而言《十二紀》者,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的《十二紀》《八覽》《六論》,當時是各自獨立的,而《十二紀》先成,呂氏將它布于咸陽市門,懸賞千金求一字之增損者,正是這一部分,而《八覽》《六論》乃后來陸續撰成。為了進一步闡述國家的治理必須遵循天地運行的客觀規律,呂不韋進一步闡釋云: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而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這段話可能在文字上有脫誤或者錯訛,理解起來比較艱澀難懂,但基本意思是清楚的,它重在申述黃帝教誨顓頊四語的深刻含義,強調人世間的運行發展,必須與自然規律相一致,不能違背客觀法則。老子講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者,取法、效法之意。只要順應自然法則,按照客觀規律行事,君王治理國家就是十分簡單和容易的事情;同時,尊重法則與規律,意味著不能用一己之私去隨意改變,私視、私聽、私慮橫行,公道、法則、規律就無用了,長此以往,社會就會亂套,國家就會衰亡。《易·系辭下》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統治國家的“大人”,能夠順應天意,順應神靈,也就是順應人心。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清楚了呂不韋說的一大段話的主要含義與用意,重在強調國家治理應該敬畏天意與人心,尊重自然法則和客觀規律,克服私心,明辨是非,彰顯公理;要善于借鑒歷史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趨利避害,努力使國家保持安定祥和,興旺發達。其立意不可謂不深遠,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特別是身為“仲父”,希望通過編撰此書,讓年輕氣盛的新君主嬴政懂得怎樣治理好國家的道理與方法。
呂不韋的這些思想觀念,顯然源于黃老,而摻雜有“陰陽家言”。《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呂不韋編撰《十二紀》,紀歷史的治亂存亡,希望為人君者從中知道禍福吉兇之所由,懂得“君人南面之術”和“為人父母”的方法和途徑,其思想與道家學說最為接近。《漢書·藝文志》述陰陽家云:“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羲和之官”乃古代掌管天文、制定歷法的官職,其職責是依據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制定歷法,便于老百姓根據四時節令,安排耕種勞作。由于中國古代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生產是立國之本,所以,國家的治亂興衰,很大程度上系于農業的發展,靠天吃飯,順時而為,祈望蒼天風調雨順,不違背時令節序規律,的確是治理國家的頭等大事。由此不難看出,呂不韋講重視歷史的存亡興衰經驗教訓也好,講敬順天時、尊重自然規律也好,其意都在于為嬴政提供治國理政的指導原則,希望他履行好“為民父母”的神圣職責。
呂不韋的這番良苦用心,似乎嬴政并不買賬。而且《呂氏春秋》公布以后,直接激化了秦始皇與這位權勢日盛的輔國者的矛盾,導致了呂不韋被疏遠和被遷謫的一系列嚴重后果。郭沫若認為:“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與政見上,都完全立于兩絕端”,指出了矛盾的根源所在。
關于《呂氏春秋》一書的主要思想,歷來研究者有不同的說法。東漢注者高誘最早對全書的思想內容作出概括:“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里也。”按照高誘自己的說法,“道德”“忠義”體現的是儒家的思想觀念,“無為”體現的是黃老的思想觀念,“公方”可能兼有儒、法兩家的思想觀念。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解,《呂氏春秋》雜取各家思想的特征比較顯著;但所謂“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里”,似乎又突出強調了儒家的思想色彩,淡化了道、法諸家的思想成分。高誘的看法對后世的研究者具有深遠影響,包括在郭沫若的研究中也可看出。對此,現代學者陳奇猷在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不同觀點,指出:“《呂氏春秋》雖說是雜家,集各家各派之說而成,但細讀全書,很自然地會注意到,陰陽家的學說是全書的重點,這從書中陰陽說所據的地位與篇章的多寡可以證明。在位置上,陰陽說安排在首位,數量上則陰陽說占有最多的篇章。請看,《十二紀》每紀的首篇就是陰陽家說,《八覽》的首覽首篇《有始》、《六論》的首論首篇《開春》也是陰陽家說,正如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一樣,陰陽家說占據書中重要的位置……凡此諸證,都很有力地證明呂不韋的主導思想是陰陽家之學。”陳說甚辯,為研究者觀照該書思想內容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與評價方法。但用《呂氏春秋》一書的主導思想證明呂不韋的主導思想就是陰陽家之學,是不夠嚴謹的;況且把《序意》所引呂不韋的話認定為全是“陰陽家言”,有將黃老學說與陰陽家學說混為一談之嫌,也不盡合理。
郭沫若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從第四部分開始,對《呂氏春秋》一書的思想內容展開了深入分析,涉及宇宙觀、人生觀、政治主張、德政思想等方面,下面擇要進行梳理評析。
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的第四部分,郭沫若開章明義是要分析《呂氏春秋》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但其內容幾乎全部都是闡述宇宙觀,只在本部分行將結束的時候,引述了《恃君覽·恃君》的一段話,證明其社會進化觀“合乎實際”,完全沒有涉及人生觀方面的內容。
所謂宇宙觀,是對于宇宙的形成、運行、變化等問題的基本看法。郭沫若認為《呂氏春秋》的宇宙觀,折衷了道家與儒家的思想。《孟夏紀·大樂》云:“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郭沫若說,這里的“太一”,與《道德經》的“道”、《易傳》的“太極”十分相似,《易傳》所說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對宇宙起源與生成方式的解釋,跟《孟夏紀·大樂》的意思大同小異。“太一”,亦即《季春紀·圜道》所說的“精氣”,宇宙的運行變化,萬物的生成變滅,就是這種精氣在發生作用:“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并且不惟自然萬物的運行規律如此,人世社會的運行秩序也是這樣:“主執圜,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郭沫若指出,《呂氏春秋》所言的“精氣”,又與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氣”一脈相通,至于為什么能夠相通,郭沫若沒有具體闡發。但當分析《呂氏春秋》的“五行相勝”與“五德終始”的觀念時,郭沫若詳細論證了它與《禮記·月令》、子思及孟子的類似思想觀念的密切聯系。郭沫若闡述五行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源時說:“在神權思想動搖了的時代,學者不滿足于萬物為神所造的那種陳腐的觀念,故爾有無神論的出現,有太一陰陽等新觀念的產生。對這新的觀念猶嫌其籠統,還要更分析入微,還要更具體化一點,于是便有這原始原子說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現。萬物的構成求之于這些實質的五大原素,這思想應該是一大進步。這本由子思、孟軻所倡導而為陰陽家的鄒衍所發展了。”
關于陰陽家代表鄒衍的宇宙學說,其所著的《終始》《大圣》等篇已經佚失難考,但基本思想觀點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得以保存。司馬遷評價說:“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大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然其要歸,必止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如果司馬遷的評述是準確的,人們不難看出,鄒衍的宇宙觀,目的并不在于抽象思考萬物的來源和變化規律本身,而是為人世社會的存在秩序與演變模式提供依據與參照,由此看,其與儒家的社會學說和歷史觀大為相似,可謂殊途同歸。郭沫若說鄒衍“受了儒家的影響”,是完全有根據的。
因此,無論是陰陽家的五行相生相克學說,還是儒家的五行遞嬗五德終始觀念,其著眼點都在于社會秩序與運轉規律的思考設計,探索歷史成敗興衰的內在原因,為當權者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呂氏春秋》的宇宙觀能夠綜合道、儒、陰陽各家的思想,深層原因正在于此,而這恰恰是與呂不韋編撰此書的主要動機相吻合的。
關于《呂氏春秋》的政治主張,郭沫若采用資料羅列的方式,提出五個方面的觀點:
第一,反對家天下。《孟春紀·貴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又《孟春紀·去私》云:“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人某姓的家天下,只有有德的賢人可以為之主;一旦其失德亂政,暴虐天下,人人可以得而誅之。
第二,尊重民意。《季秋紀·順民》云:“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必成。”又曰:“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后可舉。”《開春論·愛類》云:“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君王必須體察民意,順乎民情,民心所向之事,必欲成之;民以為便的事,無不行之,做到這樣,天下可治,事業可成。
第三,贊成哲人政治。《審分覽·執一》云:“為國之本在于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季春紀·先己》云:“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治理國家的人,要修身律己,表率天下,要求國民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善于修身的人,才善于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一貫,異位同體。
第四,謳歌禪讓。其實這與反對家天下是同一思想,主張傳賢不傳子,讓真正的賢能之人來治理天下。
第五,主張君主無為。《審分覽·君守》云:“大圣無事而千官盡能。”《仲春紀·當染》云:“古之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君主無為,并非荒政無所作為,而是要分清君臣職責,不要把大小權力都抓住不放,干預臣僚履行各自職責;君主的主要職責,是選賢任能,讓百官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履行好各自的職責。
郭沫若列舉了上述的資料論證《呂氏春秋》一書反映的政治主張,最后總結評價說:
《呂氏》書中的關于政治理論的系統大體上是因襲儒家,雖然在君道一層頗近于道家,有時甚至有些法家的氣息。無疑,呂不韋本人倒可以說是一位進步的政治家,不然他是不會容許這種理論在他的名下綜合起來的。
《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第六部分,論述的內容比較龐雜,涉及《呂氏春秋》體現的重農思想,以及賞罰、音樂、忠孝、理智、軍事等思想觀念,討論不夠深入詳盡,且是從它與《墨子》和墨家學派思想觀點的對立角度入手進行分析的,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郭沫若對《呂氏春秋》本身思想內容體系性和邏輯性的把握。
從以上對呂不韋的思想傾向及《呂氏春秋》思想內容的分析看,呂氏本人的道家、陰陽家思想成分更多些,而《呂氏春秋》一書,則更多體現了儒家的社會學說與政治主張。這種表面看起來不一致的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呂氏春秋》的各篇內容多出于眾儒生之手的事實(高誘《呂氏春秋序》云:“不韋乃集儒士,使著其所聞”);另一方面,道、儒、陰陽三家的思想,本有不少相通相近處,史載孔子曾問學于老子,兩家學說在治國理政等方面確有某些相近的思想主張;而陰陽家學說雖然有玄虛不經的一面,但其目的指向,乃在于人世社會的德政仁治。由此看,呂不韋的思想傾向,與《呂氏春秋》的思想內容,在為剛完成統一大業的秦王朝提供治國安邦的理論指導和施政原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聚焦點。
三、呂不韋與秦始皇的矛盾問題
呂不韋與秦始皇的關系,兩千多年來成為難解之謎。姑且不說嬴政是不是呂不韋的私生子,即使他們沒有任何血緣關系,呂不韋傾其家資,使盡伎倆,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幫助嬴政的父親歸國,且順利即位,才使嬴政有了繼父位為秦君的機會,其功勞對于嬴政而言,謂之有再造之恩,也不為過。秦始皇親政沒幾年,為什么就與呂不韋這位“仲父”關系惡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歷來的史家與學者都想給出解釋,但似乎都沒有得到十足的認可。郭沫若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用了大量篇幅,試圖給出他的解釋。
郭沫若首先否定了嬴政是呂不韋私生子的說法。他要論證的核心觀點是,秦始皇與呂不韋的矛盾,不是名聲之爭,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思想觀念和政治理念之爭,是兩人嚴重的思想與立場的對立,決定了他們尖銳斗爭的性質和過程。
首先,在為君之道上,呂不韋主張君王應該分權分責,讓臣僚有職有權做好各自的工作,君王不能干涉其權責;而秦始皇繼承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集權思想,大小權力均集中在自己手里,一切事務都要親歷親為,信不過政府部門的臣工,只相信和專任獄吏。郭沫若批判秦始皇:“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獨裁者,一切是自己動手,丞相大臣都是具員,博士良士僅顧飯碗,天下是獄吏的天下。”因此,在權力分配上他們必然產生矛盾。況且,嬴政在未親政前,國家大事基本上是“仲父”呂不韋說了算,到親政時,完全不能接受做一個有名無權君王的現實,他要收回權力,呂不韋就成了最大的障礙與對手。因此,秦始皇下逐客令,把他趕出京城,先是令其回到封地,隨后遷之于蜀,直到逼迫呂不韋自殺,秦始皇在斗爭中大獲全勝。
其次,在宇宙觀和人生觀上,呂不韋是無神論者,而秦始皇是有神論者。郭沫若引證《史記·封禪書》記載的秦并天下令祠官序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并在渭南修建信宮(即神宮)的事實,證明秦始皇信守著秦人的原始觀念,迷信鬼神,抱有多神的信仰。在其有神信仰支配下,秦始皇不相信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命運之說,他是一位非命主義者,迷信方術,堅信神仙的存在,為了達到自己長生不老的目的,他屢次派人尋找仙山和長生不老之藥;“大約因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極端享樂”,郭沫若評價秦始皇是一位縱欲主義者,他修建空前豪華的阿房宮和巡游天下的馳道(直道),成為這方面的有力證據。他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功業,“以為自古莫及己”,過度的自信導致他的權力欲望極度膨脹,不僅自己有生之年要盡享一切權力,而且幻想著所創立的秦王朝也可以“傳子孫、業萬世”,歷史將永遠定格于此。《恃君覽·觀表》云:“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季春紀·盡數》云:“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呂氏不相信鬼神迷信,認為事物的存在與變化有其必然性和自身規律,卜筮禱告往往適得其反。《恃君覽·知分》對“命”作了十分理性的詮釋:“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措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其觀念與秦始皇截然不同。
再次,在政治主張上,呂不韋反對集權,秦始皇信奉集權專制。郭沫若列舉了秦統一中國后設郡縣、構織嚴密的監察體系等措施,目的在于削弱中央部門和地方長官的獨立職權,那些監察官,事實上都是皇帝安插在中央和四方的耳目,專門通過秘密渠道向皇帝告密,這是源于商鞅當年在秦國推行的連坐告訐的那套做法而加以體系化、制度化;秦始皇執行嚴刑峻法的一套制度,單是死刑,就有二十多種,達到了“古今無兩”的地步。郭沫若還專門論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及其對后世的災難性影響:“春秋中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秦始皇不相信儒家的政治理念,蔑視儒家的經典,他要禁錮百姓的思想和言論,所以,焚毀儒家的思想文化典籍,坑殺儒生,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極端措施。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面對這樣一位憎惡儒家思想和儒生的專制皇帝,呂不韋居然還要聚集儒生編撰體現儒家主要思想觀念的《呂氏春秋》,這不是擺明在挑戰秦始皇的權威和忍耐力嗎?宋人高似孫論及此云:“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
此外,郭沫若還論述了呂不韋重農、秦始皇重商的政策分歧。郭沫若根據史料記載秦“收泰半之稅”,說明秦始皇統治時期徭役賦稅繁重,致使民不堪命,激發秦末農民起義。《淮南子·人間》述當時慘狀云:“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役于道,大人箕會于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錢人卻依然有錢,并乘著這紛擾的時候而大發國難財,這種傾向直到漢初都還存在。”在郭沫若看來,當時的重商政策,有利于極少數豪商大賈,但秦始皇并不想讓他們永遠享受榮華富貴,他曾不止一次下令,強制豪富遷至咸陽和蜀中,籍沒他們的財產,把商人的財富變成國家的財富,再用這些錢財去修宮闕、建復道、開邊釁。
為了直觀起見,郭沫若還列出對照表,分三大項十八小項,對比呂不韋與秦始皇的思想和政見分歧。他據此總結性寫道:
象這樣絕端的對立,兩人的關系當然不能善終。但為什么會相異到這樣呢?這并不是兩個人的對立的問題,而是兩個時代的對立。周、秦之際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轉換的時期,這不論歷史觀的新舊是一致著的,在舊時以為是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移,而在我看來則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殷、周是奴隸社會,自春秋中葉以還奴隸逐漸得到自由,向來的奴隸主大多數失掉了他的優越地位,零落了下來,在社會階層中生著上下的對流,至秦末漢初更呈現出鼎沸的現象,而社會便起了質變。呂不韋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則依然站在奴隸主的立場。
郭沫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與他的先秦社會分期理論有關,也與他反對墨、法,推崇儒家的觀點立場有關。把秦始皇定義為代表奴隸制和奴隸主利益的立場,自然是不夠科學的,但他對呂不韋和《呂氏春秋》的不少看法與分析,仍有其合理性與啟示性價值。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1973年寫了《春雷》一詩,其中有“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之句,人們拿它作為郭沫若在秦始皇評價上上下其說的證據。筆者以為,郭沫若“文革”期間,在毛澤東批評其《十批判書》的特殊背景與巨大壓力下,否定原來的觀點,未必出于真心實意,更多地是一種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僅憑此認定郭沫若完全推翻他對秦始皇的評價,尚缺乏堅實的說服力。
[1]郭沫若.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郭沫若.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劉向集錄.戰國策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陳奇猷.《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J].復旦學報,1979年第5期;呂氏春秋校釋·附錄·考證[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6]呂氏春秋·序意[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7]老子.道德經上篇[A].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易·系辭下[M].三蘇全書·經部第一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9]班固.漢書卷三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高誘.呂氏春秋序[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1]呂氏春秋·孟夏紀·大樂[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五[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2]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三[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3]司馬遷.史記卷七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4]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一[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5]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一[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6]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九[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7]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二十一[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8]呂氏春秋·審分覽·執一[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十七[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9]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三[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0]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十七[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1]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二[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2]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二十[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3]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三[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4]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二十[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5]高似孫.子略[A].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附錄·考證[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26]淮南子·人間[A].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