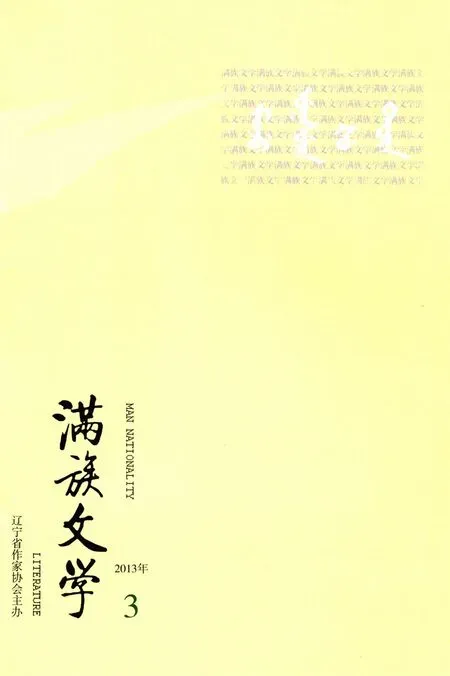夢一場
2013-11-15 19:43:42馮忠臣
滿族文學
2013年3期
馮忠臣
雨,絲絲屢屢如一襲薄紗,細細軟軟、綿綿密密地下著。陰冷、潮濕,天空灰暗,似乎惆悵布滿了每一寸空間,抓一把空氣好像都能攥出水來。幾只不知名的鳥從天際飛過,叫聲幽遠、凄涼。
吉勝站在窗前,內心一陣一陣的蟄疼。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疼越來越強烈,像一只不斷長大的怪物,用堅硬的鱗角觸碰脆弱的內臟和敏感的神經,有時讓他覺得好像要窒息了。對誰說呢?無厘頭、莫名其妙的身世,如何能說得清。縱然有人傾聽,又從何說起,怎么張開這張嘴。每當陷入痛苦的深淵,吉勝只能躲到沒人的地方,自我折磨。多少個暗夜他從精神深處分裂出另一個自己,不斷咒罵、責怪自己,以此宣泄心中積郁已久的悲涼,為自己舐傷。
傷在二十年前。
那年吉勝五歲。
吉勝的父親趙木匠常常走村串戶給人家打家具、建房屋,因為手藝妙為人厚道,受到了人們的尊敬。母親菜花心靈手巧,人長得甜,會打理家務處鄰居,人們都愿意和她來往。夫妻倆恩恩愛愛,無憂無慮,生活過得殷實、愜意。村人們經常說,這真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羨慕不已。小吉勝也生活在蜜糖罐中,享受著別個孩子沒有的充滿陽光雨露的快樂童年。父親經常出去干活,有時會給吉勝買回些稀奇古怪的玩具,讓吉勝在小朋友面前很是揚眉吐氣,小朋友都圍著他轉,小吉勝感覺很是受用。趙木匠外出短則三五日,長則個把月,偶爾三倆月也有過,回來就會格外地疼愛吉勝。時間長了小吉勝想爸爸,看到趙木匠又有些陌生,低頭不敢直接看,用眼睛一下一下地瞟。……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