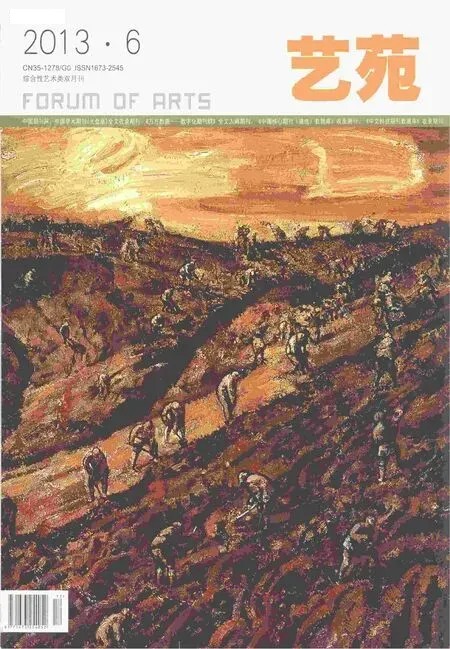《劇評家》:18世紀愛爾蘭劇場穿越之旅
文‖馮 偉

如何了解18世紀愛爾蘭戲劇行業的人情世態?讀歷史書。不,最好的方法莫過于去當時的戲劇圈里體驗。穿越?對了一半,穿越至關于戲劇的戲中。2013年都柏林戲劇節上演了本國劇作家理查德·謝禮丹(Richard Sheridan,1751-1816)的《劇評家》(The Critic,1779),巧妙地將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和步行劇場(promenadet heatre)融為一體,讓觀眾走進戲劇史,親身體驗。理查德·謝克納最早在1968年提出“環境劇場”這一概念,意指將觀眾容納到演出空間的表演方式,如此一來,表演環境和觀眾的切換都會給每一次的演出帶來新的變化,從而增加演出的同時性和代入感。而中途劇場更換,觀眾跟著演員跑到另一個劇場,又顯然是步行劇場。Promenade的意思是“散步”,而這個術語的內涵,便是觀眾一直在隨著演出而流動。雖說此劇并未時時刻刻與觀眾發生互動,但觀眾的身份,卻從頭到尾都是見證者。
演出地點是都柏林市中心坦普爾酒吧區(Temple Bar,又譯圣殿酒吧區)附近的文化之屋(Culture Box)和方舟劇院(The Ark)。坦普爾酒吧區歷史悠久,位于都柏林麗妃河南岸,沿河往西去,便是喬伊斯《都柏林人》的主要場景。由于該區域是娛樂和餐飲中心,而尚存的建筑本身就是歷史遺跡,也就終年游客不絕。對于嗜酒如命的愛爾蘭人,與朋友聚會的最佳場所莫過于酒吧。每到周末,這里就會變得熙熙攘攘,而與之對應的是——街頭老歌手的藍調、年輕人的說唱、風笛和手風琴演奏、搖滾樂隊,當然,還有每一家酒吧里的各種現場音樂,以及各種小劇場的活動。所以,歷史和表演是該區域的關鍵詞。而將此劇置于這樣的環境,顯然是導演有意為之。
原劇背景設在英國,但該劇導演將其挪到了謝禮丹的故鄉都柏林。因為該戲的場地分別在客廳和劇院,故演出地點也在中途改變。文化之屋其實就是一個起居室大小的展廳,第一場蕩格先生(Mr.Dangle)之家便設在此處。一進劇場,便看見放在屋正中的18世紀歐式圓桌和椅子,一位奧斯丁小說里走出來的婦人坐在桌旁,翻著一份報紙,并不時抬頭打量入場的觀眾。墻角坐著蕩格先生,正在溫習該劇劇本。屋子四周靠墻放著兩三排椅子,觀眾沿墻而坐,仿佛是等待主人開口的客人。所以,這是要觀眾從360度全方位身臨其境。演出開始,一位敘事者從觀眾席中走出,講述謝禮丹寫作的時代背景,比如,坦普爾酒吧區是當時都柏林的戲劇中心。他告訴觀眾,這個劇的內容就是當時戲劇界的各種亂象。彼時的謝禮丹已是倫敦的皇家特魯里街劇院(Theatre Royal,Dr ury Lane)經理,與該行業形形色色人群的來往自然也令其滿腔怨憤——否則為何需要寫一出諷刺喜劇來排遣?在本劇中,他調侃了百無一用卻還頗為自矜的批評家,自命不凡卻不停落入窠臼的劇作家,以及同行之間的抄襲現象。當然,按照愛爾蘭所有劇院的慣例,敘事者也不忘提醒觀眾關閉手機,而這時,蕩格太太舉起了餐刀,目光巡視全屋,眾人會心一笑。——但是,這到底是表演還是現實?演出過程中,敘事者不時的插話讓觀眾明確了自己的身份:保持一定距離的參與者。換言之,他好比時空旅行的導游,帶領游客返回古代,同時不忘在關鍵時刻補充一點背景知識。如果沒有背景知識,其具體的諷刺內涵就難以捕捉;而如果不推倒第四堵墻,喜劇何以成為喜劇?觀看喜劇最好的方式并非正襟危坐,而是進入越界的歡樂情境,讓身體的每一個細胞去享受越界的快感。
演出以夫妻斗嘴開場,主題自然是爭論劇評家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必要。老兩口相互抬杠,卻又一本正經,不由讓人想起《傲慢與偏見》開場中聒噪的本內特太太和冷淡的本內特先生,只不過在本劇中,冷漠的是太太,聒噪的是先生。蕩格先生會拿著桌上的報紙,念一兩句劇評,可是他手上拿的明明是今天的《愛爾蘭時報》,時間的幻覺也被打破了。屋里隨后來了兩位客人,一位目空一切的劇評家,奚睨爾(Mr.Sneer)先生,一位熱衷于抄襲別人的劇作家,胡來瘋·剽狼藉(Sir Fretful Plagiary)爵士。謝禮丹的命名中已經暗含了二位的性格:一位自控而尖刻,一位暴躁而蠢笨。室內風俗喜劇的氛圍不難想象:幾位戴著假發,穿著當時流行于上流社會的男式裙褲、吊帶襪和高跟鞋的男性,說起話來用詞考究、裝腔作勢、含沙射影,不時夾雜王爾德和蕭伯納式的愛爾蘭幽默,配以奧斯丁小說人物的神經質色彩,最后鬧得洋相不斷——難道這不很具時代風貌?剽狼藉先生代表當時抄遍天下書且抄襲品位極差的平庸劇作家,奚睨爾則是拐彎抹角、故作矜持其實卻尖酸刻薄的劇評家。油滑的蕩格先生自然是晃蕩于二者之間,盡量誰也不得罪。后來,曾以拍馬屁為業的主角捧夫(Mr. Puff)先生登場。這是一位自戀而躁動的劇作家,明明渾身散發著丑角的喜劇勁,卻非要去寫悲劇——畢竟,喜劇太低級太廉價了,只有悲劇才能彰顯人的崇高和偉大,尤其是其創作者的崇高和偉大。為了和觀眾打成一片,這位讓人聯想到哈巴狗的捧夫先生在屋內夸夸其談,搔首弄姿,四處晃蕩,并不停地撫摸四周女觀眾的金發,以及男觀眾的禿頭。為了解除他們的尷尬,所有觀眾都會哈哈大笑。當然,經理偶爾也會與之互動。觀眾沒有直接參與,但卻偷窺了當時劇評家和劇作家們不堪的一面。
第一幕結束前,捧夫先生邀請奚睨爾先生和蕩格先生去劇院指導其劇作的彩排。可是哪里有劇院?這時屋里款款走進三位年輕女郎,說著蓋爾語,請觀眾離席去另一個劇院。于是我們跟著人群走了,兩分鐘的路上還遇到三個抗議者,舉著牌子喊叫,牌子上的口號內容分別代表不同年代的愛爾蘭歷史事件。有趣的是,這一幕在酒吧區的老屋和老街中顯得尤其自然。要是放到充滿現代氣息的艾貝劇院(Abbey Theatre),或許更會讓人哭笑不得。

走進方舟劇場,坐下一看,也是一個能容一二百人的半環形劇場——類似于古希臘劇場的室內縮小版,觀眾席上方是導演調度的空間,劇場中間坐著十幾個身著演員訓練緊身衣的學生——是都柏林這邊戲劇系的學生。中間一位身著現代裝的光頭老師,正是之前那位敘事者。他手捧彼得·布魯克的《空的空間》,跟學生講席勒、布萊希特和布魯克的戲劇理念。舞臺右后方擱著大提琴、鋼琴、吉他、豎琴和鼓,左后方是掛著演出服的衣架。一個實時拍攝的鏡頭對準了舞臺上方圍觀的三位先生,其影像又被同步在了舞臺的幕布上,這樣觀眾就能看見戲內戲外全部的演出。喜歡在臺下說三道四的劇評家們被前置到了舞臺上:恐怕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吧?是捧夫先生的悲劇好看呢,還是他們幾個人好看?沒錯,這是戲中戲,而且戲中戲里面還有戲,導演真是要把幻覺和現實的吊詭關系玩個酣暢淋漓。而這種玩法,便是對書本教條中陌生化或第四堵墻的游戲,導演穿梭于其間,觀眾入戲出戲,卻絲毫不影響看戲的興致。而這種效果的實現,也有賴于現代舞臺媒體技術的加入。
《西班牙艦隊》彩排開始,三位劇中人在舞臺之外觀看,因此這部分演出主體是這些學生——學生的身份讓人聯想到演員的業余,不過除了業余演員蹩腳的演技,還能有什么配得上陳腐的劇情?捧夫先生的悲劇自然雜糅了悲劇這一題材的所有陳詞濫調:雄壯的音樂、詩體的語言、一見鐘情、相思、騎士、拯救、瘟疫、決斗、吻別、誓言,不一而足。因為他反復強調:這些都是成為悲劇的必要條件!兩位見多識廣的劇評家連連點頭附和。排練期間,捧夫先生不停地向兩位劇評家解釋每一場的“良苦用心”以及“創作理念”,而作為劇評家的蕩格先生和奚睨爾先生也會不斷地吹毛求疵,畢竟這是他們的專職:這一段不是出自《奧賽羅》嘛?怎么到你這里了?或者,這些人不是應該睡著了么,怎么又跑出來了?這好像不合邏輯。不拘小節的捧夫先生只得耐心解釋,但他越解釋,其才能的不堪、創意的陳腐、構思的粗陋越是一露無遺,而相對應的是,劇評家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也越發荒誕不經。通過目睹戲劇誕生過程,觀眾明白了陳腐而荒謬的觀念和爛戲的親緣關系,同時,也能圍觀當時所謂的劇評家們到底有什么“本事”。這些煞有介事的切磋令觀眾忍俊不禁,但反諷的是,最具喜劇性的恰恰還是悲劇的排演。


為了表現業余水平,學生們帶著不知由來的道具——舉起破傘就是劍,褲腰塞上雨衣就成了翅膀。需要制造陰森氣氛時,就有學生亂撥豎琴、吹哨笛、配合人聲,效果一團糟,這就是恐怖效果?作為學員,他們自然而然理所應當該以造作和夸張的方式去表演。因此,其道具的惡搞、劇情的陳腐和荒謬、表演的拙劣和僵硬,與投影中三位蒞臨指導的專家的一本正經構成強烈反差。悲劇也因此成了鬧劇。后來捧夫先生被演員們打出去了,奚睨爾和蕩格先生從上面走了下來,嘆道:哎呀,真是一出精彩的喜劇!謝禮丹所嘲諷的正是當時戲劇界的種種怪象:劇評家的自作聰明、劇作家的隨波逐流和無恥抄襲。隨后,蕩格先生拾起地上的《空的空間》,念了開頭,然后二人會心地相視一笑:什么狗屁玩意!歷史和現實又被混在一起開玩笑,而這背后是對兩個時代劇評家的辛辣嘲諷。如果二位先生走進后現代劇場,肯定會罵道什么亂七八糟,而如果布魯克去了18世紀,又會嘲笑他們觀念的陳舊。二者孰是孰非?
演員上臺謝幕時,作為背景的幕布起了,整面后墻被打開,室外的冷風吹了進來,外面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人,拉著大提琴。演員朝著墻外的“觀眾”謝幕,然后墻又合上。原來方舟劇院的觀眾席室內室外均可用。伴隨演出空間延伸的也是主題的深化。該劇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意將不同的時間維度置于同樣的空間維度中,這種疊加也讓本劇沾上了批判色彩:劇評家嘲笑同時代的劇作家,也嘲笑后來的劇評家,而如今的觀眾又按照當今的戲劇美學理論,嘲笑當時的劇評家及劇作家,到底誰在戲外誰在戲中,誰在觀看誰在被觀看?或者,作為評價依據的,是受制于歷史的狹隘視界,還是撇開偏見之后看見的戲劇本體?答案恐怕是后者。而最后舞臺打開其真正的幕布,恐怕是在提醒觀眾:你坐在舞臺上看戲,看戲的人在舞臺下看你。你的客觀發現和主觀體驗,你的真實和幻覺,可能都不是絕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