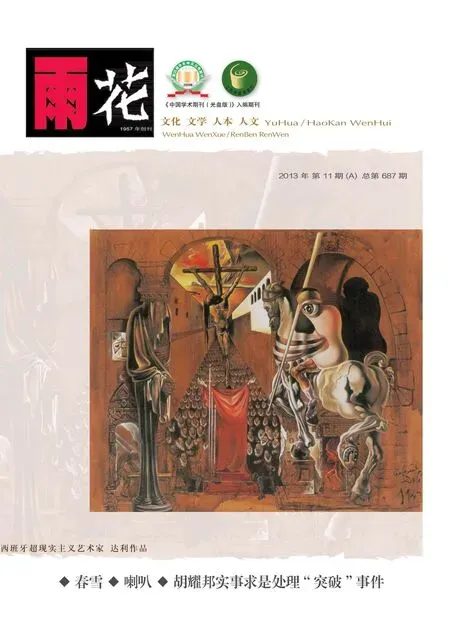雙親
● 偌 思

我從小就為父母親是騎兵而自豪,沒有比戰馬奔騰,手刃日酋更能激起一個孩子英雄夢的了。可是,每次我纏著父母講騎兵旅的故事,父母似乎都不愿多說。
母親篇
母親生了我們5個孩子,均是男兒,最后一個取名安琪,生下5個月后就夭折了。人生過得太快,安琪如果健在,今年也該虛歲60了。
安琪夭折時我三歲。我竟然記得我曾經抱過這個小弟弟;記得弟弟夭折后,母親從醫院回家時的倦怠;記得當天晚上婆婆在家里拉著長音哭唱時帶給我的恐懼——湖北人的哭唱,成了兒時與死亡聯系在一起的毛骨悚然的記憶。
母親不久罹患了肝炎,身體很快垮了,接下來就是長年拖著虛弱的病體勉力地工作,直到離休。
母親的家族,世代為楚地漕幫,自小耳濡目染,江湖道義溶化在了血液里。母親參加革命,不是因為接受了馬列主義,也不是為了謀求稻粱,完全是不滿于社會的不公,所以民族面臨危難之際,她幾乎是義不容辭,跟隨王明的美麗夫人孟慶樹到了延安。
我曾經十分好奇,母親的職位并不高,可是她受到的廣泛尊敬,甚至超過了父親。尤其是南下的戰友們,全都尊稱她大姐,比她年紀大職位高的也這么叫。
父母南來北往的戰友,時常在我兒時的家中出沒。父親總會告之母親,某某來了,晚上來家吃晚飯。歉然地又加上一句:簡單,炒盤雞蛋,來盤花生米,喝喝酒……而母親幾乎懶得與父親討論,總是一句話,你就別管了,老侉子。
見到共過生死的戰友,父母總是很開心。母親親自操廚,做出一桌豐盛飯菜,偶爾也能與這些大老爺們喝上幾杯。父親的中原大嗓門,母親鏗鏘的楚語加上她朗朗的笑,戰友們的各種南腔北調,使家里一片歡聲笑語。
母親有一次笑說道,我們家的錢,都吃掉了。
一個叔叔有次對我們兄弟說,你們不知道啊,你媽媽當年可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女英雄啊!說罷,不勝唏噓。而母親有什么英雄事跡,至今我也不甚了了。只知道,母親從延安中央黨校畢業以后就進入了野戰部隊,一直在前線作戰,在戰斗中兩次負傷。而父親是員福將,大小戰事過百,除了42年與鬼子作戰時被炮彈震得有點失聰以外,連一根汗毛也沒有傷著。
在后來成了高級將領的王叔的描述里有幅畫面頗具動感:一個深夜伸手不見五指,駐地外面忽有動靜,我提上槍沖出去,一下摸到了一個人,我厲聲喝問,誰?對方已先一步抓住我,隨即一支長槍就抵住了我的前胸,也在喝問:你是誰?我一聽,是個女人的聲音,知道不是敵人,再一看,是平俠同志……
關于母親的傳奇,我們其實一直是有點似信非信。直到文革中,我搞到一支氣槍,與弟弟和一幫玩友在院子的竹林里打鳥玩,賦閑在家的媽媽居然罕見地與我們廝混在一起,她說你們瞄準的姿勢不對,我打給你們看。她接過氣槍,竟然單手持槍,對準瞄準物就是一槍,擊中。我們都驚呆了!第二天,大院子里的孩子們就傳開了:平俠阿姨是神槍手!
家里孩子多,我們的家庭教育完全是放羊式的。父母撫育我們的那個階段,時代變遷,萬象更新,他們亢奮而投入,幾乎沒有時間關注我們。每天他們在我們還沒有醒來時就已經離家工作,晚上我們已經入睡了他們尚未歸來。
回顧往事,母親從未刻意地塑造過我們。經歷過各種運動的父親,似乎也只是希望我們能夠平安無事地學門技術。母親對我們的教誨,竟然不過是老百姓的一些凡人俗語,如:窮不倒志,福不癲狂。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不可以衣帽取人,不可狗眼看人……等等,沒有任何高深哲理,而母親的為人處事,則無一不是身體力行。
剛搬到將軍巷時,整條街的人均施我們以冷眼。人們似乎要通過觀看一個政府官員的言行來給新政權下定義,且很多人身份驟變,對新政府本身就充滿敵意。
我們這條巷子曾有過一座明代將軍的府邸,街坊中許多住戶也都是舊時的大戶人家。兒時我在同學家玩耍,對他們家中厚重的雕花家具印象深刻,猜想它們一定都有著不凡的經歷,全然不似我們家中還編了號的公家家具,讓人絲毫沒有一點文化想象。
我們居住的20號是市委房產,住戶三家,兩家都有孩子與我為同班同學,一個是張同學家,父親是戰斗英雄,炮兵團長,母親時任市衛生局長,我們兩家經歷相似,關系天然融洽;而另一位陳姓女同學家,父親是區委的工友,母親來自蘇北農村。我們那時雖小,也能真切地感覺到來自蘇北大嬸的敵意。20號院子很大,父親母親每天晚上回來很晚,敲大門里面聽不見,而緊靠大門的蘇北大嬸家,敲破天也裝作沒聽見。
街上的人更是如此,有時父親單位來車接,車胎動輒被人放了氣。我們幾兄弟每與人發生爭執,街坊們就像是專在等待這種口舌機會,借機沖進家里討要說法。
可是不久,這樣的事就少了,漸漸更是完全沒有了。這是因為母親謙讓、自律、平等的姿態,讓街鄰們不但接受了我們一家,也給予了我們一家可貴的尊敬。
后來,除了夜間,20號院都是院門大開,任人進出,一街的孩子幾乎沒有誰沒到我們院子里玩過。兒時常見的街景,就是一群鄰居在敞開大門的院子里與母親坐在涼床上、小板凳上聊天,母親與他們笑語連連。
記得我們隔壁有一個叫金城的孩子,略大我幾歲,每天幫著他拉板車的父親運送氧氣瓶,那位脾氣暴烈的父親打起兒子來,一條街的人都膽戰心驚,沒有人敢去拉架。一日,老金頭又在用爐鉤暴打金城,母親正好下班經過,厲聲喝住他,把金城擋在了身后。老頭顯然沒經歷過這個陣勢,轉身就要對母親動粗,母親一臉正氣,大聲斥責他:你有什么權利打孩子?把孩子打壞了你是要坐牢的!鄰居都圍上來,既驚訝又敬佩地看著母親,被鎮住的老金囁嚅著,沒敢再吭一句。母親大聲對鄰居說:你們大家聽好,如果你們今后再看見老金虐待這個孩子,告訴我,我把他送到公安局去關起來!
鄰里是知道母親在法院工作的,時而也會有穿法警服的司機開車接送母親,所以沒人懷疑母親這句話的份量。我當時目睹了事件的整個過程,母親的凜然至今難忘。
從此,鄰里眼里的母親,不僅僅是一個有著親和力的,操著南方口音的鄰家大姐,他們還看到了母親的爆發力。金城再也沒有挨打了,老金頭每一次見到母親都很恭敬。
將軍巷還住著一個潦倒的人,30多歲,白白凈凈,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他低著頭在地上撿拾煙頭。他沒有工作,沒有人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內容,好像就是靠撿來的煙蒂噴云吐霧。
母親是抽煙的,母親上下班時,常被他堵在街上索要香煙。他乞討香煙的方式很文明,不說話,只是伸出手,眼睛也不看人,要到了煙就走,也不說聲謝謝。
一天,我和母親在廚房里剝毛豆,忽然一個人的身影,擋住了屋外的光線。原來是他,他斜倚著門,低著頭,也不說話。這一次母親沒有立即給他香煙,而是搬了一只小板凳,讓他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聊著聊著,忽然間他泣不成聲,最后,母親要我到房間去拿兩包飛馬香煙交給他,把他送出了門。
晚上吃晚飯的時候,母親向我們講訴了他的故事。原來他曾是一個美術學院的學生,因為一次失戀而精神崩潰,從此再也沒有恢復,成天精神恍惚,完全成了一個廢人。我已經記不清母親是怎么與他交談的,只知道母親在長江路上的一個標牌店為他找了一份工作,收入一天一塊錢。他利用他的特長,為人畫標牌寫美術字。至此,再也沒人看見他在路邊撿煙頭。
有一天,我和母親在工人文化宮看到了他,他正往一個玻璃櫥窗上描畫美術字,也不打草稿,直接用油漆刷在玻璃上寫字,兩個小年輕顛顛地跟著他,為他端茶遞煙,引來一群人的圍觀。他表情嚴肅自信,還有一點矜持,全然沒有當年的頹喪之氣。
我想叫他,母親搖搖手,拉著我走了,過了一會兒,母親忍不住笑起來,用湖北話罵道:格老子的,抖起來了,都有徒弟伺候了。
看得出,母親是欣慰的。
我們在這條街上住了將近六年,這六年幾乎涵蓋了我童年的全部記憶。我11歲那年,在與街鄰們的戀戀不舍中,我們搬離這里,去了城北九華山下的新住所,這個美麗院落建成于1948年,曾經的園主是舊政權的一個高官,享受它的時間不到一年。
這個院子也住了三家人,一家是市委領導賈伯家,另一家是王姓四川人,原為賈伯的戰時警衛,進城后為機關后勤的工友,住在門口汽車間改造的房子里。王嬸是個小腳的山東美女,我們搬進去的時候,王嬸才30多歲,不能生育,領養了一個女孩。她和其貌不揚的王伯的組合,刺激著那時我們幾個兄弟的想象力。賈家女主人陳阿姨,是母親終生的老姐妹。母親與陳姨成為好姐妹的原因,源于建國初一位市領導下令的排查運動,陳姨喜歡亂發議論,不幸成為運動重點。工作組氣勢洶洶,要陳姨交代是某個謠言的始作俑者,不許陳姨回家。而關鍵的人證是與陳姨在市總工會同一間辦公室上班的母親。
母親平靜地否定了對陳姨的全部指控,工作組不滿意,一再誘逼母親的口供。母親的湖北九頭鳥的性格上來了,激烈抗辯,寸步不讓,雙方都拍起了桌子,滿走廊的人都聽到了母親與工作組的爭吵聲。陳姨關在隔壁辦公室,聽到了他們的全部爭吵,感動得要命,終于過關以后,她開始了與母親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
陳姨總跟我們說起這段往事,一說就感嘆母親的耿直義氣,怨恨她丈夫的窩囊和無能。當時賈伯是市總工會的副主席,妻子被整一言不發,絲毫沒有出手相救的意思。可是,齒以剛而折,舌以柔而存,賈伯一輩子沒見有個朋友,他卻一輩子官運亨通,健康長壽,如今已近100歲高齡。
陳姨,揚州人氏。體型富態,皮膚白皙,是官宦之后。
她怎么會到革命隊伍里來的,而且資格夠老,始終是個謎。尤其是她曾被兩個中共知名高官追求過的軼事,長時間在新四軍老兵中相傳。因此,母親始終認為她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個異類。
現在想來,時代的新舊對于陳姨或許并無太大區別,無論是舊時生長的王謝之家,還是參加革命后的高官之家,她依然保持著與生俱來的生活方式。她享受美食,講究穿著,習慣了有人伺候,一生都沒有撫育過子女。白天,她是處長,在單位看報,讀文件,游刃有余;回到家,她嬉笑玩樂,如魚得水。到和平公園看人打拳,跟打拳的人成了朋友;在珍珠橋上看人家打魚,跟打魚的人成了朋友;看到路邊有人養鴿子,跟養鴿的人也成了朋友……她就是這樣一個世間的尤物。
母親雖與她算得好友,價值觀卻是迥異。一日,陳姨不滿意保姆打掃的衛生,責罵保姆是“瘟豬”,母親聽不下去,把陳姨叫到旁邊,正色道:你怎么可以這么罵人呢?她又不是你的奴仆!陳姨當時非常尷尬。
細想,陳姨實在是非常好的一個人,善良忠厚,胸無芥蒂,忠誠友誼,樂于助人,去年無疾而終,享年九十。
賈伯工作調動搬走后,院子里搬來了另一位市領導。
這位市領導曾是當年新四軍里的文人,他資歷不老,升官很快,除了一位頂頭上司,沒有其他朋友,也從不認農村來的親戚。
一日,那位官友來他們家做客,吃完晚飯兩位官家在庭院里下圍棋。時任市委秘書長的父親走過去匯報工作,匯報完后,兩位頭頭繼續下起了圍棋,父親身子沒有動,眼睛依然盯著棋盤,斟酌還有什么工作需要匯報。母親老遠望去,勃然大怒,說:老四,把你爸爸給我叫回來!
父親回來后,母親把父親拉進房間,斥責他道:工作匯報完了就回來嘛!你又不會下圍棋,坐在那里干什么!拍馬屁!……
父親被母親罵了個暈頭轉向,呼哧呼哧的,半天說不出話。
母親嫉惡如仇和絕不阿諛奉承的剛烈性格,給我們兄弟立下了終生的榜樣標桿。有母親在側,我們都不敢沾染任何奴顏之氣。
不久,混亂的年月開始了,我們參加了紅衛兵。母親破天荒召集我們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她對我們約法三章:不許打罵侮辱老師,不許參加武斗,不許偷拿抄家物資。我們知道,母親是極其認真的。
一天,二哥被通知帶領全體紅衛兵到勝利電影院參加一個市委領導回答紅衛兵關于文革問題的大會,二哥當時是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會議開始了,完全沒想到,代表市委回答問題的竟然是父親!
父親的口才素有其名,可是那天,在狂熱的學生面前,父親卻顯得笨拙口訥。我驚坐在位子上,憤怒而無奈地看著沖上臺的十來個學生將父親推來搡去……
晚上父親回到家,情緒低落,母親做了幾個好菜,陪父親喝了幾杯酒,好半天沒說話,猛丁,母親吐出一句國罵,對父親說:格老子的,你可給我挺住啊!
接下來幾天,父親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一天,父親讓我騎車把一個本家世叔叫到家里,對他做了一些交代。又一日,父親也在家里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父親分析了時下的形勢,歷數了歷史上的朝代更迭。父親旁征博引、說古論今,最后總結說:這次運動本質上跟歷史上任何的一次權力斗爭沒有兩樣,就是要我們這些功臣讓位。所以我決定,解甲歸田,回老家去。我已經安排人把土改時分給我們的房子打掃了一下,形勢如果再惡劣,我們就走……
父親的決定很意外,也很突然,一時,大家都沒有開口,空氣嚴肅得幾近凝固。忽然間,母親一聲斷喝:胡扯!憑什么?我們出來參加革命,沒有罪,我們打鬼子,沒有罪。我不懂什么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說我們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也是上面領著我們走的!母親又重重拍了一記桌子,對著父親說:我看不得你那副倒志的樣子,我還不信這個天真能翻了,就是翻了,我們去要飯!我走前面,你走后面!……
母親脫口說出的對“上面”的微詞,把我們驚呆了。那可是1967年紅色崇拜最瘋狂的年份。
自此,回家務農的打算再也沒被提起。
一次弟弟的團伙與一個普通家庭子弟建立的“灰色組織”起了沖突,我自然為弟弟助戰。晚上家里正在吃晚飯,院子里忽然沖進幾十個端著長矛的人,叫喊著要找我和弟弟,他們個個氣勢洶洶,殺氣騰騰。我一驚,看來一場惡戰難以避免。母親問我,你倆把人家怎么了?我說沒有什么,就是白天在外語學校辯論時互相推搡了幾下。母親說,你老實告訴我,傷人了沒有?我說,沒有。母親推我進里屋,厲色道:進去!這時候莫要逞英雄!
母親放下筷子,起身開門,走進殺聲震天的院子。
母親慢慢走向這群渴望熱血搏殺的人群,母親瘦小的個子與人高馬大的入侵者形成了對比。母親走到他們面前,沉靜地對他們說:你們要找的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們的母親。現在他們不在,如果他們犯了什么錯,是我們家長的責任,我一定批評教育他們……那些孩子氣沖沖而來,非常禮貌地離去,臨走,還客客氣氣地對母親說,阿姨再見。站在紗窗后面的我,心靈里永遠印上了母親臨危不懼、大氣從容的天然風范。
遵從母親的約法三章,我們幾兄弟沒有一個參與過侮辱批斗老師,沒有一個參加過打砸搶和武斗。我們或讀書,或練武,度過了文革中最混亂荒誕的歲月。然后,參軍,入學,就業,結婚,生子,出國,創業……,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母親也老了,漸漸地走進了人生的暮年,她離休后的日子,國家經歷的變遷不一而足,而家里一個被隱瞞了半個多世紀的秘密,也終于被我們所知曉。
大哥說,1949年年末,家里忽然來了個農村婦女,手里還拉著她的閨女,來人竟然是父親的發妻,她沒有死于民團的殺戮,而是在異地躲過了戰亂。
母親平靜如常,安排了她們母女的食宿。在組織的協調下,妥善地處理了這件戰后很普遍的家庭不幸。母親把大姐送進學校,到處奔波為她爭取到了當時的一份供給制。母親對當時只有30歲的父親的前妻說,你還年輕,還可以工作,你想到南京來工作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但是她說她沒有文化,擔心沒人要她。母親說:事在人為嘛!
母親正懷著我,每天挺著大肚子滿街跑,終于在一個小學校為她找到了一份工友的職位,每天的工作是為課堂上下課搖鈴。她在這個學校工作了十幾年,直到六十年代因為急性肺炎去世。
我聽完這件往事萬分驚訝……我們怎么會一點都不知道?
大哥說:你不知道是因為媽媽沒有讓你知道,也沒有讓任何人知道。這是母親的大氣,母親的胸襟非常人可比。
我沒有能力寫出母親的全部,也不知如何評價我的母親。我想母親首先是一個具有人性的人,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和好惡愛憎,形成了她最基本、最難得、最動人的品質。
母親又是一個有個性的人,看不得人世間的不平不公。她向往共產主義描繪的世界大同,可是她也是很早就認清了政客對這個主義的利用。
母親晚年有一次與我交談,她說:管理一個國家最好的標準,就是老百姓的標準,哪里需要這個主義,那個主義?
母親參加革命前僅初通文字,還是在工廠掃盲班的夜校里學的,可是幾十年的刻苦自學,連一直自認為是讀書人的我們幾個兄弟,也都會忘記母親的教育背景。母親口才很好,記憶力超強,古典文學名著在我們小時候就基本讀完,她聽別人說話,很快就能理出頭緒,敘述事情,三五句就說到重點。解放初,母親在電信局做軍代表,市里某負責人聽了母親幾次匯報,感慨道:如果多幾個平俠同志,南京的工作局面就不一樣了。
母親不善于體現母愛,生下我之后,第9天就去上班,在總工會工作時,三年都住在單位,周末才回家看看孩子。
母親熱愛生活,卻又從不畏懼死亡。戰爭年代且不論,和平時期收到過九次病危通知書,每次都是病危通知一撤,立刻笑聲朗朗。
轉眼間,母親已經去世20年。母親臨終前囑咐我們不要開追悼會,不要搞遺體告別,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只要把她的骨灰埋在一棵樹下。
母親從來都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老百姓,來自一個草根。
母親走了,永遠地走了,可是母親向往的公平社會,還遠遠沒有到來。
父親篇
父親,陳氏家族龍字輩。
高個頭,國子臉,說話聲音洪亮。
他的出生地,是淮北一處雞鳴三村,四省交界,五方不管的貧瘠地區,因為地處戰略要沖,自古為兵家必爭,歷史上曾被無數戰禍肆虐。
民國中期,中原大地軍閥混戰,匪盜蜂起,剛值弱冠的父親竟被土匪綁了票。家里巨額贖回父親后,原本富足的家道就此衰落。爺爺飽讀詩書卻不管家事,終日領著十里八鄉的村民抗捐抗稅、抗匪抗暴。幸而有能干的奶奶主持家政,不到十年光景,家里又有了十幾畝地,幾頭牲口,再做點小生意,這樣的家境,使父親讀完了安徽蚌埠師范。七七事變時,父親已在家鄉當上了一名教師,性格溫和謙讓的他,十分適合教師這個職業。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爺爺和父親坐在了油燈下,討論國和家的前途命運。爺爺這時亮出了他地下黨的真實身份,父親立即辭去教職,又聯絡了村里的七個青年,奔赴了延安。爺爺將他們送到村口,這時是1938年1月,離南京屠城不到一個月。
父親兄妹三人,父親居長,還有一弟一妹。父親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小父親11歲,是個直言快語,性格潑辣的女性,1948年也被爺爺送走當了八路,后來嫁給了一個八路軍干部。這位姑父進城后一直在海軍服役,離休前是海軍北航政治部主任。
叔叔,父親唯一的弟弟,身材魁梧,是著名的快腿。奶奶曾經向我描述,他30里路進縣城送情報,吃過晌午飯出發,太陽下山前趕回來,不耽誤晚飯陪爺爺喝酒。1948年,叔叔因為爺爺和父親都是共產黨,被當地民團殺害,我們這個家庭因此與國民黨有了血仇。
父親他們步行,扒火車,一路風塵來到了去延安途中必經的一個黃河渡口。黃河波濤洶涌,河里不見一只羊皮筏子。父親等人正在岸邊不知所措,遠處悠悠然走來一老漢,大聲道:要過河嗎?我帶你們過去!可是,既不見他有羊皮筏子,也不見他有其他渡河工具,他光身一人。
大家將信將疑地談好價錢,老漢先自己脫光,又讓大家照他樣脫光,將脫下的衣物打成一個包袱頂在頭上,然后讓一個人趴在他的背上,慢慢地下水,踩著水將第一個人送到河對岸去。此時正是寒冬臘月,穿著衣服都凍得瑟瑟發抖,老人就這樣,把大家一個一個地背過了黃河。父親曾經回憶說,那個老漢踩水時水僅沒過膝蓋,可謂奇人。
西安到了,離延安還有600里路程。他們中有兩個本村青年從沒到過大城市,不肯走了,嚷著要在西安多停留兩天,之后再趕到延安與父親匯合。
可自此一別,他們終生也沒能匯合。因為被都市生活吸引,他倆思忖反正在哪兒都是打鬼子,就地在西安加入了國軍。打了八年日本鬼子,又同共產黨打了三年內戰,1949年跟隨潰敗的國軍到了臺灣。半個多世紀后,我因商務赴臺北,見到了他們中的世叔趙忠谷,一個退役的國軍將領。在酒店大廳里,老人幾乎是跌跌撞撞地跑過來,把我抱住,淚雨滂沱。
他終生也沒有能回家鄉看看,沒能再見他的結發妻子和從未謀面的兒子。上世紀六十年代,眼看回鄉無望,他才又娶了一個南國女性。這位和眉善目的臺灣本地女人為他一連生了五個男兒,我都見到了。其中一個穿軍服的兒子向我行了一個蔣式軍禮,他是空軍少校。我也給他回了一個軍禮,毛式的,我告訴他我也當過兵,軍銜相當于上士。
離開西安之后,父親六人徒步走向延安。途中不時遇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青年,大家結伴而行,抵達延安城時,已是一支長長的隊伍。
父親很快被分配到延安的陜北公學學習,九個月后到了作戰部隊。這支部隊是冀魯豫邊區騎兵旅,隸屬邊區直接指揮,司令是以后官拜海軍大將的肖勁光。給父親分配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云。陳云指著地圖向父親介紹說:你要去的部隊駐扎在某地,人稱小江南(我后來很是詫異,中央領導會給一個小學員分配工作?父親說:那還是打江山的年代嘛!)。
父親就此開始了馬背上的征戰。1940年,父親的部隊輾轉到內蒙古大青山與日軍作戰。一年多的對決,大小戰事數十。每次戰斗,大青山的草原上奔騰著上千匹戰馬,馬蹄帶起的滾滾風塵中,戰刀的撞擊,戰馬的嘶鳴,廝殺者的吶喊,傷兵的哀嚎,聲震中天……這是古戰場時就有的情景。
騎兵對決,沒有掩體,沒有屏障。有的,是人性與獸性瞬間的迸發,眼睛是血紅的,臉部表情是恐怖的,分秒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場戰斗,5分鐘、10分鐘就見勝負,遺留下來的,是滿地的傷兵和尸體。父親曾經回憶,他親手掩埋的騎兵旅的戰友,就有上百。
父親,奇跡般地成為幸存者。
父親是一個性格溫和的人,幽默,風趣,古今軼事信手拈來,每每讓與他在一起的人捧腹大笑。我常常閉上眼睛,默想父親騎在馬上握著馬刀向鬼子殺去時的表情,無論怎樣,也想象不出父親此時的表情會是猙獰的、扭曲的、恐怖的。想象不出用冷兵器與人近身搏殺、隨時都可能殺掉對方或被殺掉的殘忍……
這樣的表情連想象都想象不出來,生活中,我更是一次也沒有看到。
1942年,延安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整風運動開始了,整風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和地下黨,這是父親第一次接觸到的黨內斗爭。
母親回憶說,那時的延安大禮堂天天開批斗會,你父親嗓門大,騎兵旅老要他領呼口號。一次他正站在臺上呼口號,忽然上來幾個人,一把抓住你父親的頭發,反扳著他的兩個手臂,就把你父親押下臺去。說你爸爸是個托派。整個過程,跟文化大革命一樣。
父親是當時騎兵旅唯一收審的干部,也是唯一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干部。騎兵旅的底子是劉志丹領導的陜北老紅軍,不管什么運動,輕易不大碰到他們,父親的審查因此頗受騎兵旅的關注,每天都派人打探父親的消息。
母親此時也已在騎兵旅,一天,騎兵旅孔旅長對母親說:里面真是太慘了,有人受不了,想用褲帶勒自己的脖子自殺,我們旅的陳某某(指我父親)倒有意思,晚上睡覺說夢話,是有板有眼地唱京戲,白天還教人被綁著怎樣拉大便揩屁股……逼供九個月后,父親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康生下令活埋。
父親一行七十多人,被繩子綁著押向事先挖好的大坑。一隊人馬恰好經過,為首者跳下馬,質問這是在干什么?父親這批人中有人認出了來者,紛紛叫道:賀司令!賀司令!我們冤枉啊!來者是賀老總。賀老總發現許多曾經是他舊部的人將要被活埋,震怒了!罵娘了!命令押解者立即放了他們!父親因此得救。
整風運動結束,中央領導向錯批錯斗的人道歉,我父親母親皆在現場,親眼看到許多九死一生的受害者感動得痛哭流涕。
父親解脫后,被調到騎兵旅任團政治處副主任,緊接著就隨著部隊開拔到了前線與日本人作戰。
兒子和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打開電視機選一些大陸的電視劇,尤其是些抗戰題材來看。兒子很不耐煩,說:爺爺奶奶當年就是這個樣子的嗎?既能上天又能入地,一個女人徒手搏殺幾十個鬼子,這哪里是抗戰片,我看是武俠片,停,停,我要看曼聯了……他還加了一句: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卻還在騙你們。
我惱火,卻無言。
兒子的長大,使得我的思緒常被帶回到童年。兒時的晚上,滿街都能聽小販走街串巷賣驢肉,狗肉,腌臘味的敲梆聲。父親如果回來得早,會跟我咬耳朵:去,跟你媽媽要錢,到貨擔子上買點驢肉,咸魚,爸爸想喝點酒。我顛顛地跑去跑回,捧回一包用清香荷葉包著的驢肉和腌臘。父親把我抱到他的腿上,拿了雙筷子,把一塊塊驢肉遞進我嘴里,又把咸魚肉上的刺,仔細挑出,我一口,他一口……
這是一段鉤沉的記憶:小巷里悠長的竹梆聲,貨擔上暈黃的油燈光,清香的荷葉,還有,父親摟著我的那份慈愛。
而九十年代的記憶畫面里,則是一個步履緩慢的老者,衣著樸素,面目和善,會不時向街邊小販問問菜價,卻沒人見他買過一次菜。他,就像街頭任何一位鄰家老叟,連咳嗽聲都沒有任何特別,無疑,老人走近了他的暮年。這個老人,是我的父親。
逢年過節,老干部局會送來一些慰問品,也就是一兩瓶油,一包水果、十幾個雞蛋。可是父親接到電話,精神為之一振,馬上叫我去取,一刻也不能耽擱。這天正值暴雨傾盆,院子外面是一個擁擠的菜市場,車子開不出去。我只好打把雨傘,前往指定的地點。雨疾風驟,一把傘形同虛設,很快我就被淋了個透。
送慰問品的車終于來了,我代表父親表示了感謝。回來時路過菜市場,我粗略核算了一下慰問品的價格,約莫30塊人民幣,我隨手就能在路邊的菜市場買到,不用淋雨。可是父親很是興奮,趕快讓阿姨拿到廚房去……我理解,父親認為這是組織上給他的一種待遇,一種榮譽。
延安,依然讓父輩人夢縈魂牽。每當父母親回憶延安,只會懷念當時延安的勃勃生機和蓬勃朝氣。延安城的安瀾門,安琪橋,都被父母鄭重用作了我們兄弟的名字。延河,寶塔山,成了革命朝圣者的精神圖騰。
父親說,騎兵旅從內蒙回到延安時,吃過晚飯在延河邊散步,隨隨便便就能遇到最高領袖;捧只碗和他一樣蹲在窯洞外啃窩窩頭、喝玉米粥的人,或許就是一個今后的開國將帥。父親似乎有點自豪,他說:當時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精英。母親說:在延安的中央領導我幾乎都見過,有的親自在禮堂給我們放電影,有的跟我們一起跳交際舞,有的要我們組織女學員的籃球拉拉隊……可是解放后,除了在報紙上,一個也沒見過。母親笑。
1945年8月,日本戰敗,二次大戰結束,內戰即起。為保障源源不斷的物質供給,唯一的方法就是發展和壯大根據地,于是一批軍隊干部被派遣到地方,參加地方政權的建設。父親被派往豫東軍區,組建豫東濮縣政府,擔任縣長,由此結束了他在野戰軍與日軍刀槍相對的八年格殺生涯。
當時地方魚龍混雜,敵我難辨,父親每天要與各色人等打交道,還時刻要與頑軍打游擊,爭地盤、搶糧食、奪兵源,雙方反復拉鋸,天天都有小規模的戰斗。可是父親對從軍隊到地方的角色轉換似乎很適應,母親一次嗤笑:老頭子搞地方工作有什么難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農民嘛,農民的生活他熟悉,農民的毛病他都有。父親聽后笑了,一點不介意,還有點得意。
父親本應是個教師,受爺爺影響才參加了革命。可建政以后,爺爺這個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反倒要求去搞教育,他做了專區聯中的校長,僅兩年后,爺爺因患肺結核辭世。爺爺與他的抗戰故事,可謂當地的傳奇。爺爺領導的抗日組織的成員,此后許多都成了黨的高級干部。奶奶對我們說,當年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經常來家里找爺爺商量事情,來了就得吃飯啊,都是我去張羅,一來,連警衛就是十好幾口。彭師長嘴利索,進門就喊我老嫂子,一聲老嫂子我要忙半天,孬×嗑子的……奶奶能干,喜歡罵人,喜歡不喜歡的人,她用詞都一樣。
1949年4月,父親隨三野南下到了南京,組織上分配工作時,父親也要求去搞教育。這樣進城后,爺爺在老家做校長,父親在南京一個中學和一個中專也做校長,兩年多后,父親短暫的教育生涯結束,被調去做了一個區的區長。
與父親一起在濮縣打游擊的戰友南下時都隨著父親到了南京,因此這批戰友們與我們家的交往最密切,與我們這些孩子也最熟悉。濮縣的司法科長賈伯,進南京后一直在法院擔任領導工作。賈伯體型修長,皮膚白皙,戴一副五十年代還很少見的金絲眼鏡。他生性內斂,話語不多,從不搶人話頭,可是只要他開口,他那不高不低,不疾不徐的語調立即就成為談話中心。與我們孩子在一起,他依然語言不多,可是你能感覺到他對你毫不敷衍的態度。我和三哥曾經私下贊嘆,父母的戰友中,數賈伯風度最好。
文革后期的1971年,父親已經“解放”,從部隊回來的我看到賈伯來了,我幾乎沒有認出來,他蒼老了許多,背駝了,衣服也十分破舊。他從公檢法看守所剛剛放出來,還沒有回家。我第一次見到賈伯的激憤,他語調沒有了往日一貫的平靜,幾次憤憤不平地罵將起來。他遞給父母一份申訴,準備交到當時的軍管會去。母親竭力支持,可是父親認為不可,然后父親分析了當時的大形勢、小局面,又給他一一解釋了為什么現在不行,而應該如何才行……
第二天,父親謀定而動,找了當時唯一被結合到市革委會的地方干部方叔,沒有多久,賈伯的上訴有了轉機。方叔今年高壽90,為人豪爽義氣,進城后成了父親的朋友加酒友,他是山東人,與當時在南京的大當家許上將夫人是同鄉,最后是許夫人出面解決了問題。
終于有一天,賈伯來到家里,見了父親就拱手作揖:老哥,謝了,謝了。父親有點得意,跟他說:你跟這些家伙不能硬來,要搞清楚他們聽誰的,他們只聽許當家的。此時的賈伯,神清氣爽,衣冠楚楚,又恢復了我們自小就熟悉的風采。不久,賈伯官復原職。再一日,五臺山體育館召開公判大會,我與母親在收音機里聽現場直播,突然,一個高亢尖細的聲音開始宣讀判決,不用看,是賈伯。賈伯在法院工作幾十年,為老百姓所熟悉,不是因為他宣讀判詞聲音洪亮,相反是他聲音像刀鋒般尖厲,攝人心魂。父親曾對我說,你賈伯是我戰友,落難時我竭盡全力相救當義不容辭,何況,賈伯曾經還救過你母親的命。
我從小就為父母親是騎兵而自豪,沒有比戰馬奔騰,手刃日酋更能激起一個孩子英雄夢的了。可是,每次我纏著父母講騎兵旅的故事,父母似乎都不愿多說。后來大哥告訴我,這或許是因為騎兵的搏殺與其他兵種不同,與炮兵更不同,近身格殺,太過血腥。他說騎兵旅自建制以來,共犧牲1000多名戰友,全都是被冷兵器所殺,每次戰斗下來埋葬戰友尸體,孔旅長都嚎啕大哭,不吃不喝,多少天都緩不過勁來。父親不愿意談這些“騎馬打仗”的故事,也是不愿意重溫猶如中世紀古羅馬斗獸場般的戰場慘烈……
我恍然大悟。后來一個開國將軍的后代對我說的與大哥說的一樣。他父親曾經是山東兵團騎兵師師長。
父母的口中,更多的是一些輕松軟性的戰斗回憶。
母親是在到濮縣當了區長后,與父親結的婚。回憶濮縣打游擊生活的話題,明顯要比回憶騎兵旅輕松。
父親回憶說:某次國軍來襲,他們被堵在了一個院子里,情況十分危急。父親斷后,離開時出不去了。情急之下,父親三下兩下爬上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樹,跳進隔壁一個村院,又縱身翻過后院子的高墻,跳進一條河里,潛水跑掉了。父親以后回到這個院子,重新把他那天逃跑的路線又走了一遍,他疑惑了,這三米高的墻,平常自己是無論如何翻不過去的,那天怎么神了?母親笑了:農村哪里有三米的高墻呢?你是急了,你沒聽人說狗急跳墻嗎?父親想想,自嘲地笑了。
1947年濮縣,有一天國軍來清剿,父親忙著組織撤退,突然發現母親還在村里,而敵人已經進了村子。賈伯知道后,帶了一人飛快騎車沖回村子,把母親架上車,一個在前,一個在后,一口氣狂奔了8里地才脫離險情。一次濮縣的幾個戰友在家喝酒,母親笑著對我們說:你這個賈伯伯,曾經救過你媽媽的命!
我們都敬佩地看著賈伯,賈伯也只是淡淡一笑:那次大姐要是被抓住了,就沒有你們一個個的小蘿卜頭嘍!
我發現,經歷過戰爭的人,看待生命顯然不同于常人,或許是看慣了生死,沒有普通人那么多愁善感。而在江湖上就不同了,會把它當作一件天大的事、命大的事。母親是有江湖氣的,1964年,她把本該分配給自己的提級指標讓給了賈伯,自己因此被擋在了中共高干序列之外。
大饑餓來臨的那年,家里忽然來了一群神色恓惶,饑腸轆轆的老家人,奶奶在用大鍋煮飯,父親神色凝重。家鄉竟然餓死人了,這幾個老鄉都是偷跑出來的。
父親時任財貿部長,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崗位,父親每天要為全市老百姓的蔬菜糧食揪心。記得父親成功組織到了南京市民每人每天一斤“飛機包菜”的定量,他陶陶然。當南京的糧食供應即將告罄之際,他從外地調來的糧食抵達了南京地界,他在江寧縣塵土飛揚的路旁看著糧車經過,興奮之極。
可是他個人,除了自己28斤的定量,拿不出多一顆的糧食。晚上,父母臥室的燈光,一夜未熄。多出7個人吃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父親第二天首先給所有他從老家帶出來的老鄉打電話,要他們送糧票,能送多少送多少,這樣十幾個老鄉湊了糧票100多斤。還不夠,父親又搞到200斤豆餅,50斤豆渣。父親不慌了,因為院子里還有父親種的滿園子蔬菜。可以挺過去了,父親松了一口氣。
就這樣,饑荒過去了。留在那段記憶中的是每天三頓亂七八糟的糊糊粥,曬在簸箕里的各種次食品散發著霉味……父親說他沒有能力救全體老家人,但是老家人來了,看到了,就不能不管。
父親家鄉一半人餓死,而這些逃來南京的老鄉活下來了。以后,零星逃難的老家人從未斷過,每次,父親都要想辦法搞一點東西填飽鄉親的肚子,糧票成了我家的珍寶,以至糧票廢除時母親悵然若失:格老子的,說沒用就沒用了?
她手上還藏著若干準備應急的糧票。
一天下午放學回家,三樓閣樓的兩間房空了,老家人走了,母親正在指揮家人燒開水,燙被單,消滅里面的虱子。“客走主人安,”母親說。
我感到一絲惆悵,記起了和他們在一起近四個月的歡樂時光。
老鄉里有個豁子叔叔,因為是兔唇,說話甕聲甕氣,可是我和他最親,他會做各種各樣的小玩具:竹勺,竹哨……,更讓我驚奇的是他將一片樹葉放在嘴里,就能吹出各種鳥叫。尤其記得他帶我們兄弟到紫金山上挖草藥,我站在山上對著空谷大喊,回音繚繞……
1964年他來南京,父親為他找醫生動了手術,治好了他的兔唇。
文革期間一天深夜,他來到南京對父親說,如果在南京有危險,你就回老家,有我們在,誰敢動你?……我看到了豁叔的真性情。
豁子叔曾有一天,手里握著一把米,甕聲甕氣地對我說:哎,一把,就這么一把米,熬碗粥,一條命,一條命啊!豁叔滿臉的悲愴震撼了我一生。從此,一把米一條命,在我腦子里成為了生命的方程式,至今,在餐館吃過飯,只要有剩,我都打包。兒子問:這些剩菜剩飯隔夜就壞,你想干什么呢?我說:一把糧食一條命。兒子很不以為然,將它們從冰箱里清出扔掉,問:健康呢?
是啊,現在的人講究的是健康,講究的是長壽,講究的是生活質量;而當年的人,講的是生死,講的是仁義,講的是信仰。“什么時候我要給你好好講講爺爺奶奶那輩人的事。”我喃喃地對兒子說。
父親的晚年,寧靜如水。離休后遠離了權力中心,家里往日的車水馬龍漸漸趨于清寂。每天天沒亮父親就出了門,他在離家一里的半徑內,緩緩地走著,一個多小時后,他回到家里,天已大亮。父親也就完成了一天的早鍛煉。
物質的豐富超越了我們曾經能夠有的想象,父親不在院子里種菜了,菜園子的功能有了改變,他開始種花,玩盆景,我又給他買了一只鸚鵡,這只會學舌的美麗的鳥,每天重復著的幾個單詞,帶有中原口音。
父親的離休生活,平淡得就像一個農民。沒有人可以想象,這個步履蹣跚的老人曾經殺過人,殺過很多,也砍過人頭,砍過無數,并曾經多次把寒光閃閃的刺刀,拼力刺進日寇的胸脯……
世紀之交的兩千年之秋,父親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父親的一生,經歷了軍閥混戰,民族救亡,中原逐鹿,改朝換代。和現代人相比,可謂波瀾壯闊。他現在走了,完成了一個社會個體細胞從誕生,分裂,成長,旺盛,衰弱,死亡的全過程。
他,不是什么偉人,可以引領千軍萬馬,爭雄天下。他,不是什么學科泰斗,學富五車,留下傳世之作;他不是什么經世偉才,創典立科,惠澤普天大眾。他,只是一個普通人。有著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的情感,傳統繼承,是非判斷。
他曾經的理想,是做一名鄉村教師,傳道解惑,教書育人。可是在一個大歷史時期,他以一粒沙子之勇投入另一種人生。這種抗御外侮的樸素的民族情緒,不需要任何人的引領教誨,它來自數千年在民間口口相傳的楷模,來自岳武穆,文天祥……
父親走了,永遠地走了。他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英雄,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打過小日本的老百姓,來自農村,來自中原地區一個名叫柳子集的貧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