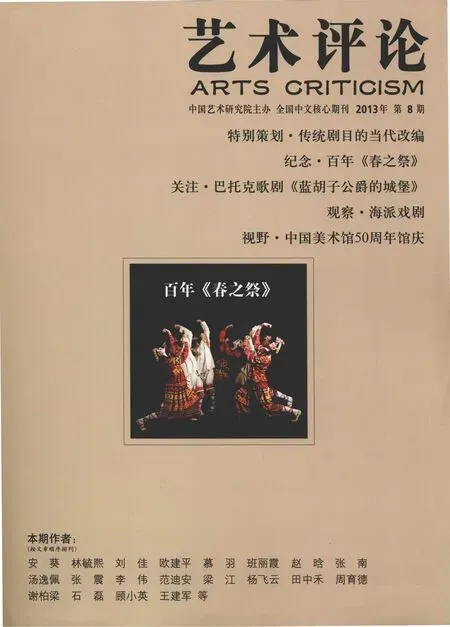海派·劇作家
郭晨子
一
上海而今被稱作“魔都”,請教過新老上海人因何得名,語焉不詳,但似乎又都默認(rèn)了這雅號。這“魔”,是“魔術(shù)”般的神奇?“魔鬼”般的摧殘?是這座城市有“魔幻”的屬性還是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有點“瘋魔”?這是驕傲還是自貶?是膜拜還是戲謔?是上海被非上海人妖魔化后的稱呼、還是指認(rèn)上海會妖魔化非上海人?
都是,又都不是。
但和“魔都”的諢名一致,海派好像也帶有某種不大正宗、不大正經(jīng)、不大正派的意思,缺乏某種“響當(dāng)當(dāng)”、某種正當(dāng)性。又因其不“正”,可以有無限的別樣的空間。那么,需要“正”嗎?如果“正”本身就意味著話語權(quán),不“正”也罷?
本文將要論述三位當(dāng)代的上海劇作家,沒有征求過他們本人的意見,不知他們是否愿意認(rèn)領(lǐng)海派的烙印。他們都生于上世紀(jì)五十年代,他們在從事編劇之前都有過或知青或工廠的生活經(jīng)歷,他們都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xué)院戲劇文學(xué)系,他們時至今日都還在寫作舞臺劇,他們都有研習(xí)西方戲劇乃至現(xiàn)代派、后現(xiàn)代戲劇的學(xué)術(shù)背景,特別是,他們的劇作都寫過上海,不是寫一個發(fā)生在上海的故事,而是情節(jié)和人物抽離上海就不存在——他們何嘗不海派?他們寫出過“魔都”的“魔”性。
他們是曹路生、張獻(xiàn)和趙耀民。
二
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永遠(yuǎn)是名正言順的,一個遠(yuǎn)離草原的蒙古漢子聽到馬頭琴和長調(diào)嗚咽了,一個久別巴蜀大地的四川游子吃到麻辣燙痛快了,一個山東人自豪來自孔孟之邦,一個陜西人或東北人自得地講著方言,都沒有問題。但一個上海人公然愛上海就會迎來全國人民狐疑的目光,目光中有對上海人自成一體的既鄙夷又艷羨、既疏離又好奇的復(fù)雜態(tài)度。哪怕這“公然”依然是私密的,是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行李里的大白兔奶糖和醬油膏。
盡管狐疑去,海派劇作家們不能因為家鄉(xiāng)是上海就不好意思愛了,相反,他們愛上海的方式就非常上海,是公然的又是私密的。例如生于1955年的張獻(xiàn),1970年隨父母內(nèi)遷昆明,1978年考入上海戲劇學(xué)院重返上海,接著又因和外國留學(xué)生的接觸入獄,等他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再次回到黃浦江邊,聽到路邊穿睡衣的老婦用上海話談家常,立即落淚。例如生于1951年的曹路生,他的口袋里常放著《東方早報》、《新聞晨報》,都是上海的本埠報紙,隨意翻看著。這或許不是最典型的細(xì)節(jié),但也很少看到別的城市的作家開會前、路途上隨手拿出報紙且是本地報紙吧?報紙不是書,沒有裝點的作用,只是一種對這座城市的關(guān)切習(xí)慣。例如生于1956年的趙耀民,已經(jīng)移居加拿大的他每年定期回國給研究生授課,曾有一年連續(xù)發(fā)表兩篇博文,題目分別是《上戲周邊租房指南》和《上戲周邊咖啡地圖》,事關(guān)安居事關(guān)生活習(xí)慣,是點點滴滴的,是上海人在意的點點滴滴。
他們出生在上海已經(jīng)漸漸失去上海特色的年代,但不經(jīng)意,他們的感受中,上海頑強存在!睡衣、老婦、方言、家常,大都市里活著的都是小市民,無論經(jīng)歷了怎樣的變故,總要有日常、有常態(tài),上海從來不缺市民的“過日腳”的狀態(tài),是平庸的也是撫慰的,是損耗的也是建設(shè)的。
再如看本埠報紙,不僅是關(guān)心本地新聞,也有著另外一種承繼,上海本是全國出版業(yè)最發(fā)達(dá)的地區(qū),上海曾出現(xiàn)過種類繁多的報刊雜志,在現(xiàn)代出版業(yè)、傳媒史上都是其他城市不可比肩的。報紙和上海人有著更親密的關(guān)系,是和柴米油鹽醬醋茶一樣的開門的第八件事。
至于租房子和喝咖啡,包含了生活方式里的西方化,無需標(biāo)榜,一標(biāo)榜反而矯情,流水賬似的記下了,不當(dāng)回事又是回事,是上海生活本身。
睡衣和方言、報紙和咖啡,所有的上海,不經(jīng)意間都在指向過去,都在逆流,都在回溯,都帶著不可磨滅的舊日痕跡。
三
他們筆下的上海也是這般。
1993和1994年,張獻(xiàn)創(chuàng)作的《美國來的妻子》和《樓上的瑪金》先后搬上舞臺。對上海戲劇界而言,這兩出戲才是所謂白領(lǐng)戲劇的鼻祖,之前一直投身先鋒戲劇的張獻(xiàn)忽然有了向市場邀寵之作,一時令人乍舌。兩個戲的風(fēng)格都是寫實主義的,臺詞異常密集,關(guān)注的是當(dāng)時最受社會熱議的話題,比如,要不要出國,比如,關(guān)于期貨、妓女和“臺巴子”(上海人對臺灣人的稱呼)。以《美國來的妻子》為例,該劇書寫了一個離開上海的上海妻子對出國的感受和一個留在上海的上海丈夫的嘆息,前者代表著上海人對西方的親近,出國倒像是還愿,后者落寞地優(yōu)雅著,傷感于上海越來越不像上海。這兩出已然有了民間資本介入和明星演員加盟的演出,遠(yuǎn)比今日之“都市情感”劇登樣!
后來有評論者指出,上世紀(jì)九十年代的上海遭遇“后發(fā)”開放,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帶來城市個性的蘇醒和民間社會的復(fù)蘇。而張獻(xiàn)在當(dāng)時就是有清醒認(rèn)識的,他要做“對”的戲劇而不是“好”的戲劇,“好”指的是美學(xué)意義上的好,而“對”是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指戲劇要向類型化、市場化、專業(yè)化發(fā)展。何謂“對”的戲劇呢?他制定了一個二十要二十不要的原則,“要話劇劇場,不要綜合劇場;要城市,不要農(nóng)村;要當(dāng)下,不要過去;要寫實,不要表現(xiàn);要個人生活,不要公眾生活;要新的身份職業(yè)人物,不要舊的身份職業(yè)人物;要地方化,不要國家化;要大眾,不要小眾;要俗,不要雅;要時尚,不要永恒;要人物少,不要人物多;要人物貫穿到底,不要間斷更換;要線性順時針平鋪直敘,不要逆時針插曲閃回;要表演快,不要慢;要室內(nèi),不要室外;要一景到底,不要遷換景;要低成本,不要高成本;要售票,不要送票;要高票價,不要低票價;要小劇場多場次,不要大劇場少場次。”

趙耀民,《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張獻(xiàn),組合嬲《舌頭對家園的記憶》
對于這一歷史階段的話劇,從選材、制作、風(fēng)格,從前期策劃到編劇策略再到市場定位,張獻(xiàn)清晰地做了規(guī)劃。偏頗的一言以蔽之,也可以說是要上海、要很上海,不要不上海。要上海的地域特征,要上海的生活特點,要都市才有的新的身份職業(yè)和時尚,這些,都和上海開埠后曾經(jīng)有過的以職場為代表的市民社會形態(tài)息息相關(guān)。而要售票、要大眾、要俗,乃至于在劇場美學(xué)上要趨向于保守的寫實主義,這是另一種對市民社會審美習(xí)慣的迎合。
是的,張獻(xiàn)有意識地要恢復(fù)上海“市民劇場”的傳統(tǒng),“新的市民文化在形成中,話劇作品應(yīng)該反映、表現(xiàn)新現(xiàn)實,在新現(xiàn)實中尋找新的倫理價值,建立新的共同經(jīng)驗,玩味共同情趣,把尚處邊緣的新文化逐漸主流化。”
而在張獻(xiàn)劇作的研究者殷羅畢看來,這兩部話劇標(biāo)志著一再受到鄙薄的上海小資產(chǎn)階級的城市生活價值終于有了一次正面的表達(dá),張獻(xiàn)自稱的肥皂劇般的密集臺詞里實質(zhì)上浸透了上海人幾十年來被壓抑而不滅的價值觀,幾乎是“論壇戲劇”。
不僅與此,張獻(xiàn)還提出過用上海話演話劇,就像香港人的粵語話劇一般。上海方言話劇并非上海土產(chǎn)的另一個戲劇品種——滑稽戲,在這里,張獻(xiàn)認(rèn)為用上海話演出是上海人的公民權(quán)利。無獨有偶,劇作家曹路生也一直有同樣的呼吁,并在2013年5月上演的由他任編劇的《永遠(yuǎn)的尹雪艷》中實現(xiàn)了這一想法。和用四川方言演出《死水微瀾》、用陜北方言演出《白鹿原》不同,上海方言話劇不僅試圖用方言更準(zhǔn)確地刻畫人物,還有一種對長期遭到冷嘲熱諷的上海群體性、獨特性的反彈。
只有在上海,對于把看話劇當(dāng)成生活習(xí)慣可以說是“恢復(fù)”。
四
伴隨著上世紀(jì)九十年代起上海經(jīng)濟地位的蒸蒸日上,對老上海的懷舊性文化消費成了另一景觀。海派的劇作家們做了些什么呢?
前文提到曹路生改編了白先勇原著的《永遠(yuǎn)的尹雪艷》,趙耀民則把同樣出自于白先勇之手的《永遠(yuǎn)的金大班》搬上舞臺,并完成了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的話劇文本。
《永遠(yuǎn)的尹雪艷》也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也罷,都收錄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中,“她”們已然是“臺北人”,是帶著對上海風(fēng)華無限眷戀與不舍的寶島新移民,空懷有一襲海上繁華舊夢。兩位劇作家的改本中,百樂門舞廳中的一幕幕光景都被還原了,把小說中回憶的部分變成舞臺場面是編劇技術(shù)的需要,也無意識地形成了與白先勇小說原著的互補。小說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jì)六十年代中后期,隔了二十年的光陰和海峽細(xì)訴往日旖旎,重心是在不如意的臺北,戲劇改編則完成在新世紀(jì)之后,續(xù)連了上海而臺北那一端是上海的延續(xù)。如果說,張獻(xiàn)的兩部作品是用當(dāng)下來廓清上海和上海人的面目,白先勇小說的改編則是用對“東方巴黎”的記憶打撈復(fù)制出一個舊上海來。不再以“市民戲劇”接通市民文化傳統(tǒng),而是直接搬演過去的傳奇。
《長恨歌》不同,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原意是唱反調(diào)的,選美小姐出身弄堂,后來的大半生也在粗鄙市民的包圍下渡過,死得尤其沒有半點浪漫美感,上海的“芯子”不是一般的務(wù)實,浮華都是做給人看的。文學(xué)批評家陳思和稱,王安憶這部在海派文化中不和諧的《長恨歌》恰恰是海派文學(xué)的典范。
在趙耀民的改編中,最為觀眾津津樂道的是一場打麻將的戲,其時的王琦瑤做了王護(hù)士,鄰居們常聚在一起玩牌。作家孫甘露發(fā)表在《文匯報》上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在一個泛交際花時代,妖艷早已不是她的重要特征。也許從來就不是。這在臥室里開放的秘密之花,委自凋謝,把人們對庸常拮據(jù)的家庭生活的厭倦,通過牌桌上的閑言碎語得以緩解。有意思的是,王琦瑤的困境正是源自于實際和幻想的‘言語’。這個故事改編成話劇,可謂適得其所。”他把《長恨歌》稱為“一位上海女子的隱秘生活”,“對這個形象的吹毛求疵,大約意味著,在潛意識里,想賦予這個‘居家’的特殊人物更多的‘合法性’。因為上海的生活對于女性的姿色有著太多的訴求,因為她幾乎就是今日人們的親友、姐妹、子女,甚至已經(jīng)不太年輕的母親。”王琦瑤是搔首弄姿的嗎?不,也許是隱忍內(nèi)斂的,因為“她既想讓人知道,又不想讓人知道。”
——這說的是王琦瑤,還是上海?
五
有這樣的一個“魔都”,必然牽扯到對“帝都”的看法,正如海派相對于京派。
當(dāng)2003年國家話劇院帶著《趙氏孤兒》、《青春禁忌游戲》、《薩勒姆女巫》和《戀愛的犀牛》來滬演出,一種要以經(jīng)典震撼上海話劇的氣勢撲面而來,國家名頭的劇院和劇目是“大氣”的,而上海觀眾是“小資”的,以小對大,除了屏氣凝神接受啟蒙教育外別無他路。上海早已經(jīng)對北京的文化氣場俯首稱臣,直至劇作家趙耀民寫了一篇題為《國家話劇的文化態(tài)度》的文章。
文中指出,“國話”無愧代表了目前中國話劇的一流水準(zhǔn),然而,其在“這次演出活動和演出劇目中所流露或張揚的文化態(tài)度,則是落后的。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在劇目的宣傳炒作上,用單一、僵硬的文化價值觀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擺出一副‘戲劇傳教士’和‘文化救世主’的面目,令人反感;二是在這些劇目(《戀愛的犀牛》除外)的創(chuàng)作本身,還是高高在上地對觀眾進(jìn)行思想灌輸、道德說教、審美強迫;以致劇場里充滿壓抑、累人的氣氛,聲嘶力竭的叫喊,理性硬塊的投擲,聲光效果的轟炸……而那些說教大部分不是似是而非,就是無的放矢,甚至還因為嚴(yán)重脫離觀眾和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實際生存狀態(tài)而顯得虛偽和矯情。”
倘若不是在上海,國話的文化態(tài)度不會受到這種質(zhì)疑和批評吧?這是國話的也是帝都一向習(xí)以為常、不假思索的姿態(tài)。難道他們還不能是“戲劇傳教士”和“文化救世主”嗎?倘若他們不是,誰還會是?誰還配是?竟然敢不需要傳教士、甚至反感救世主嗎?
文中最后說,“好在上海的話劇人雖然‘小家子氣’,還不至于自欺欺人。所以,我們寧可‘媚俗’,也不要精神壓迫;寧可‘小資’,也不要沒落貴族;寧可觀眾把看話劇當(dāng)作‘談戀愛的佐料’,也不要他們連談戀愛也不看話劇;我們寧可承受一噸的‘文化垃圾’,也不要一毫克的‘文化毒品’,哪怕它被包裝成‘精品’,成為‘經(jīng)典’。不若此,‘國家話劇’怕只會成為‘廟堂話劇’;今天的‘主流話劇’怕只會成為將來的‘逆流話劇’。”
這種腔調(diào),是不是也只有上海?
六
必須說,曹路生、張獻(xiàn)、趙耀民三位劇作家的作品不是小資的、媚俗的、文化垃圾的。他們對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戲劇的浸泡使得他們各自都有帶有實驗意味的劇作。
曹路生的小劇場戲劇《莊周戲妻》顛覆了傳統(tǒng)戲曲《大劈棺》,《誰殺死了國王》解構(gòu)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他在任上海戲劇學(xué)院學(xué)報《戲劇藝術(shù)》編輯和副總編時,開辟了每年兩期的“外國戲劇專號”,介紹外國戲劇現(xiàn)狀,并編譯了《西方后現(xiàn)代戲劇》一書;趙耀民的《鬧鐘》、《天才與瘋子》等劇始終在實踐著別具一格的“荒誕喜劇”,他曾撰文,對敘述體戲劇的內(nèi)在悖論性、對荒誕派戲劇和中國語境的貌合神離等都有極為精準(zhǔn)的分析;張獻(xiàn)從早期的《屋里有貓頭鷹》、《時裝街》到嘗試取消語言的《擁擠》、《母語》再到近年來他組團的“組合嬲”,索性開辟了現(xiàn)代舞蹈劇場,他在上海民間戲劇組織的“下河迷倉”任藝術(shù)總監(jiān),不斷地介紹著各種先鋒和實驗的國內(nèi)外演出。張獻(xiàn)言,他的戲劇觀是和他的二十條原則反的,他最終要的是他在二十條里所不要的。
是的,他們堅持海派的戲劇可以不廟堂不教化,他們創(chuàng)作著和上海這座城市密切相關(guān)的舞臺劇作品,但他們的眼光從未局限于上海。他們內(nèi)心為上海焦慮,為上海的文化格局何時才能像紐約而著急,他們提出“市民戲劇”是因為市民戲劇曾經(jīng)中斷,他們用上海方言寫作是為了爭得方言的生存權(quán),他們寫著尹雪艷、金大班和王琦瑤,是為了不曾消失的上海基因,似乎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個原因——上海的被壓制,主觀的和客觀的,自身的和外來的。他們從來沒有與惡性海派同流合污,而今后誰來延續(xù)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海派劇作的新問題。
無需為海派正名或揚名,只要存在著,就是有“魔”的。
注釋:
[1] 參見《國家戲劇中的個人反戲劇——訪張獻(xiàn)》一文,《學(xué)術(shù)中國》2008-03-10,http://www.docin.com/p-395704638.html
[2] 同上。
[3] 原文見《上海戲劇》2003年第11、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