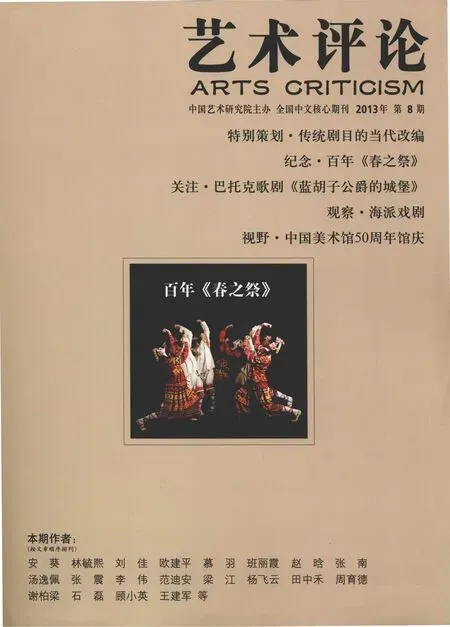海派話劇的沉淪
李 偉
近來,隨著上海風情話劇《亭子間嫂嫂》、滬語方言話劇《永遠的尹雪艷》的先后上演,關于“海派話劇”又成了坊間網上熱議的話題。
然而,在“海派話劇”這個概念之下,我們想到的遠不止這一類以上海方言為手段、以上海歷史、風情、民俗為表現對象的話劇作品。在這個概念之下,我們會聯想到夏衍、沙葉新、趙耀民、曹路生、張獻、宗福先、趙化南等劇作家,黃佐臨、胡導、楊村彬、胡偉民、陳明正、徐企平、谷亦安、熊源偉、雷國華等導演藝術家,焦晃、俞洛生、祝希娟、奚美娟、李媛媛、婁際成等表演藝術家,熊佛西、朱端鈞、顧仲彝、陳恭敏、陳多等戲劇教育家,我們還會想到《上海屋檐下》、《布谷鳥又叫了》、《于無聲處》、《假如我是真的》、《秦王李世民》、《屋里的貓頭鷹》、《蕓香》、《歌星與猩猩》、《原罪》、《白娘娘》、《莊周試妻》、《留守女士》、《OK,股票》、《公用廚房》等劇目,我們還會聯想到1980年代從上海發起的“戲劇觀”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中國戲劇界的思想,使戲劇舞臺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探索劇”。
“海派話劇”,從外延上看,指的是整個上海乃至周邊地區的話劇創作,但用“海派”而不直接用“上海”做前綴定語,還意味著從內涵上是對上海話劇所呈現出來的風格、特色、精神風貌的概括和描述。
“海派”,常常是和“京派”相對而言。其名稱的由來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有關。在當時“海派”并不是一個褒義詞。在自詡“京派”的人士那里,“海派”作家是“玩票白相”的不務正業,愛錢、商業化、作品低劣、人格卑下。反之,“京派”文人則心懷天下、憂國憂民、代表著精英文化和主流價值。但在魯迅眼里,這兩派都是有問題的,京派并不比海派好到哪里去。“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WWW.COM》

《武林外傳》

《永遠的尹雪艷》

《志摩歸去》

《長恨歌》
撇開當時的時代背景導致的意氣之爭不論,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分野確實存在。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文化差異很大。歷史上常常有南北文化風格不同論,又由于北京長期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代表著政治上的主流和文化上的正統;江南則一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遠離京畿,代表著新興的商業文明和文化上的邊緣與異端。所以,如果說“京派”意味著傳統、保守、正宗、政治氣、北國味,那么“海派”則意味著現代、開放、洋派、商業氣、江南味。然而現在經過建國后文化格局的調整以及近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全國通行,政治與經濟本身相輔相成,融為一體,北京與上海都是中國的大都市,上海也近官、北京也近商,北京未必保守,上海未必開放。區別似乎主要在方言與地域風情上了。然而這樣的看法是不夠的,也是不對的。
上海話劇,在解放前,幾乎就是大半部中國話劇史;解放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也可以看成是中國話劇的半壁江山。無論是解放前還是新時期,上海都在中國話劇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表現出包羅萬象、思想敏銳、勇于創新、敢為天下先的特點。北京的話劇,解放前根本不能和上海比;解放后,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統制下,北京作為共和國首都,一下子積聚了大量的戲劇人才,不僅有中央實驗劇院和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這樣的國家話劇院團,而且形成了北京人藝這樣以京味話劇為主要內容的代表國家水平的話劇藝術院團,與上海相比具有了明顯的比較優勢。新時期以來的上海和北京,本來一直上演著中國話劇的雙城記,但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這個雙城記呈現出越來越不平衡的態勢。上海話劇在原創能力上呈現出明顯的頹勢,越來越不能和北京相比。我們從近十多年來的京滬兩地話劇界的兩輪交流演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2003年國慶節黃金周,北京國家話劇院帶了《哥本哈根》、《青春禁忌游戲》、《趙氏孤兒》、《戀愛的犀牛》等四個戲到上海來舉辦“上海文化周”。這四個戲分別是國話最有實力、最當紅的因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導演藝術家王曉鷹、查明哲、田沁鑫、孟京輝的作品。總體上來看,演出非常成功,反響也很熱烈,國話用自己的實力賺夠了面子和銀子。在國家話劇院召開的座談會上,上海話劇界在為國話叫好之余,也表現出了些許謙虛和自卑。不過劇作家趙耀民以慣有的犀利指出了北京話劇的問題,認為北京話劇就知道板起面孔高臺教化,不如咱們上海戲劇平民化、生活化、接地氣,懂得戲謔解嘲。趙耀民的發言非常準確地指出了京派話劇和海派話劇之間氣質上的不同,也為上海話劇挽回了一點面子。次年7月,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也攜《蝴蝶是自由的》、《藝術》、《長恨歌》和《正紅旗下》等四個戲隆重進京,贏得了不少口碑。北京劇評家廖奔撰文說:這四臺戲“跨度大、風格各異,使人看到了其藝術創造力,更看到了海派文化的魅力。它廣納百川的包容性強,為我所用的氣魄大,中西勿論,它尤其把京派文化拿來,經過再加工之后,敢于送回發源地來經受檢驗。”另一位重要的劇評家宋寶珍直接以《上海話劇超過北京》為題,說:“‘海派話劇’的展演讓北京人既震驚又汗顏,不免要追問:‘當代中國話劇發展中心應該定位在哪里?’”這些贊譽雖然不免客氣,但總歸是對海派話劇的充分肯定,讓人以為兩地的話劇旗鼓相當,尚在同一個層面上。
十年之后的2012年7月中下旬,另一個京派話劇重鎮北京人藝攜《知己》、《原野》、《窩頭會館》、《我愛桃花》、《關系》等五個劇目南下,其劇目之精湛、表導演陣容之強大,再次攪動了上海話劇觀眾的審美胃口。人藝副院長、著名演員濮存昕自信滿滿地說:“我們的戲和現在一些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說什么的戲不一樣,我們做的都是落地有聲,實實在在的戲。”人藝的演出引發了上海全城的熱烈追捧,幾乎所有場次的門票都銷售火爆、一票難求。這一次沒有高臺教化的戲,也沒有翻譯、改編的戲,都是人藝的原創劇目,而且4部是新戲,只有1部是舊作新演。作為人藝60周年的紀念活動,這充分展示了她老樹開新花,充滿生機的原創活力。而在次年的2013年北京人藝舉辦的首都劇場精品劇目邀請展上,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帶來的三部最能反映當下創作狀態的作品——國外經典法庭話劇《原告證人》、現代題材原創舞臺劇《資本· 論》、2012話劇金獅獎作品《活性炭》,與以色列卡梅爾劇院的《手提箱包裝工》和蓋謝爾劇院的《唐璜》同場獻藝。無論是原創能力還是表演水平,兩者都相距甚遠。一直關注上海話劇的北京評論家宋寶珍說:“《原告證人》說到底是個類型化了的情節劇……是經濟視角下商業運作的產物……它承載不了更深刻的哲理與思想反思意義。”《資本· 論》的“文本沒有為演員提供開掘和表現的空間,因此他們只是作為話語符號而存在”。“《活性炭》主打溫情牌……讓人們惜緣、惜福,用智性與寬容,趕走歷史的陰霾與現實的塵埃,還心靈的天空以安然與純凈。”基本上可以說是反響平平。《資本· 論》甚至在網上被譏為思路混亂、根本不會講故事。這次北上可謂是鎩羽而歸。
說來也怪,上海近十年來能拿得出手的話劇,往往只是二度、三度創作在上海完成,而一度原創則都是請外地藝術家加盟。從十多年前的《商鞅》算起,編劇是南京的姚遠,《秀才與劊子手》編劇是北京的黃維若;《藝術》好則好矣,編劇是法國人;最近的《萬尼亞舅舅》贏得了少有的好評,然而導演和編劇都是俄國人。上海的戲劇谷,請了好幾位外地的戲劇名家來創辦工作室,如國家話劇院的孟京輝、田沁鑫,也不斷引進臺灣的賴聲川、香港的林奕華、毛俊輝等人的舞臺劇作品,但很少有上海的戲劇藝術家在北京做工作室(僅有曹路生先生為北昆創作的昆曲《舊京絕唱》和為總政話劇團創作的《九三年》等),也很少有上海的話劇作品在外地名利雙收、凱旋歸來(趙耀民的《志摩歸去》最近在北京等地巡演,效果如何尚待觀察)。而上海市劇協在2013年初發布的內部調研報告顯示,上海的原創劇目數量不到劇目總數的三分之一、45歲以下編劇短缺且缺乏領軍人物、創作力量疑似出現斷層。難道上海只能是來料加工廠和產品營銷地,僅僅是一個藝術產品的集散碼頭而已?上海話劇有沒有自己的原創能力?上海話劇為什么失去了曾經具有的原創能力?
上海也有一些原創戲票房很好,如喻榮軍編劇的“白領戲劇”系列,《愛情方程式》、《哈瓦那的一夜》、《www.com》等,獨領上海劇壇風騷十幾年,何念導演的所謂“減壓喜劇”如《武林外傳》、《羅密歐與祝英臺》、《資本· 論》等,移植的阿加莎系列所謂驚悚劇、懸疑劇,但這些戲看過也就看過、笑過也就笑過了,似乎難以引起人們的討論、思考,像一縷鵝毛飄落在水面上,難以引起一點漣漪。更別說轟動效應了。僅有幾臺主旋律話劇,獲得了政府的獎項,但其藝術水準如何,是很值得懷疑的。
和北京相比,上海話劇原創力的衰落已經是明顯的事實,制作能力的下降恐怕也是遲早的事。沒有一度原創的底蘊,導演、表演、舞美再強,也就是玩玩技巧而已,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原因何在?
2013年4月,南京的《蔣公的面子》和北京的《驢得水》,先后上演于上戲劇院,仿佛平地驚雷,在上海戲劇界引起了極大轟動,并很快在微博上也產生了關于上海話劇現狀的論爭。從這次論爭中可以窺見上海話劇的現狀及其形成的原因之一斑。
論者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思想性”的匱乏上。微博上“戲劇小寶貝”說:“這部劇(《蔣公的面子》)的價值就在于在近30年相對沉悶、禁錮、毫無思想建樹的戲劇氛圍中,用巧妙的方法樹起了思想性的旗幟,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和另一神劇《驢得水》是相得益彰、南北交輝。就像30多年前的《于無聲處》,無論成熟與否,地位不可撼動。”然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總經理楊紹林并不完全接受這一說法:“用中國戲劇三十年思想空白來贊美(疑為“否定”上海戲劇)是否欠缺理性”,因為“如此并不利于中國戲劇良性生態環境的營造”。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新生代導演何念甚至不認為戲劇需要“思想性”,他質疑:“思想性?我們現在該往哪里思考?思考出來了,怎么解決?解決不了不是心里更堵,不如不思考。”對此,“戲劇小寶貝”駁斥道:“沒有思考的戲劇是缺少靈魂的雜耍。在世界各國,都把戲劇視為文學藝術的最高樣式,沒有靈魂的戲劇能有這個擔當嗎?思考出來無法解決,說明戲劇環境的糟糕,但不能作為不思考的理由。”同樣,何念既不同意劇作家賀子壯關于“上海戲劇已經滑坡”的判斷,也不承認上海話劇原創力萎縮和文化生態萎靡的現實。他的理由是“我們的演出是全國最多的。阿加沙團隊一年有200場的演出場場爆滿,我們團隊一年也有150場千人劇場的演出。去年制作的音樂劇《女人一定要有錢》連續千人劇場72場,2月到5月持續演出《武林外傳》、《羅密歐與祝英臺》、《21克拉》、《撒嬌女王》,今年努力做到全年持續演出!這為什么還滑坡?”可見,何念根本不能理解“話劇滑坡”的真正內涵,以為票房就是一切,十分滿足于上海僅僅作為一個“演出的集散地”。只要小清新、小浪漫,拒絕大思考、大創造,無疑是海派話劇的沉淪。不過,他也承認,之所以不思考,是因為思考性的作品難以通過有關機構的審查。這就說明,上海的文化環境本身是很有問題的。何念在上海有“票房小蜜糖”之稱,他選擇的作品一般而言還是比較穩妥的。所以,“戲劇小寶貝”指出:“如果有能讓何導的選擇也過不了的機構,那可是一個真正的‘殺手’機構,是造成上海文化萎縮的‘主兇’。實質上只有兩種可能:要么何導承認自己‘反骨畢露’,要么就是不可否認有這樣惡化文化環境的專業機構。”這和濮存昕所說的:“北京人藝享受著很自由的創作環境,從來沒有政府部門對人藝的戲指手畫腳。”相距何止以萬里計。
上海戲劇界依然還在堅持話劇創作的三駕馬車:沙葉新、趙耀民、曹路生。沙葉新新近創作了《鄧麗君》、即將創作《汪精衛》,但只能在境外演出;曹路生改編了《江南好人》、《永遠的尹雪艷》,但被導演改得一塌糊涂,只見花哨的外表,華麗的舞臺景觀,而不見真正的海派精神,把一個深刻的揭露舞女悲劇命運的戲活生生地改編成了一個留戀上海風花雪月的懷舊的戲;還是趙耀民再一次為上海話劇掙回了一點面子,他的《志摩歸去》讓久違的上海劇壇看到了希望,但這希望也讓人很絕望:趙耀民本身在上海就很邊緣、很孤獨了,很好的劇本,三四年前就寫出來了,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直到今天才搬上舞臺。趙耀民之后,還能作何期許呢?思想內涵和形式技巧都全面探索的現代話劇《志摩歸去》,對趙耀民是必然,但對上海,則是偶然了。真正的話劇早已不再主流,而成為邊緣了。
上海話劇的主流現在是所謂白領戲劇、減壓戲劇和懸疑劇、驚悚劇等類型戲劇,這在話劇史家丁羅男教授看來是走上了文明戲的老路,在我看來則是話劇領域的“惡性”海派:只是唯利是圖、唯票房馬首是瞻,不再有精神追求、理想信念了。
顯然,走到今天這樣地步的原因,一是文化管制太甚,二是商業追求過急。兩相擠壓,上海話劇只能走上搞笑的狹路和自宮的邪路上去。這無異于飲鴆止渴、自取滅亡。
要想重拾上海話劇的輝煌,必須重振海派文化的精神。
海派文化和海派戲劇的精神實質就是自由創造,而不是表面的上海風情和方言。
1990年代初,有位上海劇作家曾經直言不諱地批評上海的文藝界說:“上海的藝術家可能什么也不缺,生活閱歷,文化素養,藝術感覺,創作技巧,應有盡有,唯一缺乏的是藝術家的勇氣和真誠。”他還說:“上海的藝術家則過于膽小拘謹而又乖巧玲瓏,因而最善于揣摩各種精神,最善于察言觀色、見機行事,或者說最‘拎得清’。”“他們始終不可能有恢宏博大的氣度,不可能有淪肌浹髓的深刻,不可能創造出與人民貼心貼肉的文章,不可能產生出振聾發聵的警世之作。”這些振聾發聵的批評,如果我們好好記取,或許還有重振雄風的希望。但如果我們完全不知道上海曾經擁有什么,因此并不知道失去了什么,反而覺得我們現在好得很,那么我們將永無復興之日。
*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重點項目支持。
注釋:
1. 魯迅《“京派”和“海派”》,《申報·自由談》,1934年2月3日。
2. 趙耀民《國家話劇的文化態度》,《上海戲劇》,2003年第11、12期合刊。
3. 廖奔《海派話劇的風格和實力》,《中國作家網》,2004年7月22日。
4. 宋寶珍《上海話劇超過北京》,《藝術評論》,2004年第9期。
5.《濮存昕:我們做的是落地有聲的戲》,《青年報》,2012年3月20日。
6. 宋寶珍、馬倩《玉蘭花開香自來》,《北京人藝》,2013年第2期。
7. 史學東《戲劇焦慮的鍋底》,《上海戲劇》,2013年第6期。
8. 相關引文見新浪微博@戲劇小寶貝、@楊紹林、@賀子壯老師、@何念,2013年4月8-9日。
9. 《濮存昕:人藝創作自由,不受政府干涉》,《京華時報》,2012年7月23日。
10. 沙葉新《繁榮上海文藝創作之管見》,《沙葉新的鼻子》,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