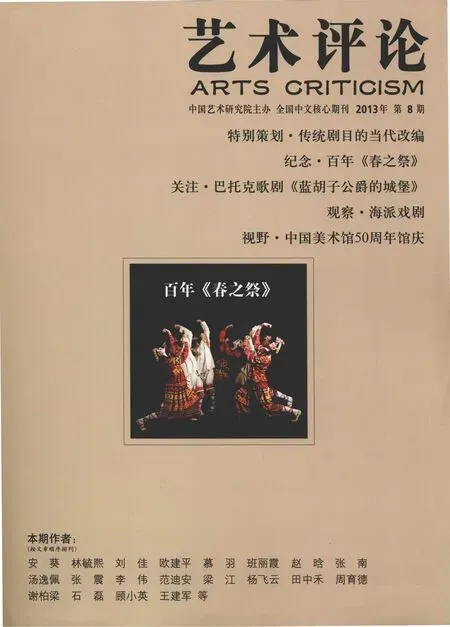《春之祭》何以成為音樂經(jīng)典?
班麗霞

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關(guān)于“經(jīng)典”(classic)的探討是當(dāng)下文藝?yán)碚摻绲臒衢T話題,尤其是文學(xué)與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已為這一研究提出不少有價(jià)值的理論與觀念,對我們思考音樂經(jīng)典及經(jīng)典化問題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就“經(jīng)典”的定義來說,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jīng)典》中提出,經(jīng)典就是“那些你經(jīng)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作品”。同理,音樂經(jīng)典也正是那些歷經(jīng)時(shí)間考驗(yàn),被一代代愛樂者反復(fù)聆聽和詮釋,從而彰顯出持久生命力的作品。在西方音樂領(lǐng)域,與“經(jīng)典”類似的表述還有“保留曲目”( repertoire,最常用)、“音樂杰作”(masterpiece)、“博物館作品”(museum piece)等稱謂,基本只限于“藝術(shù)音樂”或“嚴(yán)肅音樂”的范疇。自巴赫、亨德爾兩位巴洛克晚期的音樂大師開始,經(jīng)維也納古典樂派至19世紀(jì)多位浪漫主義 “天才”的杰作,共同構(gòu)成了西方音樂經(jīng)典曲庫的主體部分。
與文學(xué)和視覺藝術(shù)經(jīng)典一樣,音樂作品經(jīng)典地位的確認(rèn)也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經(jīng)歷了或長或短的“經(jīng)典化”過程,像巴赫的《馬太受難樂》(1727)就為之等候了上百年的時(shí)間。音樂經(jīng)典在19世紀(jì)中葉之后逐步占據(jù)音樂廳,將音樂廳轉(zhuǎn)變?yōu)橹饕涎荼A羟康摹耙魳凡┪镳^”。與藝術(shù)博物館相似,音樂廳背后所遵循的也是“審美自律性”(aesthetic autonomy)的原則,“即藝術(shù)音樂應(yīng)該以自足的權(quán)利供聆聽鑒賞,而不是在一個(gè)占據(jù)支配地位的非音樂過程中服務(wù)于某種功能。”“音樂博物館”的長期存在,對整個(gè)音樂世界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它將不符合其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低劣之作、民間音樂、流行音樂、實(shí)驗(yàn)音樂排斥在外,又通過一系列謹(jǐn)而慎之的遴選過程,將更早(如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或更晚(如20世紀(jì))的經(jīng)典作品收納其中,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1913)就是少數(shù)被音樂廳“收藏”的現(xiàn)代音樂經(jīng)典之一。影響音樂經(jīng)典建構(gòu)的因素非常復(fù)雜,常常既有藝術(shù)的、審美的,也有文化的、歷史的。那么,《春之祭》究竟具有哪些“經(jīng)典性”?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經(jīng)典化”歷程?這正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一、《春之祭》的音樂原創(chuàng)性
從藝術(shù)與審美的角度來說,“原創(chuàng)性”是一切經(jīng)典作品的首要特征,也是遴選經(jīng)典的首要條件。美國學(xué)者哈羅德·布魯姆在維護(hù)經(jīng)典之權(quán)威的著作《西方正典》中提出:“任何一部要與傳統(tǒng)做必勝的競賽并加入經(jīng)典的作品,首先應(yīng)該具有原創(chuàng)魅力。”將原創(chuàng)性作為西方音樂歷史書寫中支配性的美學(xué)前提屢屢遭遇質(zhì)疑,因?yàn)樗鼔焊贿m用于18世紀(jì)之前的以功能性為主導(dǎo)的音樂寫作。但就19世紀(jì)以來形成的經(jīng)典概念來說,原創(chuàng)性無疑有著根本的意義。面對前輩大師留下的經(jīng)典范例及其神圣權(quán)威,新一代藝術(shù)家總要面臨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他認(rèn)為,能否擺脫前代大師的創(chuàng)作模式并彰顯自身的獨(dú)創(chuàng)性,既是天才與庸才的根本區(qū)別,也是形成新的經(jīng)典的必要條件。
作為芭蕾舞劇的《春之祭》,其原創(chuàng)性的體現(xiàn)是全方位的。第一次觀看這部舞劇的觀眾,無論從哪一個(gè)角度——音樂、舞蹈、情節(jié)、服裝、布景——都能感受到它突兀的新意。有趣的是,這部作品背后的藝術(shù)統(tǒng)帥劇院經(jīng)理佳吉列夫,在其藝術(shù)執(zhí)導(dǎo)中遵循著嚴(yán)格的等級制度:“第一是音樂,第二是編舞,也就是翻譯成動(dòng)作的音樂,第三是布景和服裝,當(dāng)然前提是與音樂相適合。而腳本,也就是情節(jié)則是次要的。”這樣的等級安排讓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主導(dǎo)了整部舞劇的基調(diào)和氣氛,即便是脫離舞臺而采用音樂會(huì)的形式,似乎也不影響其音樂的完整性與表現(xiàn)力。
在《春之祭》的音樂中,最具“革命性”的姿態(tài)首先體現(xiàn)在節(jié)奏上。在它之前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藝術(shù)音樂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表現(xiàn)要素是音高。以音高為基礎(chǔ)的旋律歷來是情感的載體、創(chuàng)作的核心;由音高組成的主題動(dòng)機(jī)與調(diào)性和聲,更是支撐作品整體架構(gòu)的基本手段。但《春之祭》卻徹底推翻音高的統(tǒng)治,將節(jié)奏從機(jī)械單一的傳統(tǒng)律動(dòng)中解放出來,并賦予其近乎主題的地位和功能。樂曲中的旋律、和聲、調(diào)性、織體、力度、速度等因素均以節(jié)奏的表現(xiàn)為核心,使音樂以前所未有的狂暴和粗野直穿耳膜、撞擊心靈。《春之祭》在此挑戰(zhàn)的不僅是前代作曲家的經(jīng)典范例,還有1913年5月29日參與此作首演的藝術(shù)家與聽眾。早已習(xí)慣欣賞優(yōu)雅音樂與高貴舞姿的巴黎觀眾,在舞劇一開場就出現(xiàn)騷動(dòng),人群中逐漸爆發(fā)的噪音幾乎淹沒了整個(gè)樂隊(duì)。據(jù)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回憶,指揮家蒙特“像鱷魚那樣不急不躁”,堅(jiān)持將樂曲演奏到最后;舞劇編導(dǎo)尼金斯基站在側(cè)幕的一張椅子上,大聲叫喊著數(shù)字以指揮舞蹈的進(jìn)行;佳吉列夫“忽開忽關(guān)地操縱演出大廳的燈光”,希望以此平息混亂;而作曲家自己則怒氣沖沖地站在尼金斯基背后,一直到演出結(jié)束。

1913年《春之祭》 手稿
斯特拉文斯基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實(shí)現(xiàn)其對節(jié)奏的革命:一、在看似常規(guī)的節(jié)奏模式中采用不規(guī)則的重音移位;二、在正常的節(jié)奏進(jìn)行中臨時(shí)附加音符;三、讓兩種不同時(shí)值的節(jié)拍同時(shí)進(jìn)行,造成節(jié)奏的縱向錯(cuò)位;四、異常頻繁地變換節(jié)拍,在某些段落中甚至達(dá)到一小節(jié)一換的程度。除了單純的節(jié)奏節(jié)拍,《春之祭》的節(jié)奏表現(xiàn)力還離不開其他要素的輔助與烘托,如持續(xù)強(qiáng)勁的力度,固執(zhí)反復(fù)的音型,刺耳不協(xié)和的和聲等。所有這些處理方式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的節(jié)奏律動(dòng),使《春之祭》充盈著一種原始粗獷的自然力量,像是直接從地底深處升騰出來的。這種力量既洋溢著生命,又昭示著死亡,被選少女的獻(xiàn)祭象征著遠(yuǎn)古人類與自然、與土地的渾融一體。斯特拉文斯基曾在一封書信中談及這部作品,他說:“我的作品傳達(dá)了人類與地球的、人的生命與土地的緊密聯(lián)系的感情,我嘗試通過強(qiáng)勁的節(jié)奏來達(dá)到這一點(diǎn)。這個(gè)少女必須自始至終在舞蹈。我不允許她有一小節(jié)靜止。”
當(dāng)然,《春之祭》對傳統(tǒng)的反叛并不僅僅局限于節(jié)奏。為了與德奧浪漫主義音樂劃清界限,斯特拉文斯基極力控制弦樂的抒情性,避免由它演奏長線條的旋律,因?yàn)橄覙匪赜械氖闱樘刭|(zhì)很難抹去浪漫主義的色彩。這種做法在斯特拉文斯基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始終存在。《春之祭》唯一長線條的主題出現(xiàn)在序奏開頭,這段出自立陶宛的民間曲調(diào)是由巴松管獨(dú)奏的,對于這件低音木管樂器來說,這個(gè)主題的音高遠(yuǎn)遠(yuǎn)超出它的正常音區(qū)。與弦樂地位的下降相反,銅管樂與打擊樂因著粗野氣氛與節(jié)奏表現(xiàn)的需要而獲得巨大的表現(xiàn)力。在作品的多處段落,作曲家甚至將弦樂和管樂均變成節(jié)奏性樂器,例如《春天的預(yù)兆》開頭,像是擊鼓蹬足的猛烈節(jié)奏主要是由弦樂在低音區(qū)演奏的;在《大地之舞》與《當(dāng)選少女的祭獻(xiàn)舞》中,音樂的所有表現(xiàn)要素都被卷入節(jié)奏的狂嘯中,樂器音色與旋律的個(gè)性均被抹殺,整個(gè)樂隊(duì)變成一個(gè)巨大的打擊樂組。
《春之祭》的原創(chuàng)性是獨(dú)一無二的,它比此前兩部芭蕾舞劇《火鳥》與《彼得魯什卡》更加遠(yuǎn)離“五人團(tuán)”代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其音樂語言的個(gè)性化如此突出,使得其后的作曲家難以仿效它的風(fēng)格,因?yàn)槟呐轮挥袛?shù)小節(jié)的模仿,也會(huì)立刻浮現(xiàn)《春之祭》的影子,甚至包括斯特拉文斯基自己也極力避免自我重復(fù)。面對這樣一部特立獨(dú)行的作品,音樂評論家很難找到一個(gè)合適的術(shù)語來表述它的風(fēng)格,于是乎再一次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視覺藝術(shù)領(lǐng)域,并從那里再度借來一個(gè)時(shí)髦詞匯——原始主義。
二、《春之祭》的傳統(tǒng)繼承性
對《春之祭》的反應(yīng)與評價(jià)在不同時(shí)期有不同的傾向。在首演的大騷亂中,支持者與反對者盡管持相互沖突的立場,但他們所關(guān)注的都是作品的“新”。反對者譴責(zé)它粗暴踐踏了傳統(tǒng),支持者則贊賞它包含了自由與新奇。在首演之后的第二年(1914),《春之祭》以音樂會(huì)形式再度演出于巴黎,作曲家認(rèn)為這是一次輝煌的平反。據(jù)說音樂結(jié)束之后,青年觀眾高呼著斯特拉文斯基的名字,將他抬到大街上接受人們的祝賀。在意大利,未來主義者們還在街道游行中打出這樣的標(biāo)語:打倒瓦格納,斯特拉文斯基萬歲!可見,在《春之祭》問世之初,最吸引觀眾目光的主要是它的革命性與現(xiàn)代性。但事隔六七十年之后,這一傾向明顯發(fā)生了改變。美國音樂學(xué)家漢森在其著述中將《春之祭》定位于“過去時(shí)代的東西——一個(gè)屬于晚期浪漫派的作品”。盡管筆者并不完全贊同他的說法,但他重新審視《春之祭》之“舊”的傾向卻值得我們思考。
其實(shí),對《春之祭》的評價(jià)有如此大的轉(zhuǎn)向并不奇怪,與斯特拉文斯基同處現(xiàn)代主義第一階段的作曲家,如理查德·施特勞斯、勛伯格、貝爾格的作品,同樣經(jīng)歷過這一轉(zhuǎn)向。奧地利作曲家勛伯格對調(diào)性音樂的突破和十二音體系的開創(chuàng),在20世紀(jì)初期有著毋庸置疑的先鋒性,他的1908年之后的作品,也屢屢在首演中遭遇騷亂。但就在勛伯格剛剛?cè)ナ溃?951)之后,屬于現(xiàn)代主義第二階段的法國作曲家布列茲就發(fā)表了一篇評論,標(biāo)題為《勛伯格死了》(1952),這篇看似頌揚(yáng)性的訃告,實(shí)則是宣告與勛伯格所代表的傳統(tǒng)決裂。盡管這篇評論缺乏理性的批評意識,但勛伯格與古典音樂傳統(tǒng)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卻首次得到強(qiáng)調(diào)。就《春之祭》來說,站在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當(dāng)我們看過20世紀(jì)花樣翻新、無奇不有的現(xiàn)代音樂圖景之后,再來“俯瞰的凝視”這部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它與古典傳統(tǒng)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不妨先將《春之祭》與20世紀(jì)其它的先鋒派音樂做個(gè)比較:與魯索羅的噪音音樂相比,《春之祭》的音響雖然有些 “粗糙”,但仍屬樂音體系;與哈巴的微分音音樂相比,它仍然循用十二平均律的全音半音體系;與布列茲的整體序列音樂相比,它顯然不追求如此全面的理性控制;與約翰·凱奇的偶然音樂相比,它對樂譜和演奏者有更嚴(yán)格細(xì)致的要求;與施托克豪森的電子音樂相比,它仍在使用傳統(tǒng)的管弦樂隊(duì);與美國的簡約派音樂相比,它對技術(shù)復(fù)雜性的追求似乎不遺余力。通過這一系列比較,《春之祭》在問世之初所顯露的叛逆與革新就不再那么令人驚奇,而與古典音樂傳統(tǒng)的承繼關(guān)系卻越來越凸顯出來。如果進(jìn)一步對音樂本體做細(xì)部分析,還會(huì)發(fā)現(xiàn)更多的傳統(tǒng)特征:如樂思或動(dòng)機(jī)的反復(fù)與貫穿;對傳統(tǒng)三部曲式、回旋曲式的運(yùn)用;間或出現(xiàn)的民歌風(fēng)格的主題旋律;雖現(xiàn)多調(diào)性但尚未脫離調(diào)性的范疇;等等。除此之外,漢森將《春之祭》歸為“晚期浪漫主義”主要參照了它的三個(gè)特點(diǎn):一、音樂語言的復(fù)雜化;二、與文學(xué)、戲劇等姊妹藝術(shù)的合作;三、技法的創(chuàng)新服務(wù)于特定內(nèi)容的需要。他認(rèn)為《春之祭》在這些方面明顯延續(xù)了19世紀(jì)音樂的傳統(tǒng)。
美國音樂學(xué)家伯克霍爾德曾專門論及20世紀(jì)的“博物館作品”,《春之祭》亦列其中。他提出,盡管20世紀(jì)音樂表面看來紛繁復(fù)雜,不存在風(fēng)格一致的趨向,但其中依然存在著一個(gè)“歷史主義主流”(the historicist mainstream)。這個(gè)主流從勃拉姆斯的時(shí)代延續(xù)至今,其特征就是創(chuàng)造性地延續(xù)傳統(tǒng),對其既有效仿又有突破。像理查德·施特勞斯、新維也納樂派、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等作曲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多以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德奧古典大師為典范,其共有的特征就是“追求永恒價(jià)值、專業(yè)技巧、鮮明的個(gè)人風(fēng)格,及與古典傳統(tǒng)的緊密聯(lián)系。”這是他們的作品被音樂廳遴選為保留曲目的根本原因。同理,那些一味標(biāo)新立異的實(shí)驗(yàn)派音樂,盡管有著絕對的原創(chuàng)性,但因無視對古典音樂傳統(tǒng)的承繼,因而注定與“音樂博物館”無緣。
三、《春之祭》的聲譽(yù)構(gòu)建與經(jīng)典化歷程
《春之祭》除了音樂自身所具有的經(jīng)典特性外,在其經(jīng)典化的歷程中,還受到音樂之外的多種因素的推動(dòng),這其中,聲譽(yù)就是一個(gè)至關(guān)重要的因素。音樂社會(huì)學(xué)家威廉·韋伯曾經(jīng)提出,音樂中“古典”經(jīng)典的確認(rèn)及其被合法化為高雅藝術(shù)的現(xiàn)象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過大量音樂出版商、印刷者、經(jīng)紀(jì)人、音樂會(huì)促進(jìn)者、教育主辦者、教師和音樂家本人的積極活動(dòng)而促成的。也就是說,音樂作品的聲譽(yù)很少只是與音樂本身有關(guān),在《春之祭》的聲譽(yù)構(gòu)建中,這個(gè)基本由精英組成的群體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1913年《春之祭》首演劇照
首先要提及的是佳吉列夫,他是斯特拉文斯基人生中的“伯樂”,也是一位杰出的藝術(shù)活動(dòng)家、評論家和經(jīng)紀(jì)人。奠定斯特拉文斯基大師聲譽(yù)的三部經(jīng)典舞劇——《火鳥》、《彼得魯什卡》、《春之祭》——以及1929年之前的許多芭蕾舞作品都是在他的組織和指導(dǎo)下完成的。佳吉列夫以其對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敏銳感受與鑒別力,將眾多出類拔萃的“先鋒派”藝術(shù)家聚在一起并促成他們的合作。用今天的話語來說,這是一種“強(qiáng)強(qiáng)聯(lián)合”的藝術(shù)策略,不僅直接影響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與水準(zhǔn),還為作品的推出制造一種“品牌”效應(yīng)。與這些杰出的舞蹈家、畫家、劇作家的長期合作,使斯特拉文斯基尋求革新的愿望不斷受到激勵(lì),同時(shí)也為年輕的他帶來不小的聲譽(yù)。就《春之祭》而言,除了音樂,尼任斯基的編舞和廖里赫的美工同樣極富原創(chuàng)性,這部芭蕾舞劇在首演時(shí)產(chǎn)生的巨大沖擊力,是由這些藝術(shù)家合力創(chuàng)造的。
評論家、學(xué)者、教師對《春之祭》的關(guān)注,同樣參與了它的經(jīng)典化歷程。德國哲學(xué)家阿多諾曾在《新音樂哲學(xué)》一書中收入兩篇文章:《勛伯格與進(jìn)步》、《斯特拉文斯基與退步》,直截了當(dāng)?shù)貙?0世紀(jì)的兩位音樂革新家對立起來,并對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作出不太公允的批判。針對《春之祭》這部作品,阿多諾承認(rèn)它在音樂語言和技法上有許多大膽的“革命”,但對其中的思想傾向卻大加鞭撻。他認(rèn)為,把一位無辜的少女送上祭壇是對人性的一種殘暴的摧殘,“音樂在面對這種瘋狂的、神經(jīng)錯(cuò)亂的兇殺儀式時(shí),只是一種令人恐懼的、震撼的聲音,而似乎并沒有悲痛的表現(xiàn)。”阿多諾以單一的社會(huì)學(xué)標(biāo)準(zhǔn)來論斷《春之祭》的藝術(shù)價(jià)值,結(jié)論明顯缺乏說服力。但是,阿多諾作為20世紀(jì)影響最大的哲學(xué)家之一,他對斯特拉文斯基和《春之祭》的遴選與批評本身就帶著一定的價(jià)值判斷,即便是以否定或批判的方式,也同樣為作品帶來了聲譽(yù)。
此外,通常來說,成功的首演可以為一部作品帶來聲譽(yù)。但《春之祭》似乎恰恰相反,它的聲譽(yù)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首演的失敗,得益于騷亂的丑聞。筆者以為,這一看似荒謬的現(xiàn)象正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風(fēng)潮使然。20世紀(jì)初西方藝術(shù)領(lǐng)域正處于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藝術(shù)與社會(huì)均需要革新與叛逆的精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遭遇丑聞就標(biāo)志著叛逆。斯特拉文斯基和佳吉列夫都在這場丑聞中看到了它的宣傳作用,以至于有更多的自信和氣度面對保守派的攻擊。在歌劇《夜鶯》(1914)首演時(shí),斯特拉文斯基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首演只要沒有引起騷動(dòng)就不能算作成功!”布魯姆曾經(jīng)抨擊過一些“學(xué)術(shù)激進(jìn)派”,因?yàn)樗麄冎鲝垺败Q身經(jīng)典的作品是由成功的廣告和宣傳捧出來的。”這種主張盡管夸大、極端,但在經(jīng)典作品的建構(gòu)過程中,不能說宣傳完全不起作用。在《春之祭》首演百年之際,世界各地對這部作品的重新排演和紀(jì)念同樣是一種宣傳,并將為《春之祭》帶來更廣泛持久的聲譽(yù)。
盡管經(jīng)典的意識與建構(gòu)是歷史的產(chǎn)物,但人們對經(jīng)典的認(rèn)同和喜愛卻常常是超越歷史的。莎士比亞在文學(xué)世界之所有有不可撼動(dòng)的經(jīng)典地位,是因?yàn)橐淮x者都能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人物中看到自己的幻想和傷悲。同樣,《春之祭》之所以有著持久的藝術(shù)魅力,是因?yàn)樵谖覀冃牡啄硞€(gè)神秘的角落,始終存留著先祖遺傳下來的對自然和神圣的敬畏。盡管這一亙古的記憶,在人類狂妄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漸漸被遺忘,但斯特拉文斯基用狂野的節(jié)奏和音響將之喚醒,讓我們在迷醉的狀態(tài)中向大地和春天頂禮膜拜。
注釋:
[1] 伊塔諾·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jīng)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2] J. Peter Burkholder:Museum Pieces: The Historicist Mainstream in Music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Vol. 2, No. 2 (Spring, 1983).
[3] 卡爾·達(dá)爾豪斯:《音樂史學(xué)原理》,楊燕迪譯,上海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頁。
[4]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與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5] 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 沃爾夫?qū)ざ嗄缝`:《斯特拉文斯基》,俞人豪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
[7] 羅伯特·克拉夫特:《斯特拉文斯基訪談錄》,李毓榛等譯,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8、216、217頁。
[8] 同[6],第44頁。
[9] 彼得·斯·漢森:《20世紀(jì)音樂概論》,孟憲福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10]斯塔羅賓斯基:《波佩的面紗》,轉(zhuǎn)引自喬治·布萊《批評意識》,郭宏安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11]“新維也納樂派”主要是指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三位奧地利作曲家。
[12]J. Peter Burkholder:Museum Pieces: The Historicist Mainstream in Music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Vol. 2, No. 2 (Spring, 1983), p.132.
[13]彼得·約翰·馬丁:《音樂與社會(huì)學(xué)觀察:藝術(shù)世界與文化產(chǎn)品》,柯楊譯,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頁。
[14]轉(zhuǎn)引自于潤洋:《現(xiàn)代西方音樂哲學(xué)導(dǎo)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