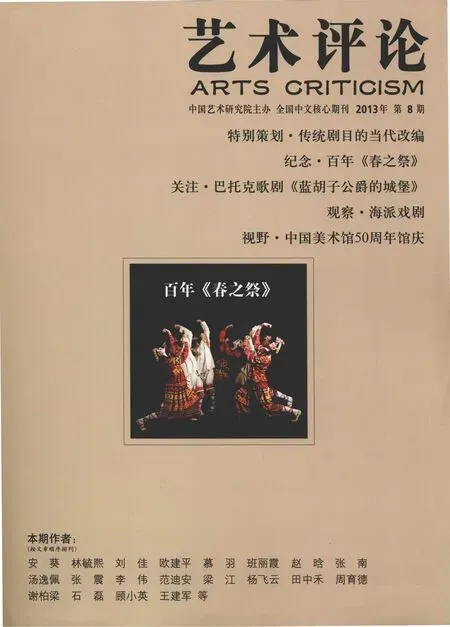經(jīng)典改編:拓寬戲曲傳承之路
劉 佳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動態(tài)性的文化,傳統(tǒng)戲曲雖產(chǎn)生年代久遠,雖長于表現(xiàn)古代題材,但她仍在大眾娛樂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仍是讓華夏子孫引以為豪的民族文化名片,對她的保護和傳承也需具有動態(tài)性思維。前輩藝術大師為我們留下眾多傳統(tǒng)經(jīng)典劇目,面對這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我們不應只滿足于袖手旁觀,任憑珍寶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被歲月塵封,而應勤于擦拭打磨,讓它們煥發(fā)出新的神采。王國維先生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那是因為一代有一代之智慧、需求和創(chuàng)造,因此實現(xiàn)傳統(tǒng)戲曲當代化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必行的。傳統(tǒng)戲曲當代化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而通過改編使經(jīng)典劇目當代化則是一條非常行之有效的途徑,盡管這條路走起來也許并不那么輕而易舉。
2012年,一出新劇目的上演使觀眾和評論家們的熱情在瞬間被激活了——京劇《香蓮案》,由天津京劇院排演,榮獲第六屆中國京劇節(jié)一等獎,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筆者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感嘆:“《香蓮案》,不只是一出戲。”這出戲的誕生以及它所引起的熱議都不應僅僅被當作個案看待,如果說它所引起的質疑牽動了后大師時代戲曲創(chuàng)作中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那么它所獲得的掌聲則令人欣喜地看到背負著繼承與發(fā)展雙重使命的戲曲藝術如何在古老與現(xiàn)代的立體時空中艱難前行并殺出一條血路。
經(jīng)典改編——傳統(tǒng)戲曲當代化的可行之路
《香蓮案》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備受矚目,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它講的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故事,而京劇舞臺上也早有一出關于這個故事的、由多位藝術大師打造的經(jīng)典之作流傳,于是質疑者責其“擅動經(jīng)典”,支持者憂其難獲認同。然而,就是這樣一出在質疑聲中起步的劇目竟然獲得了成功,特別是得到了大江南北戲迷觀眾由衷的喜愛,并有學者將其看作“戲曲經(jīng)典改編的范例”。《香蓮案》所引起的波瀾不是偶然現(xiàn)象,它首先促使我們用更加客觀、全面的眼光對“經(jīng)典改編”這一創(chuàng)作方法進行新的審視。

在已有劇目的基礎上編寫新故事的方法,歸納起來,表現(xiàn)為三種形態(tài):第一,對劇目結構、詞句進行微調,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傳統(tǒng)劇目加工整理,目的是壓縮不必要的場次,使戲劇結構更為合理,并增強詞句的文學色彩,但對全劇的思想內涵基本沒有明顯的改變。第二,通過增首益尾將折子戲擴展為故事完整的大戲,例如京劇大師馬連良創(chuàng)演的《十老安劉》、《胭脂寶褶》等馬派名劇都是在折子戲的基礎上擴展而來的。第三,在老故事的房前屋后添加新的篇章,與好萊塢喜歡為經(jīng)典影片拍攝前傳、續(xù)集的方法很相似,譬如《星球大戰(zhàn)前傳》和最近熱映的、可以被看作《綠野仙蹤》前傳的《魔境仙蹤》,以及《碟中諜》的續(xù)集等等。實際上,這種方法是依賴觀眾對老故事的普遍熟悉和認同而另起爐灶。上世紀50年代和新時期以來某些新編劇目雖然在主題立意和舞臺樣式上有新的處理,但也走的是增寫“前傳”或“后記”的途徑。第四,借用老故事的基本情節(jié)講述新的故事,只抽出舊劇中對情節(jié)事件最簡練的、具有客觀性的歸納進行新的藝術構思,并用新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思想內涵往往與舊劇各有異趣。這個故事中最小的、能夠持續(xù)在傳統(tǒng)中流傳,并具有某種不尋常的和動人力量的成分,如欲望與壓抑、罪惡與復仇、金錢與人性、自私與無私之間的斗爭,就是一個個文學的母題。不同的作者可以利用同一個母題寫出各自的故事,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于是,同樣一個復仇母題,元人紀君祥可以寫出《趙氏孤兒大報仇》;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可以寫出《中國孤兒》;京劇中則前有《搜孤救孤》,后有《趙氏孤兒》;而豫劇又可以寫出《程嬰救孤》。與之相同,“狀元負心”也是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上流傳了千百年的母題,從趙貞女與蔡二郎的悲歡離合,到秦香蓮和陳世美的恩怨情仇,這個母題在不同朝代、不同作家的手中,經(jīng)歷了漫長的嬗變過程,反映著不同時代的思想觀念。
在以上四種故事新編的方法中,第四種的難度無疑是很大的,而在戲曲界尤甚,極易背上“擅動經(jīng)典”的罪名。因為,戲曲是一種綜合藝術,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出神入化的表演。就拿京劇《秦香蓮》來說,它之所以被看作經(jīng)典,并非因其文學性和思想性堪為表率,而是因為張君秋、裘盛戎、馬連良幾位前輩藝術家的精彩演繹成為后人難以逾越的高峰。人們擔心這出經(jīng)典被擅動,并不是因為對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百分之百認同,而是擔心因情節(jié)結構的變化而失去那些美妙的唱腔與傳神的表演。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重新書寫不是強制性地以舊換新,而新劇也必然會有新的亮點,喜愛張派唱腔和馬派表演的觀眾仍然可以去看《秦香蓮》,喜愛程派、余派、麒派的觀眾則可以去看《香蓮案》,或者二者兼愛之,從而獲得更豐富的藝術享受。實際上,這種并存現(xiàn)象在古今中外戲劇史上并不罕見,王實甫的《西廂記》與“董西廂”剪不斷理還亂,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李爾王》改編自前人舊劇,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則脫胎于元雜劇……至于若干年后,哪出劇目更深入人心,而哪出劇目將退出舞臺,那是觀眾自由選擇的結果,并非由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愿望所決定。因而,我們無需擔心經(jīng)典被“動”,而應思考如何讓經(jīng)典因“動”而“新”?
心靈成長——傳統(tǒng)戲曲當代化的深層呈現(xiàn)
應該說,對某些歷史故事、戲劇人物的重新塑造體現(xiàn)了觀念的進步和人性化的關懷,而與新技術的結緣,也會讓戲曲如虎添翼,但那些匪夷所思的翻案和受累不討好的過度包裝卻令人啼笑皆非。因此,對經(jīng)典的顛覆和外部包裝都不等同于新生,而盲目的顛覆和過度包裝更如同給本來枝繁葉茂的大樹來個倒栽蔥或扣上個彩色罩子,違背其生長規(guī)律,此生尚且不保,又何言新生呢?
真正的新生應該從內而外,為大樹剪枝蔓、增養(yǎng)料,也就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消弭前人還未及打磨的瑕疵,為經(jīng)典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很多戲曲劇目包含著精彩的程式化表演,但卻因情節(jié)牽強、頭緒繁多或意識滯后而無法被今天的觀眾所接受,甚至從上演全劇變?yōu)橹挥行┰S唱段或片段見于舞臺,從而造成劇目數(shù)量的萎縮。這種片面的經(jīng)典化在戲曲劇目中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現(xiàn)象,它與戲曲藝術重視聽、重娛樂的特點有關,也與審美趣味、欣賞心理的演變有關。當那些可以用表演藝術掩蓋劇本一切瑕疵的大師們已漸漸遠去的時候,許多劇目在情節(jié)上的勉強之處、人物性格的不可信與不可愛之處就不能再被忽視了。而且,當京劇已躋身高雅藝術的行列,觀眾早已不滿足于單純的視聽享受,他們期待一出新戲能傳達出對現(xiàn)實生活新的感悟,并在認識上高于他們,從而給予他們啟迪。因此,今天的戲劇應該既是可看的,更是可讀的、可思的。
或許有人會說,京劇是古典藝術,反映現(xiàn)實非其所長,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像京劇和昆曲這樣高度程式化的古典戲劇樣式,的確最擅長表現(xiàn)古人的生活場景,如果硬要把21世紀的白領、電腦、發(fā)報機搬上舞臺,只能讓人有削足適履之感。其實,藝術反映現(xiàn)實有不同的方式,除了直接將現(xiàn)實生活呈現(xiàn)于舞臺,也可以采用借古諷今的方法,在精神上與現(xiàn)實息息相關。為了表達對戰(zhàn)爭的譴責,梅蘭芳、程硯秋分別排演了《生死恨》和《春閨夢》,這些劇目看似與現(xiàn)實無關,實則緊扣時代脈搏。這樣的例子在京劇史上不勝枚舉,說明京劇從來都與其他戲劇形式一樣,發(fā)揮著反映生活、干預生活的職能,這在今天仍然不應被遺忘。
古羅馬雄辯家西塞羅認為,戲劇是“生活的摹本、習俗的鏡子、真實的反映。”生活、習俗和真實永遠都不會是靜止的,那摹本、鏡子和反映也該隨著它們的變化而變化吧。因此,優(yōu)秀的創(chuàng)作者必須適應新的時代要求,采用新的敘事手法、呈現(xiàn)方式,并為古老故事注入全新的精神理念。以《秦香蓮》為例,它誕生于激情澎湃的“十七年時代”,充滿階級對立的尖銳和婦女翻身解放的豪邁。當人類社會已邁進21世紀,階級對立、性別對立這些外部沖突已逐漸淡化,人們更傾向于從人性的深度和哲學的層面探究悲劇形成的原因。所以,今天的戲劇僅僅展示外在沖突是不夠的,它只有將外在沖突與內在沖突結合在一起,才能在舞臺上與文學領域中獲得成功。為此,《香蓮案》將原先始終以女主人公為敘事焦點的單線敘事變?yōu)殡p線敘事,分別表現(xiàn)秦香蓮的堅守和陳世美的墮落。兩條敘事線索勾勒出兩條各不相同的人生之路,雖偶有交叉,卻最終分道揚鑣,分別表現(xiàn)出男女主人公面對貧困、金錢、壓力所作出的不同選擇,彰顯出心靈的高下美丑。這樣一來,秦香蓮的忍無可忍、陳世美的一錯再錯便更加具有說服力,而原先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也成為性格多側面、性格有發(fā)展的立體人物。
劇中,秦香蓮面臨著三次艱難抉擇:第一次,看著已完全被富貴腐蝕的丈夫,她放棄破鏡重圓的幻想,選擇用自己的雙手為兒女們“撐起遮風擋雨一片天”;第二次,面對韓琪自刎,她毅然攔轎喊冤,誓為屈死的恩人討回公道;第三次,面對包公的為難,她發(fā)自內心地唱出“香蓮能忍一家怨,不愿人間失好官”,一句既充滿無奈又飽含理解的“我不告了!”令全場觀眾為之動容。在一系列考驗面前,秦香蓮的第一選擇始終是保全親情、犧牲自己、成全他人,而每一次抉擇又是一次新的歷練與升華,愈加凸顯出她的忍辱負重、深明大義與自尊自強。
陳世美也不再單純是一個貪圖富貴的小人,而是一個在良知與欲望的煎熬中苦苦掙扎的悲劇人物。“接旨進宮”——表現(xiàn)他內心的天平在欲望與親情間徘徊,“夜訪香蓮”——表現(xiàn)他殘存的人性和漸漸顯露的無賴嘴臉;“狠下毒手”——表現(xiàn)他人性的最終泯滅。在考驗來臨時,他的選擇永遠是棄親情、求富貴,與秦香蓮形成鮮明對照。陳世美一系列錯上加錯的選擇,體現(xiàn)了欲望對人性的腐蝕,也體現(xiàn)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面臨的艱難的抉擇。“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千千萬萬讀書人的夢想,而古往今來又有多少“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能夠對突如其來的權力富貴一笑置之,繼續(xù)堅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生操守?又有多少人間悲劇就是由于這突如其來的美夢成真?因此,陳世美的形象不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意義。
文章合為時而作,《香蓮案》正是新時期以來對“狀元負心”母題的一次全新書寫,而經(jīng)典也正因為這一大膽的書寫而獲得了新生。
開拓劇目創(chuàng)作與流派傳承的雙贏之路
很多京劇經(jīng)典劇目之所以常演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所體現(xiàn)出來的流派藝術特色。流派藝術的形成與京劇鼎盛時代的主演中心制有著密切相關,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流派代表劇目與藝術特色基本都產(chǎn)生于那個時代。今天的院團體制與四大須生、四大名旦挑班的時代已有很大不同,任何一出新編劇目都不會只為某個流派的某個演員而創(chuàng)作,主演中心制已被編、導、演三位一體的新模式所取代。這是否意味著,新編劇目不需要再體現(xiàn)流派特色了呢?當然不是,我們仔細考察以后就會發(fā)現(xiàn),凡是那些在觀眾中反響強烈的新編劇目除了其思想性、文學性之外,往往還得益于流派特色的恰當運用,如上世紀50年代的《趙氏孤兒》、《赤桑鎮(zhèn)》、《義責王魁》、《將相和》,還有流派隨新劇目而創(chuàng)建的張(君秋)派的眾多代表作。而新時期的《曹操與楊修》,更因巧妙引入言派藝術而魅力大增。近年來,觀眾之所以很少將新編劇目與流派特色聯(lián)系起來,往往是因為編導在創(chuàng)作之初并未考慮到如何將流派的價值發(fā)揮到最大化,還有就是流派傳人們在演出新編劇目時沒有進行自覺的二度創(chuàng)作。難怪觀眾常有這樣的感覺,某個很優(yōu)秀的流派傳人在演老戲時特色鮮明,但排演新戲就流于一般了。
年逾八旬的程派名家李世濟先生說,周總理當年曾這樣教誨自己:“流派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流派藝術是京劇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是讓京劇區(qū)別于其他許多劇種的、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它的確應該不斷豐富,而不應停滯不前。而從培養(yǎng)京劇人才的角度來看,流派藝術的發(fā)展絕不僅僅體現(xiàn)在批量生產(chǎn)只會唱幾出老戲的傳人,因為那樣看似隊伍壯大,實則只是原地踏步,沒有實質上的進步。優(yōu)秀的青年演員成長到一定階段,必須通過實踐,學會甄別劇本優(yōu)劣、自覺選擇和安排技巧,具備主動運用流派特色塑造人物的能力,才能獲得獨立的藝術生命力。否則,很容易因單純模仿前人而成為早衰的“折下之花”,或因饑不擇食的盲目創(chuàng)新使多年打下的基礎功虧一簣。當前,流派傳承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條件好、資質高的流派新人層出不窮,而立得住的流派新劇目卻如鳳毛麟角。我們在創(chuàng)作新劇目時,只有運用流派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打造新的經(jīng)典劇目,才能將流派藝術發(fā)揚光大,才是在真正延續(xù)流派的藝術生命力。
在《香蓮案》劇本的前言上,開宗名義地寫道:“讓程派藝術多一出新戲” ,體現(xiàn)出編者對流派藝術傳承與發(fā)展的高度重視。或許是秦香蓮的堅強隱忍、忠貞不屈,令人聯(lián)想到如白菊傲霜般的程派藝術;或許是韓琪的性如烈火、知恩圖報,令人想起了如濁浪排空般的麒派藝術,編導們在劇中大膽設計了程派的秦香蓮和麒派的韓琪這兩個京劇舞臺上從未有過的形象,使喜愛程派和麒派的藝術的觀眾大呼過癮。除此之外,這出戲還匯集了生、旦、凈、丑的多個流派,觀眾和專家紛紛表示,劇中的多位優(yōu)秀青年演員正在變被動為主動、變模仿為創(chuàng)造,憑借自己的努力賦予新的人物以生命。一出新的劇目,往往因優(yōu)秀的流派傳人而神采奕奕,同時,年輕的流派傳人們也應因難得的實踐機會而獲得藝術道路上新的生長點,這才是劇目創(chuàng)作與流派傳承的互利雙贏。
探索傳統(tǒng)藝術與現(xiàn)代技術的和諧相生
不管我們是否情愿,人類社會的腳步都已邁進了21世紀,現(xiàn)代視聽技術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使人們的欣賞習慣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遙想電影藝術剛剛誕生的時代,人們看到銀幕上火車駛過,還會驚聲尖叫,而如今在3D影院里,即使看到月亮朝自己沖過來也可以穩(wěn)坐泰然了。當劇場條件和觀眾的審美心理都在與時俱進,傳統(tǒng)藝術與現(xiàn)代技術的結緣怎么還能阻擋得住呢?新時期以來,我們看到了太多不惜血本的大制作,它們的確給觀眾帶來了視覺沖擊,但這種沖擊不僅沒有贏得好感,反而把觀眾沖得暈頭轉向,從而使新技術成為新編劇目被詬病的主要癥結。而多出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的劇目恰恰都是采用了新技術的新戲,如京劇《北風緊》、豫劇《程嬰救孤》、桂劇《七步吟》、秦腔《西京故事》等,它們的成功充分說明觀眾所反對的不是技術手段本身,而是對技術手段的濫用和對戲曲藝術規(guī)律的背離。只要板鼓絲弦沒有在交響樂的進攻下無處藏身,只要寫意之美、虛擬之妙不在沉重的布景下呻吟,觀眾并不排斥新穎別致的視覺效果。
以《香蓮案》為例,這是一出堅守傳統(tǒng)的劇目,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依然是由一桌二椅構筑的大千世界和由水袖圓場抒發(fā)的無限情感,但我們也時時能感受到編導們對創(chuàng)新的孜孜以求,劇中匠心獨具之處俯拾即是。第一場,陳世美剛剛金榜得中,總管太監(jiān)又傳達了皇家招婿的喜訊,真是天降洪福、一步登天,可當他猛然瞥見妻子為自己縫制的寒衣時,眼前不禁浮現(xiàn)出往日情景。只見舞臺上燈光漸隱,秦香蓮在一束皎潔的追光中出現(xiàn),“一線線,一針針”將無限深情寄予寒衣,這樣一個具有表現(xiàn)主義蒙太奇意味的處理方法,使觀眾感受到陳世美此刻的猶疑眷戀。但是,伴隨著官員們的一聲高喊“狀元公速請更換袍服,跨馬游街”,秦香蓮身影隱去,舞臺燈光全亮,陳世美的思緒也被拽回到現(xiàn)實。官員們的聲聲催促終于迫使他痛下決心“船到急流難回轉,我只得順風逆浪高揚帆”,斬釘截鐵地吩咐道:“冠帶伺候!”說罷,將寒衣往張三陽手中一丟,投入眾人的簇擁之中。此時,燈光漸隱,舞臺上只見張三陽一人呆呆地手捧寒衣,而在他垂下眼簾注視寒衣的一刻,燈光也隨之全暗,這一場落幕。這里,燈光的明暗變化和演員的表演仿佛共同起到了區(qū)分景別的作用,我們先是看到了由眾人構成的全景別、張三陽構成的中近景別,最后又在張三陽的引領下將目光聚焦到寒衣上,完成了一個從全景到中近景,再到特寫的前進式蒙太奇。其中對寒衣的特寫作為畫龍點睛之筆,暗示丟棄寒衣正是陳世美對親情人性的背棄,也是他踏上不歸路的開端。
技術技巧,只有在以深厚人文關懷為依托的前提下,才能有所突破。京劇傳統(tǒng)戲中自由的場景切換、堪與長鏡頭媲美的導板、回龍,曾令蒙太奇學派的大師們?yōu)橹畠A倒,如今《香蓮案》融敘事蒙太奇與表現(xiàn)蒙太奇于一體的藝術創(chuàng)造,又使京劇舞臺煥發(fā)出新的魅力。
“移步”與“換形”
新時期以來,各種以鼓勵新劇目創(chuàng)作為宗旨的藝術盛會年年都在舉辦,新編劇目也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xiàn)。如果我們對這些劇目做一個粗略的跟蹤統(tǒng)計,恐怕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的尷尬——新創(chuàng)劇目不少,斬獲獎項無數(shù),但真正能流傳下來并被觀眾所喜聞樂見的卻寥寥無幾,很多劇目更是在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就偃旗息鼓,而能證明其往日風光的就只有那一個個正在生銹的獎杯。無論是劇團賴以生存的日常演出劇目,還是票房里百唱不厭的名劇名段,幾乎全部都是建國以前和解放初期誕生的那些老戲。花了錢——排了戲——獲了獎——入了庫,這仿佛已經(jīng)成為很多新創(chuàng)劇目殊途同歸的生命周期,甚至因其高頻度復現(xiàn)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被定型為新劇目創(chuàng)作的常態(tài)模式。這一生命周期的荒謬性透露出的是近年來京劇劇目建設所遭遇的瓶頸,而探究瓶頸形成的原因、尋找突破瓶頸的方法就成為關乎京劇藝術生存發(fā)展的關鍵。
也許有人會說,京劇講究的是唱念做打,只要四功五法還有人在練,老戲還有人在演,京劇就不會滅亡,何必還要費力不討好地去創(chuàng)作新戲呢?這種主張聽似忠于傳統(tǒng),實際上只不過是固步自封的借口。縱觀前輩藝術大師所走過的道路,無論是他們對唱念做打的精雕細刻,還是對流派特色的悉心打磨,無一不伴隨著新劇目的創(chuàng)作和上演,因為唱念做打和流派特色都是以劇目為載體呈現(xiàn)出來的。而且,劇種要適應新的時代需求,尋求新的發(fā)展,劇目建設永遠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
與其他戲劇樣式相比,戲曲劇目建設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戲曲是一種體現(xiàn)古典美、彰顯傳統(tǒng)道德操守的藝術,但她所面對的又是當今信息時代的觀眾,所以不得不在古典性、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也就是說,它應該既是“老”的,又是“新”的。倘若一出新戲運用了傳統(tǒng)程式,引入了現(xiàn)代思維,嫁接了尖端的聲光電技術,是否就兼顧了“老”與“新”?當然不是。因為,“老”不等同于老腔老調,“新”也不等同于新衣新景,而它們二者的平衡更不單純體現(xiàn)為表面上的平分秋色。如果說“老”意味著扎扎實實的繼承,嚴格按照戲曲特有的藝術規(guī)律進行創(chuàng)作;如果說“新”意味著切切實實的成長,即讓新劇目煥發(fā)出新時代的新風貌;那么,“老”與“新”的平衡就意味著堅守與開拓的統(tǒng)一,也就是梅蘭芳先生所說的“移步而不換形”。其中,“移步”是目的,“不換形”則是前提和保障,這個“形”絕非單指戲曲藝術的表面形態(tài),而是其內在本質和規(guī)律。如今,在戲曲新劇目創(chuàng)作中,真正應引起重視的不是因移步而不得不換形,而是雖換了形卻并未移步,即背離了戲曲所秉承的價值評判、審美標準,卻并未實現(xiàn)真正的發(fā)展。
從表面來看,成功的新劇目確實換了形——新的解讀、新的流派、新的呈現(xiàn),但它們的內核從未換形,始終堅守著戲曲最核心的藝術本質。從長遠來看,它們實實在在做到了“移步”,讓我們看到戲曲藝術在新時代的新發(fā)展,而這一嘗試的啟發(fā)性和感召力也已漸漸體現(xiàn)出來。如何在堅守的前提下開拓,如何在繼承的基礎上發(fā)展,這些優(yōu)秀新劇目或許只邁出了一小步,但這一小步卻具有不折不扣的開創(chuàng)意義,我們期待看到更多這樣生機勃勃的作品,讓古老的戲曲藝術活在當下、活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