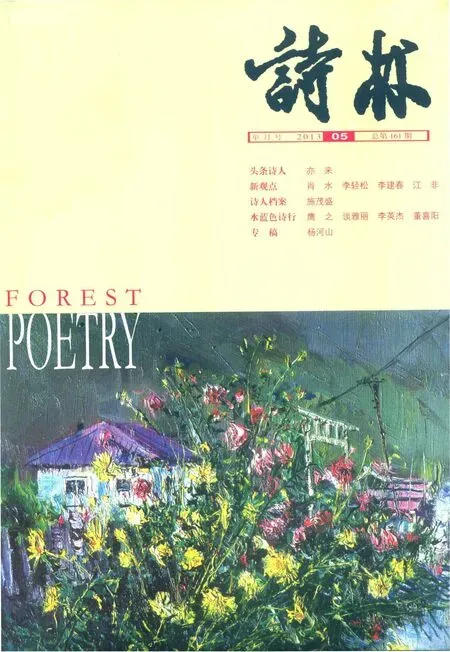反 應(組詩)
鷹 之

反 應
世界就是我的大實驗室
我等待著
陽光、綠樹、山川、河流
還有草坪上的一只沙皮犬
發生化學反應的剎那
就像一個不飲盜泉之水的渴者
等待著 一雙手
把一坨黑乎乎的山石
擰出一串清涼的水滴
洗 牌
每一條河流
都是行腳的蝜蝂
昨夜的星空
還在身體中蕩漾
今晨的藍天白云
又疊印而來……
我是說——
在嘩嘩嘩的水聲中
多少渾濁的中年
正在睡夢中洗牌?
我只詛咒自由
從一匹虎背上下來
只為盡快騎上另一匹
所謂命運 就是在兩只虎之間
來回滑動
但 當一個個黎明
被體內的一陣馬蹄聲喚醒
我從不詛咒滑動,而
只詛咒自由
淺度失眠
我還是無法進入深度睡眠
如同一條游了數千里的魚
在入海口被困住
現在,我龐大的身體
身體外龐大的羽翼
正成為這條淺淺的河流
最沉重的負擔
暗語——給je
星子鑿天熠熠閃耀
山泉裂石汩汩涌出
這些綿里藏針之物
分明在五百年前
便已參透時間的暗語
親愛的,不必夸大
區區二十年的埋沒
每次轉身,我都將
與時間撞個滿懷。
一個人厭倦了天堂的簡單
必將迷戀上人世的繁雜
沒有一把錐子
會抱怨口袋太深
親愛的,笑一笑
我就從底部露出尖來
九月酒,雁過紅
每一無用之物
都是天公地母親手做成
都有著大自在
井壁上的葉子,是四季常綠的
巖洞中的石花
是常開不謝的
雨水把落葉抽進山坳
分明是道公式1+1=3
西風狂吹一夜不停
無人知道,老槐樹的膝蓋長癰
替他刮骨療毒
乍寒還暖時節
詩歌的種子依然在暗處發芽
弄來樂天的紅泥小火爐
溫上老杜的太白醉
搞來東坡的砂鍋
燉上先發愛吃的狗肉
如果對面蒲團上再坐個
三分像佛印七分像于堅的光頭
這頓酒便喝到好處
而胸中的一枝桃子正悄悄熟透
哪個最紅,先摘哪個
后二十年
一定有人在無窮無盡尋找我——
冰面異常炸裂又須臾復原
林間唧唧喳喳又瞬間幽靜
云朵久纏不雨又倏忽四散
我一定也在尋找他們——
悄悄前躬著的脊背
暗暗厚著的腳繭
胡須上 揩不凈的霜花兒
后二十年我在哪兒?
我一直立于時光的對岸
看 歇斯底里的人群
把 一尊尊驚慌的泥菩薩 推下船
忍 冬
每一棵忍冬樹
都不知道自己叫這個名字
每年四月間,銀杯換金盞
朵朵金銀花注滿蜜汁
看著饞嘴孩童與蜜蜂爭著吮吸
茶館、藥鋪內忙忙碌碌
她們像一個盡到職責的廚娘
在沁脾的芬芳里笑得噗嗤噗嗤
每年冬月里,紅燈高高掛
滿樹紅彤彤的忍冬果 就是
黧黑的枝丫間 唯一的喜氣
但,除幾只零星太平鳥偶有啄食
這些苦澀的果子隨意掉在地上
像一只只小啞鈴,無一點聲息
菊瓣已落盡、紅楓已凋零
獨自忍受冬天的,卻是顆顆最飽滿的果實
被一個噴嚏突襲
每一個噴嚏的來頭
都是幽遠的——
當一種癢暗暗臨身
喉頭處被曖昧脹滿
一扇門
便 砰地一聲被撞開
但,電光石火間
那個一閃而逝的身影
究竟是誰
你真的沒看清
接下來的幾天
你突然發現:
冬青的劉海
油汪汪的
水杉的腰身
是婀娜的
偷嘴的麻雀
生著異性的腳丫……
一棵容易被騙的樹
一陣風 輕易就把一棵樹騙入夢中
顛簸在風的馬背上
他們 都是威風凜凜的十字軍騎士
在曠野間、棧道上東擋西殺
在山坳、村落中合縱連橫
在煙塵彌漫、金鐵交鳴聲里
仰天長嘯……
風停了。他們又在昨天的那張床上
極不情愿醒來
腰膝酸軟 大汗淋漓
像在回味著十八歲的那場軍訓
點睛者
所有的詩,都源自第一首詩。
——題記
每一首詩都是孤獨的
提著一盞小巧的燈籠
在無邊的暗夜中飛
沒錯,你曾攫住它、塑造它
但它仍舊 不是你的
你只是一個 點睛者
當它被另一時空的另一只手
再次攫住
剝去黑暗的殼,他將驚愕——
這一小朵活火山的新鮮
一小座冰山的冷靜, 和一小陣
細微而清晰的轟隆聲
真理像胡子
天外有天,地下也有地
地球并不是放在地上的一只球
它是飄著的——
當藍天的傘包又一次掙脫
它將直線掉落下去
這時,黑暗中便伸出一只手
接住它。另一只手,則
一針一線地在天地間
勾連、縫合著……
在鄉下的每一場細雨中
我總是重復加固著這個想象
像把一個虛擬的蛋糕越做越大
若此時空曠的鄉路上
恰好出現一個,沒帶雨具
卻又心無旁騖地走著的人
我便會想到“王”字中間的一橫
若他恰好又把這雨聲聽成了
噠噠噠的縫紉聲
我便說,真理像胡子
正從他下巴突突突地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