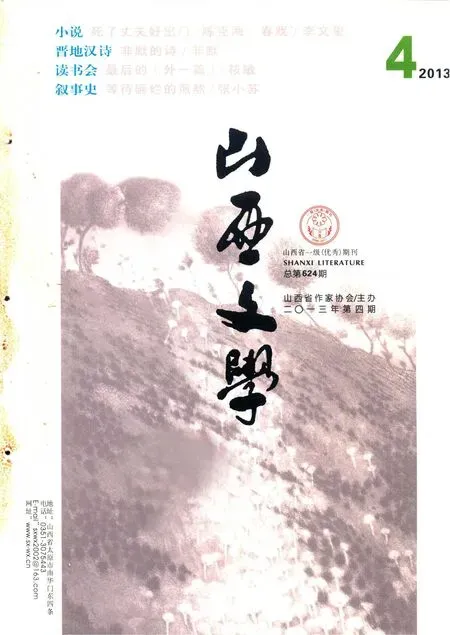大人與孩子
孫萊芙

右玉老漢(油畫)/白羽平
薛天生今年70歲,在右玉城開了一個修理水泵、電動機的鋪子,右玉北邊人爭趨之焉,專其利一世矣。
他曾是右玉中學高二班的高材生,1959年秋入學,1962年畢業。家庭成分貧農,父親薛常孩一生務農當長工,母親趙云香,滿族人,吃過香的喝過辣的,此時也不過是尋常社員,家庭婦女。
1958年大躍進,報紙上放衛星,說一畝地打12000斤糧食。初十班班主任給全班讀報,然后讓大家討論。薛天生說:“凈瞎說,不可能!”班主任批評他表現不好,思想消極。
1959年,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薛天生家是農戶,每人每天僅有二兩半粗糧,頓頓喝稀的,同學們連體育課都不能上,老師們講課提不起精神。人們吃榆樹皮、灰菜,薛天生的同學蔡金祥的父親在一天夜里餓死了。
高一班的張貴中,家庭市民,也餓得夠嗆。有一天張貴中、薛天生,還有高三班的張永江,高一班的張玉,四個臭味相投的人湊到一塊,說起餓肚,四個人的嘴沒個把門的,瞎嚼開了。
不知是誰說了句,咱們成立狗個“均產黨”哇,把土地平均分給大家,不就吃飽了。張貴中說:“對,我們就鬧它個黨綱、黨章,我當書記,天生當部長。”但是黨綱、黨章怎么鬧,由誰來鬧,還沒眼眼。他們四人雖然是高中生,但張貴中是個賴學生,其他人偏重數理化,語文均稀松平常,黨綱、黨章是個啥,見也沒見過,根本就弄不來。何況也僅僅是過過嘴癮,說說也就算了。
第二天,薛天生在街上遇見他初中的好友傅恒山,傅沒上高中,在街上晃悠。薛天生對他說:“我們成立了個組織,你參加不?”傅恒山還沒鬧清是做啥,就連連說:“行,行,耍時候一定叫上我!”
薛天生高中畢業后,在下柳溝教了一個月小學,接著又到上堡小學當了一年教師。他把這事早忘光了,豈不知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經降臨到他們和很多人頭上。
1963年9月23日,放了暑假,薛天生正在家睡覺,沖門進來兩個人,是公安局的譚某和李某,給他戴上手銬,說聲“走”,就把他押進公安局。
當天夜里,預審股股長譚某就對他和張貴中分別進行了審訊,一直審到半夜,有三四個鐘頭。半個月后,正式下了逮捕證。
審問的重點集中在黨綱、黨章上,他們承認說過。緊接著讓寫出來,他們說沒有。但此時說沒是不行的,為了弄出黨綱、黨章,公安局下了很大力氣。你說沒有,一聲斷喝“老實交待”,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不行,不讓吃飯、睡覺。
他們只能拿出黨綱和黨章,薛天生平時作文就臭,這時不得不硬著頭皮編“無影傳”。寫好后,交上去,說不行,怎么啦?兩人寫的不一樣。咋辦?把他們弄到一起協商。張貴中對薛天生說:“我說你寫!”捏務了半天,終于寫出來了,連黨綱帶黨章總共不足半張紙。
案件在半年后到了檢察院,這中間他們在看守所一共蹲了13個月。1964年8月案件正式判決,罪名是“反革命集團”,因為發現早,未造成大的危害性,判處張貴中有期徒刑五年,薛天生有期徒刑四年。
此案如果說到此就結束了,也沒什么。關鍵是它還牽連了好多親戚、朋友與同學。比如薛天生的哥哥薛恩淵,山西大學英語系畢業,兄弟倆平日難免有個書信來往,至于查出了什么,我不清楚。反正是他因此也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十年,妻子離婚,留下一個男孩叫毛毛。因為這樣的家庭,毛毛從小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改革開放后因攔路搶劫,又被判了重刑。
那些與他們一起讀書的同學,來往過的朋友,甚至說過話,在一起玩耍的人,都受到了審查和處理,凡能牽扯者,升學、就業、當兵都不許。
判刑后,張貴中和薛天生被送到懷仁下寨勞改農場改造,學習修配。三年里,薛天生學會了修理鏈軌車、柴油機、水泵、電動機。
1966年薛天生刑滿釋放,出獄后在懷仁住了一晚,第二天步行回家。在監獄,他因為看《古文觀止》,里面有篇文章叫《臥薪嘗膽》,監獄管理人員說他想變天,要給他加刑。他據理力爭,刑雖然未加,但為此又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
他回來后,給大隊開柴油機,澆地、脫粒。分糧,別人一年是360斤,他是200斤。每天“六出勤”,社員是“三出勤”,他是早飯前出一回,午飯晚飯后再出兩回。
那年,有人在黑流堡挖出一個日本人留下的摩托大架,薛天生給它安上柴油機、轱轆,設置了轉向、速度等裝置,做出一臺碾場機,帶上兩顆碌碡,跑得快,碾得凈。公安局來人,給他摘掉了帽子。
好景不長,第二年春耕抓糞,下了場雨,糞堆黏得不行,他揮鍬把糞堆上面的一層豁開,公社書記說這是搞破壞,當天夜里,五個大隊輪流批斗,給他總結了十條罪狀,又給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十條罪狀主要第一條是“破壞農業學大寨”;還有“毆打隊長,兇惡至極”;“散布反對言論”等等。
有回深挖地,他累了,坐下來歇息。隊長劉生大跑到他跟前喊:“反革命不能坐!”他不聽,劉生大舉鍬就劈,他一頭把劉生大撞了個“蛋迎天”,劉生大剛爬起來,他又一頭撞過去。
劉生大被撞后,氣不過,指著薛天生說:“我要把你徹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薛天生說:“不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社會不可能永遠這樣,想斗誰就斗誰,我也不可能一輩子不如你。”這話被定為“污蔑社會主義長不了”,罪行嚴重得很。
公社安排第二天召開萬人批斗大會,小隊長朱寬和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對他說:“你請假吧,說馬上就回來,然后跑球了算了。”他趕緊去找劉生大請假,說:“十七溝我三大病得快死呀,我得去見他最后一面。”劉生大還不知道開會,就說:“去吧,快去快回。”
薛天生帶上修理工具,到右玉東山溝的中窯子、楊于后窯、大王廟、程家窯,給這幾個大隊修柴油機。
第二天批斗大會開始了,許多人被五花大綁,脖子上用細米絲掛著牌子,等候民兵把他們架上舞臺。主持會議的人大喊一聲:“把反革命分子薛天生拉上來!”支書和民兵們找了半天,結果發現他根本就不在。法院院長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們繼續開會!”
“文革”開始后,李達窯中學又“發現”了“繼均黨”,成員都是教師。“繼均黨”就是繼承“均產黨”之意。
教師中有幾個是薛天生初中的同學,公安局來人找他,問:“你和李達窯的同學們誰慣熟?”薛天生說:“孫明!”
孫明是個瘋子,神經得啥也不知道。公安局的人就說:“哈哈,你看這家伙狡猾不狡猾!”
“繼均黨”事件使李達窯中學的許多教師陷入滅頂之災,教師楊占林被無休止的批斗弄成神經病,把兩支筷子插進鼻孔朝墻上撞。
“均產黨”主犯張貴中刑滿釋放后下放雞家溝,批斗時被打斷腿,半個身子不能動,后患精神病,生火時點著了身上的衣服,燒死了。
“均產黨”的出臺是右玉縣“文革”當中耳熟能詳的大事件,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非常年代大人對孩子的一場算計。學生們的行為對不對,不對;有問題沒有,有。但論其實質,不過是年幼無知,不懂輕重而已。
凄風苦雨中,終于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1979年,薛天生已經38歲了,他所從事的修理行業也進入了真正的春天。幾年來,他奔走口里口外,憑手藝掙下不少錢。也就是這年,城里25歲的姑娘楊林林嫁給了他,添人添丁,日子從此越過越紅旺。
青春多么美好,生命多么短暫!
薛天生還是那樣,好開玩笑,“好瞎球說”,雖然70歲了,但望之似50如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