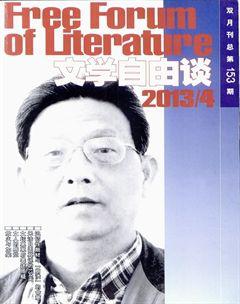《美學操練》與葉廷芳先生
仵從巨
如果就時今中國學者、研究者撰寫的著作與論文數量言,怕是可以如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樣讓我們生出些自豪感的。但是只要身在其中即清楚,這實在是一種無根底的虛妄。評價體系的惡劣指向與功利主義的激勵性驅使,所謂的學術成果有太多的泡沫,太多的垃圾,更令人悲觀的是似乎迄今仍看不到有回頭的跡象。正因此,著書為文、開會研討、發言辯論,“問題”或“真問題”或“問題意識”便成了一個學者或研究者的價值選擇與學術道德的體現。所以發此感慨,是因為在認真、全面、仔細拜讀了著名學者葉廷芳先生2012年8月新出文集《美學操練》之后,對其中明晰而自覺的“問題”意識有了甚是真切的感受。
《美學操練》收錄文章共二十六篇,時間跨度長達二十五年(1985——2010),作為近三十年中國當代學術環境、學術生活發展變遷的有限經歷與體驗者,閱讀中我似乎又重回被知識界、思想界視為黃金般的“八十年代”。作為50后、60后的一代學人正是在那一時期開始接受基本的學術訓練,開始嘗試性、起步性的學術研究,而葉廷芳先生的文章與著作是那時幼稚樸素的我們的讀本之一。
在《美學操練》中,我們深刻感受到的是,論者自覺的人文情懷以及與之相通的平民意識、民主思想。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問題的研究,對于研究者以至任何從業者,他(她)必須有對“人”的自覺關注。人是出發點,亦是歸宿點。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無此,學問是干癟的、僵硬的;論者是機械的、冰冷的;其結論則是可疑的。因為人文情懷,才會去關注活生生的問題、關注活生生的人,文也才可能有溫度、有靈魂、有介入、有力量。讀葉廷芳先生的文章,聆聽他關于文學藝術問題或文化問題的言說,檢閱他因為“自己的興趣”而選取的“題目”就能清楚見到:他討論“后現代”文化現象,提煉出其中的“平民美學”并予以積極的認同與贊賞:“藝術,終于從高雅的殿堂走下來了,走到了民間,走到了廣場。”他呼吁,對“平民美學”的認識是“理論工作者的一項任務”;他以歌德與席勒兩位巨人為對象討論“大寫的現代人”問題,指出兩位智者的偉大正在于他們“放眼世界、擁抱人類,并把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當作最高的價值追求”;他關注高行健的先鋒、實驗戲劇,早在1988年就對這位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度評價,肯定他戲劇觀中“戲劇不是舞臺,戲劇不是布景,戲劇不是道具,戲劇不是服裝,最后只剩下了人,唯獨戲劇不可以不見人。只有有了人,有了人的動作,才有戲劇的可能”;他在討論中國當代戲劇的強身之道時明確提出“戲劇的人文觀念必須更新”,應有“更深厚的人文品格”與“大愛意識”;他在討論中國傳統建筑時,準確指出了“中國的木構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親近人性”這一特征,并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建筑精神》發現并肯定“人不能離開自然”、建筑應“以人為中心”這一觀念高度認同;至于進入“專業”領域討論卡夫卡、迪倫馬特等德語文學大師時,葉廷芳先生“人”、“人文”的焦點就持續性地存在甚至可說是以之為圭臬。簡言之,人,人文情懷,平民意識,民主思想與文學藝術以至理論問題,在葉廷芳先生處,是與他的文與人融為一體的。
借《美學操練》回顧葉廷芳先生迄今四十余年的學術道路與學者生涯,他實在是個不曾停息的耕耘者。作為物證,僅僅我的書架上榮幸羅列的“葉著(譯、編)”便有二十余冊(他全部的編、譯、著已四十余部)。其中的《卡夫卡全集》(主編,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迄今仍是權威性的中文版本;《現代藝術的探險者》(專著,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不僅是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或中國“新時期”卡夫卡研究開創性、奠基性的代表作,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甚有啟發;《論卡夫卡》(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9月),作為當年影響甚大亦意義深遠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之一種,迄今仍是卡夫卡研究的重要文獻,它體現出的“選家”眼光佐證的是關于卡夫卡研究的“世界性”視野;而《美的流動》(2000年)、《遍尋繆斯》(2004年)、《揚子——萊茵:搭一座文化橋》(2008年)、《不圓的珍珠》(2008年)、《卡夫卡及其他》(2009年)以及我們正在討論的《美學操練》,這些由商務、人民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北京大學等出版社出版的“隨筆性”文集則是作者關于德國文學(文化)、歐洲文學(文化)、中外戲劇電影繪畫音樂、東西方建筑以及與之相涉的諸多“美學問題”思考的辛勞成果。
我個人自然無能力就葉廷芳先生的學術造詣作出準確、到位、全面的評價,但從1992年有緣“識荊”武陵源至今已二十余年,其間因學術會議等活動又與葉先生過從甚多,亦榮幸忝列為友,對葉先生說“了解”甚至“理解”大概還是可以的。我知道,葉先生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幼少時因傷病亦因庸醫致左臂截肢。就是以這樣的身體狀況,1961年畢業并留任北大、1964年入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至今近五十年。在他學習、成長、發展、成家、成名家、成大家的過程中,先后有名師大師如馮至、朱光潛、趙蘿蕤、聞家駟、楊周翰、吳達元、田德望、楊業治等的教誨培養獎掖提攜,葉先生迄今仍對前輩學者感念不已,尤其是于馮至先生。是馮至先生當年校改他(們)的譯稿,是馮至先生1964年調任新成立的外文所時從北大西語系點名帶了葉廷芳,是馮至先生對葉廷芳執筆并發表于1979年《世界文學》第一期的《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同時配發李文俊先生譯《變形記》)大加贊揚,還是馮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一道,設法排除阻力,有”管事者”以為,以葉廷芳之身體條件不宜出國,錢鍾書先生聞之抱不平:“這真是豈有此理!解放前潘光旦一條腿走遍世界,你一只手還不如他一條腿?”,促成了葉廷芳1981年第一次出訪,也正是此次出訪瑞士有了與次年即去世的迪倫馬特長達四個半小時的聚談和此后關于迪倫馬特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從馮至先生及其他的前輩學者那里,葉廷芳先生受到的更深刻的影響不僅是知識、理論、治學,更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立場與價值觀。例如,馮至先生在席卷全國的“大躍進”狂潮中力阻了北大西語系學生想“抓大傢伙”、要批“歌德”的狂想,馮至先生關注并支持周揚動議、王元化王若水等學者積極參與的“異化”問題研究并因此被整肅,令他印象深刻。所以,當從干校歸來的葉廷芳與何其芳在北京市外文書店的倉庫(在通縣)偶然發現了涉及“異化”主題的卡夫卡之后便萌生興趣,也就此開始了他成為中國卡夫卡研究權威的學術“探險”旅程。此“險”是學術之艱“險”,亦是政治之危“險”:在1983年的“清污”運動中,他被要求“自我清毒”寫自我批判稿。“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是多么可恥啊!”持此一念的葉廷芳以“拖”為計,終于在這場為時二十九天的短命“運動”中未有違心文字。因為廣泛的學術影響,1998年葉廷芳被有關部門“安排”為全國第九屆政協委員并在五年后又連任一屆。在其位謀其政,葉廷芳先生的政協委員也當得有聲有色:他利用自己的美學理論知識與學術影響,征集了同為社會名流的四十九名政協委員的簽字,歷經曲折,成功地阻止了“圓明園”的“復建”與“仿建”計劃;在關于“國家大劇院”的設計方案的招標、討論過程中,他在《建筑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日報》連連發文、“筆戰群儒”與相關領導,影響了方案的最終選擇結果,他的主張甚至成為媒體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證明中標方案選擇科學性的“證詞”:外國文學專家葉廷芳先生認為,國家大劇院設計的可取之處是使用了“反差效果”。葉先生還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就“計劃生育”提出議案,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并引起更為廣泛的關注、支持與爭議。他以為獨生子女的政策影響中華民族的前途。他的思路不在經濟學、社會學而在人文思考。他認為,人類面對兩個自然,即外在的大自然,內在的人類自身的自然。獨生子女政策使人的“內在自然”被破壞掉了:獨生子女無“兄弟姐妹”天情天性的原生環境;獨生子女(將)無姑表堂表姨表等血親關系破壞了“倫理關系”的自然生態;獨生子女易導致父輩之溺愛與子輩孫輩之嬌氣驕縱。并且,人口多未必全是壞事,“人口紅利”一說便是證明。而且,從世界范圍看,人口的增長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成反比的關系,即:經濟文化的發展引致的觀念變化會使人口生育率降低而非提高;同時,要相信“大自然自行調節”的規律。人口可控制,但強度應適當,不可超越國際認可的二胎底線等等。盡管“計劃生育”這一問題的確復雜,臧否難以簡單判定,但葉廷芳先生的思考與言說無疑會對“推動”這一“國策”的適時調整的歷史合力產生不可低估的意義。
2008年,葉廷芳獲瑞士蘇黎世大學“名譽博士”,理由除他較早地把卡夫卡、迪倫馬特兩位歐洲的現代主義作家介紹到中國,促進了日耳曼語言文學在中國的認知度,亦因為他在國內有爭議的熱點文化問題上積極參與,表現了“勇敢精神、先鋒精神和正直品格”。葉廷芳先生在接受訪談論及學術、學者時表示:“一個學者應該意志堅強、視野開闊、胸懷博大。一個學者不應有黨派觀念、狹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這些東西,而應以人類利益為最高坐標,站在時代制高點說話,唯真理是求”,“堅持精神操守,勇于社會擔當,為社會的公平、公正、自由、民主、憲政而大呼猛進”——這應是上述“精神”所指與上述“品格”所是的立場證明。
基于對葉廷芳先生為文為人的了解和理解,我以為:葉廷芳先生是中國進入“新時期”之后在學術研究領域內最早的“破冰者”與“先行者”之一;是德語文學與德國文學研究與推廣的領銜學者;是我國無可爭議的卡夫卡研究權威;是對中國當代藝術尤其戲劇藝術關注最多并最富見識的外國文學專家;是我國當代杰出的文化學者之一;是“新時期”身在前線突破思想牢籠不斷前行的“探索者”;是以學術精神(“有道”)入世的勇敢踐行者(“有為”)——他對我國當代文化的“現代性”轉型作出了并仍在作出重要的貢獻。
凡與葉先生有所交往的人,對他為人的真誠友善、率性天真都印象深刻。他不僅治學嚴謹、成果累累、成就令人敬仰,而且熱心提攜后進,有許多年輕學者都得到過他的幫助與指導。這就讓我們更加欽敬這位可以為師亦可為友的前輩學者。葉先生今已七十又七,愿他健康快樂、思想不衰,愿總能聽到他讓人難忘、高吭嘹亮的男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