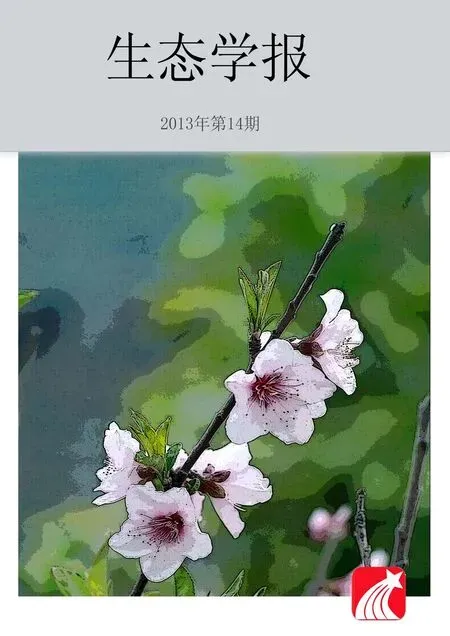西江下游浮游植物群落周年變化模式
王 超,賴子尼,李新輝,* ,高 原,李躍飛,余煜棉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廣州 510380;2.農業部珠江中下游漁業資源環境科學觀測實驗站,廣州 526100;3.廣東工業大學,廣州 510006)
浮游植物利用光能驅動光合作用產生有機物,是水域生態環境中生命有機體的初級生產者,形成水生動物食物鏈的基礎環節[1-3]。其通過吸收水體中的營養鹽成分促進自身的生長繁殖,同時也滿足了浮游動物的攝食需求,進而開啟了能量在水生動物食物鏈中的傳遞,并最終將影響漁業資源的輸出甚至整個水域生態系統的穩定。此外,浮游植物群落的組成和變化與水環境密切相關,是水環境細微變化的敏感指示生物[4]。
西江源出云南沾益馬雄山,河長2074.8km,是珠江最大的支流。該流域地處亞熱帶,水生態環境良好,漁業資源較為豐富,是沿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肇慶江段位于西江的下游,是珠江干流匯入珠三角河網水域的咽喉通道,受上游河水沖刷所帶來的泥沙、礦物質和有機物的影響,該江段的水體較為渾濁,營養物質含量豐富,加之水流較緩,滯留時間較長,為水生動物和浮游植物提供了較好的生存環境。為了解西江水生態系統的現狀及未來演化趨勢,本研究小組自2005年起在西江肇慶江段設置長期監測點(距離河口約160多km),內容涉及魚類群落、漂流性仔魚、浮游生物、水化因子和重金屬污染等。其中,浮游植物的連續監測工作始于2008年,具體監測時間為每天8:00;2010年起改為晝夜分布的連續監測,分早、中、晚3個時段進行。
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目前有關西江浮游植物的研究報道并不多。除了20世紀80年代初由珠江水產研究所牽頭對珠江水系的漁業資源進行調查時涉及到了西江浮游植物的常見科屬,近年來僅見王超等[5-6]對西江兩個廣東魴(Megalobrama terminalis)產卵場的浮游植物組成及顆粒直鏈藻的種群生態特征進行了研究報道。國際上的相關研究發現,江河浮游植物群落結構的普遍模式為綠藻在種類豐富度上占據優勢地位,而少數硅藻物種在生物量上占據優勢[7-9]。作者的研究報道已表明中心綱硅藻顆粒直鏈藻(Aulacoseira granulata)是調查江段的全年優勢種[6],但是有關浮游植物群落組成及變化的內容仍未進行闡述。此外,國際上的相關假說認為在營養鹽較為豐富的低地河流中,浮游植物群落組成及變化主要受物理因素的影響,與營養鹽含量關聯不大[10]。本文基于西江肇慶江段長期監測點2009年浮游植物群落及環境因子的數據資料,闡析浮游植物群落的周年變化特征及其與環境因子的關系,并與國際上在類似區域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比,分析它們的共性及差異,為西江水域生態環境評價和保護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調查站位和時間
調查站位是本研究小組的長期監測點,位于肇慶市區肇慶漁政碼頭上游約50 m處(23°2'40″N,112°27'5″E)(圖1),本次調查時間為2009年1月1日至12月30日,調查頻率為每5d 1次,具體時間為每天8:00。春節期間(2月15日、20日)未進行野外樣本的采集工作。

圖1 調查站位布設圖Fig.1 Map of sampling sites
1.2 樣本采集、處理及數據收集
浮游植物樣本取表層(離水面0.5 m)水樣1 L裝入聚乙烯瓶中,立即用魯格氏液固定,使其最終濃度為15‰。水樣運回實驗室后,立即移入標記刻度1000 mL玻璃量筒內,加蓋靜置24 h后,用管口包裹篩絹的虹吸管或吸管小心吸去上清液。如此反復多次,直至將水樣濃縮至30—100 mL。分析時取均勻樣品1 mL注入Sedgewick—Rafte浮游植物計數框中,在Nikon TS100倒置顯微鏡下進行浮游植物的種類鑒定和計數。另取500 mL水樣,現場過濾后置入帶冰塊的冷藏箱中運回實驗室,用水質流動注射分析儀進行營養鹽分析。
水溫數據采用自動水溫記錄儀獲得,每小時記錄1次。徑流量和水位的數據是從以下網址:http://xxfb.hydroinfo.gov.cn獲得,降雨量的數據是從以下網址:http://www.weatheronline.co.uk/weather的趨勢圖上讀取近似的數據。
1.3 數據整理和相關分析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計算方法參照Hillebrand等[11],通過體積法計算取幾何近似值,分析過程中將生物量在總種群中所占百分比大于5%的物種定為優勢種。
為了更好地闡析浮游植物群落組成及變化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對浮游植物總種類豐富度、真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和偶然性浮游植物進行了比較分析,物種的劃分依據參照Van den Hoek等[12]的結果。
本文后述的種群演替的時間變化圖用Origin 6.1軟件完成,而種群變化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用Canoco 4.5軟件進行分析,并得到PCA二維降序圖。
2 結果
2.1 水文環境
文章中所調查的西江肇慶段水文環境數據隨時間變化情況引自作者報道的資料[6]。
在研究水域中,9月份之前水溫呈緩慢上升,4月10日前水溫基本低于20℃,全年最低水溫出現在1月15日,僅8月20日至9月15日期間水溫高于30℃,9月10日達到最大值,之后下降,11月10日后水溫開始在20℃左右徘徊,一般低于20℃。相鄰兩次調查的水溫最大差值出現在11月10日和15日之間,差值為14.35℃。
西江肇慶段全年徑流量僅在5月至8月期間出現4個明顯的洪峰,與之相比,其它季節變化不大。但是仍可發現4月份之前的徑流量基本維持在3000 m3/s以下水平,4月份開始緩慢上升;8月1日第4個峰值過后,徑流量開始下降,10月1日后,徑流量基本維持在2000 m3/s以下水平。
調查期間,除1月和2月外,其它月份均有降雨。6月和7月的降雨頻率最高,其中7月份的降雨頻率達85.71%。單月僅出現1次降雨的包括8、10、11、12月。單日降雨量最大值出現在9月15日,為50.5 mm。
2.2 物種組成及優勢種分布
調查期間共發現浮游植物種類7門,245種(包括變種、變型)。其中硅藻32屬104種,占總種數的42.44%;綠藻37屬85種,占總種數的34.69%;裸藻6屬31種,占總種數的12.65%;藍藻8屬18種,占總種數的7.34%;其它包括甲藻4種,金藻2種和黃藻1種。
調查期間主要物種(包括優勢種和常見物種)的組成和分布如表1所示,包括硅藻7種,綠藻6種,裸藻2種。其中,出現率高且對總生物量貢獻大的物種有顆粒直鏈藻原變種(Aulacoseira granulata var.granulata)、變異直鏈藻(Melosira varians)和尖新月藻變異變種(Closterium acutum var.variabile),僅顆粒直鏈藻原變種為真浮游植物種類。出現率高且對總生物量貢獻小的物種有梅尼小環藻(Cyclotella meneghiniana)、扭曲小環藻(Cyclotella comta)、短小楔形藻(Licmophora abbreviata)、舟形藻(Navicula sp.)、鐮形纖維藻奇異變種(Ankistrodesmus falcatus var.mirabilis)和被甲柵藻(Scenedesmus armatus),大多數種類為真浮游植物。其它物種出現率低且對總生物量的貢獻小,僅在某些月份成為優勢種,多為真浮游植物種類。
2.3 種類豐富度的時間變化
由圖2可知,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的時間變化模式整體呈現高溫季節高,低溫季節低的特點。種類豐富度的變化范圍為2—58種,最大值出現在7月20日,最小值出現在3月5日。4月份之前,種類數總和維持在20種以下,之后呈現上升趨勢,持續至8月底。8月份之前出現了幾個明顯的高值,分別為4月25日的49種,5月25日的55種和7月20日的58種;8月份的種類數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該月最大值為8月30日的50種。自9月份開始,種類數的變化比較平穩,基本維持在15—25種的水平。浮游植物主要類群(硅藻和綠藻)種類豐富度的時間變化模式與總種群的變化模式基本一致(圖2)。從百分組成上看,硅藻和綠藻在總種群中所占百分比之和一般不低于80%(圖2);從兩者的相對組成上看,1月,硅藻和綠藻相等;2—4月,綠藻優于硅藻;5—12月,硅藻優于綠藻,其中10—12月,硅藻的優勢度極為明顯(圖2)。
真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的時間變化模式與總種類數的變化模式是一致的(圖2),種類豐富度的變化范圍為1—29種,最大值出現在7月20日,最小值出現在3月5日。真浮游植物的主要類群為硅藻、綠藻和裸藻,其中硅藻種類數的周年變化模式比較平穩,變化幅度(0—8種)也不大,這與硅藻總種類數的單峰型的變化模式是不一致的,與其變化幅度(0—29種)也存在很大差異(圖2);綠藻為真浮游植物的最主要類群,其周年變化模式與綠藻總種類數的變化模式一致,其變化幅度(0—18種)與總種類數的變化幅度(0—21種)差異也不大;裸藻物種基本均為真浮游種類,主要出現在高溫季節。從百分組成上看,綠藻為真浮游種類的最主要類群,一般不低于50%;硅藻次之,但是高溫季節百分比明顯低于低溫季節,3月至9月期間維持在20%左右;裸藻百分比額變化范圍為0—31%,最大值出現在6月,4月至8月的其它月份維持在20%左右(圖2)。

表1 主要物種(優勢種和常見物種)的組成和分布Table1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ain species(dominant and common species)
2.4 種群生物量的時間變動
由圖3可知,調查期間浮游植物的總生物量變化呈現明顯的雙峰型,兩個峰值分別出現在8月30日(5.29 mg/L)和11月1日(10.91 mg/L)。生物量的變化范圍為0.003—10.91 mg/L,均值為0.39 mg/L,最小值出現在3月15日。硅藻是浮游植物總生物量的最主要組成類群,調查期間其在總種群中所占百分比均大于50%,尤其在8月至12月期間,其百分組成基本不低于90%(圖3)。除硅藻外,1月至3月期間的主要類群為綠藻,4月至7月期間的主要類群為綠藻和裸藻。
真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周年變化模式與總浮游植物非常一致,兩個峰值也分別出現在8月30日(5.26 mg/L)和11月1日(10.88 mg/L)。生物量的變化范圍為0.0001—10.88 mg/L,均值為0.35 mg/L,最小值出現在3月1日。從百分組成上看,除1月至3月期間硅藻的優勢程度更加明顯之外,還發現,4月至7月期間裸藻生物量貢獻大于綠藻,這與圖中綠藻貢獻大于裸藻的結果相反。其它月份各類群的相對組成均為硅藻占據絕對優勢(圖3)。
2.5 相關分析
2.5.1 種類豐富度與環境因子的關系
用Canoco軟件首先對5個浮游植物類群(硅藻、綠藻、裸藻、藍藻和其它)的總種類豐富度數據進行去趨勢對應分析(DCA),在所得的各特征值部分發現4個排序軸中梯度最大值小于3,以此為依據選擇線性模型中的間接梯度分析PCA模型對5個浮游植物類群的種類豐富度與9種環境因子(水溫、徑流量、降雨量、硅酸鹽、磷酸鹽、硝態氮、亞硝態氮、氨氮和總氮)進行相關分析,圖4為所得到的種類豐富度與環境因子的PCA二維降序圖。

圖2 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的時間變化及相對組成Fig.2 Tempor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richness and relative contribution
對于浮游植物各類群種類豐富度而言,第一、第二排序軸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表明這兩個排序軸所包含的信息是相互獨立的(表2);對于環境因子來說,前2個排序軸的累計貢獻率分別為57.8%和90.3%,這說明前2個排序軸約含有9種環境因子的90%的信息,所以可以用PCA二維降維圖研究9種環境因子間的相互關系(表3)。各類群種類豐富度第一個排序軸與環境因子第一個排序軸的相關系數較高,為0.78,各類群種類豐富度第二個排序軸與環境因子第二個排序軸的相關系數為0.73(表2),這表明PCA二維降序圖可以較好地解釋種類豐富度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圖4)。
從PCA二維降序圖可看出,浮游植物各類群種類豐富度與水溫和徑流量的排序方向一致,均呈正相關,因而當水溫高、徑流量大時,有利于所有藻類豐富度的增加;而硅酸鹽主要影響硅藻、對藍藻和其它藻類也稍有影響(均呈正相關),但與綠藻及裸藻的相關性不高(其夾角余弦值較小),故影響并不明顯,因而當硅酸鹽含量高時,主要是對硅藻豐富度的增加有好處。
用Canoco軟件對5個浮游植物類群的生物量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的過程與種類豐富度的相同,最終得到各類群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的PCA二維降序圖(圖5)。
對于各類群生物量而言,第一、第二排序軸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表明這兩個排序軸所包含的信息是相互獨立的;對于環境因子來說,前2個排序軸分別含有9種環境因子的99.3%和0.7%的信息,這表明基本上可以用二維降維圖的橫坐標值研究9種環境因子間的相互關系(圖5,表3)。浮游植物各類群生物量第一個排序軸與環境因子第一個排序軸的相關系數為0.45;各類群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第二個排序軸的相關系數為0.42(表2),這表明PCA二維降序圖基本可以用來解釋生物量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

圖3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時間變化及各類群相對豐度Fig.3 Tempor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population density 、biomass and relative contribution

表2 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和生物量、環境因子前2個PCA排序軸與環境因子間的相關系數Table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phytoplankton species richness,biomass,environment factors axis1 and axis2,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CA二維降序圖表明,浮游植物各類群生物量主要與水溫、徑流量和硅酸鹽有關。水溫升高時,主要有利于硅藻、綠藻、藍藻和其它藻類的生長,對裸藻的生長也稍有些好處;徑流量大時,主要有利于裸藻的生長,對藍藻、綠藻和其它藻類生物量的增長也稍有好處,但不利于硅藻的生長(因徑流量與硅藻的夾角為鈍角,兩者呈負相關);而硅酸鹽對藻類生長的影響主要是硅藻,當其濃度升高時,硅藻生物量的增長會加大,但對裸藻的生長沒好處,與藍藻、綠藻和其它藻類的線性相關程度并不高,影響不明顯。

圖4 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與環境因子的PCA二維降序圖Fig.4 Ordination diagram of the first two axes of princ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richnes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圖5 浮游植物生物量與環境因子的PCA二維降序圖Fig.5 Ordination diagram of the first two axes of princ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表3 PCA分析中環境因子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的下半區Table3 The next part of coefficient matrix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PCA analysis
3 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西江下游浮游植物種類和類群組成豐富,這與Bahnwart等[13]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其認為具有一定的水深且流速緩慢的下游江段有利于不同浮游植物類群的存在和生長。硅藻和綠藻是西江肇慶江段浮游植物群落的最主要類群,此外,裸藻在種類及生物量組成上均有一定的貢獻,藍藻雖然在種類組成上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生物量極低,這種群落組成模式與國內外其它江河[14-18]的研究結果也是一致的。
如表1所示,調查江段的主要物種僅有15種(包括硅藻7種,綠藻6種和裸藻2種),其中出現率高且對生物量貢獻大的物種僅3種(包括2種硅藻和1種綠藻)。有研究表明,存在少數優勢種并伴隨大量零星的其它物種是世界上大的江河生態系統中浮游植物群落結構的主要特征[19-20]。作者的前期工作已表明,顆粒直鏈藻是調查江段的全年優勢種[6],其它優勢種的出現不具有連續性,對生物量的貢獻也明顯偏低(表1)。此外,在所鑒定的245種藻類物種中,出現率大于10%的物種僅69種,絕大多數為零星出現。以上結果均表明,調查江段的浮游植物群落結構特征與國內外其它江河的結論相吻合。
浮游植物總種類豐富度的周年變化呈現明顯的季節特征(圖2),PCA分析結果表明,當水溫高、徑流量大時,有助于提高所有類群種類豐富度;硅酸鹽含量高時,能提高硅藻的豐富度(圖4)。Unni和Pawar[16]在Mahanadi江的研究表明,對浮游植物種群影響最大的環境因子是水溫。西江肇慶段的浮游植物種類豐富度呈現高溫季節高,低溫季節低的特點(圖2),一方面,是因為西江大多數藻類物種直接喜好高溫,另一方面,高溫季節一般伴隨著高強度光照,有利于藻類進行光合作用。Lakshminarayana[21]調查發現Ganga江夏季的浮游植物種類從之前的37種增長到82種,這與夏季水溫升高和高光照有直接關系。此外,種類豐富度與徑流量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圖4),不難發現種類豐富度的季節波動與徑流量的季節波動規律關系密切[6]。Train和Rodrigues[22]在Baía江的調查發現洪水期的種類豐富度最大。高徑流量不僅可以從上游帶來更多的藻類物種從而增強藻類豐富度的累積效應,也可以通過更強烈的水體攪動作用使已沉降藻類和底棲藻類重新懸浮回到表層水體中,從而增加了種類豐富度。硅藻是調查江段浮游植物群落的最重要組成類群,硅藻物種的細胞壁組成需要大量的硅元素[23-24],因此硅酸鹽濃度的升高有助于硅藻種類組成的穩定和生物量的增長。盡管真浮游植物總種類數的周年變化趨勢與總浮游植物的變化趨勢及其相近,但是不同類群之間卻存在不一致性(圖2)。單從最主要類群硅藻和綠藻來看,真浮游硅藻種類數周年變化平穩,與硅藻總種類數的單峰模式及數值均存在顯著差異;而真浮游綠藻種類的周年變化趨勢及數值與綠藻總種類豐度極其接近,這說明調查江段的浮游植物物種組成中,硅藻組成主要依賴半浮游種類和偶然性浮游種類,而綠藻組成主要依賴真浮游種類。Istvánovics和Honti[9]認為江河浮游藻類的自我維持種群主要是半浮游硅藻物種,而真正的浮游種群主要是綠藻,其主要依靠周期性的外源注入。研究結果支持此觀點,但是所得到的半浮游和偶然性浮游硅藻物種主要來自于外源注入還是調查江段的底棲種類再懸浮,有待進一步研究和驗證。
調查期間,浮游植物生物量呈現明顯的雙峰型(圖3),且2個峰值均出現在4次洪峰之后。PCA分析結果顯示,水溫升高有利于硅藻、綠藻、藍藻和其它藻類生物量的增長,對裸藻的增長也稍有些好處,但是兩個峰值出現之前,盡管水溫持續上升,生物量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沒有明顯變化,很可能是因為水溫上升對浮游植物生長的促進作用被徑流量增大導致的稀釋作用所掩蓋。PCA分析結果也顯示,徑流量大時雖然有助于其它藻類類群生物量的增長,但對硅藻的生長不利,而硅藻恰恰是生物量的最重要貢獻者。調查期間,生物量的兩個峰值所對應的水體徑流量分別為3430 m3/s和1680 m3/s,代表了相對穩定的水體環境。巧合的是,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兩個峰值的比值(大/小)2.06近似等于各自對應的徑流量數值的反比值2.04(大/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體徑流量增大對浮游植物種群豐度的稀釋作用。Salmaso和Braioni[25]認為徑流量大不僅可以稀釋藻類密度,同時引起的水體渾濁可以削弱藻類對光的可利用率,相反,徑流量小,水體中懸浮顆粒少,水下光照條件好,在適宜的水溫條件下,浮游植物種群豐度和生物量均會出現較大增長[26-27]。Istvánovics和Honti[9]在匈牙利的3條河流的研究也發現,葉綠素a濃度與徑流量存在負相關關系。除稀釋作用影響外,高徑流量時浮游植物生物量還受制于較短的運輸時間和平流損耗的影響[28]。從各類群的相對組成上看,硅藻生物量占據絕對優勢(圖3)。Swale[29]的研究發現,綠藻主要在水流較快的江河上游江段占據優勢,而硅藻主要在江河下游江段占據優勢。其它江河的研究也發現,硅藻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并伴隨有大量不同的綠藻物種是世界上不同江河的基本特征[14-15,30-33]。真浮游植物生物量的變化趨勢和數值與總浮游植物極其接近,這主要得益于真浮游硅藻物種顆粒直鏈藻的優勢,其對生物量的最大貢獻接近100%(表1)。
綜上所述,硅藻和綠藻是調查江段浮游植物群落的重要組成類群,且硅藻在生物量上占據絕對優勢,這與國際上江河浮游植物的群落組成模式是比較一致的。但是硅藻的種類豐富度略高于綠藻,這很可能與調查江段的硅酸鹽含量比較豐富有關。浮游植物各類群的種類豐富度和生物量的周年變化趨勢均與水溫和徑流量的關系密切,這與國際上相關假說的結論也是一致的,不過水溫對種類豐富度和生物量的增長均起到積極作用;而徑流量對種類豐富度的增長起積極作用,主要是有助于真浮游綠藻種類的外源補充及半浮游和偶然性浮游硅藻的補充;徑流量對生物量的增長起消極作用,主要是徑流量的增大所帶來的稀釋作用減緩了生物量增長的速度。
致謝:營養鹽數據由穆三妞等協助測定,樣本采集由肇慶漁政支隊協助完成,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林強研究員幫助寫作,特此致謝。
[1] Forsberg B R,Araujolima C A R M,Martinelli L A,Victoria R L,Bonassi J A.Autotrophic carbon-sources for fish of the central Amazon.Ecology,1993,74:643-652.
[2] Skidmore R E,Maberly SC,Whitton B A.Pattern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phytoplankton chlorophyll a in the River Trent and its tributaries.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1998,210/211:357-365.
[3] Cloern J E and Dufford R.Phytoplankton community ecology:Principles applied in San Francisco Bay.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2005,285:11-28.
[4] Kowe R,Skidmore R E,Whitton B A,Pinder A C.Modelling phytoplankton dynamics in the River Swale,an upland river in NE England.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1998,210/211:535-546.
[5] Wang C,Li X H,Lai Z N,Tan X C,Li J,Li Y F,Pang SX.The study on community structure difference of phytoplankton in two Megalobrama hoffmanni spawning grounds of Xijiang River.Guangdong Agriculture Science,2010,4:156-160.
[6] Wang C,Lai Z N,Li Y F,Li X H,Lek S,Hong Y,Tan X C,Li J.Population ecology of Aulacoseira granulata in Xijiang River.Acta Ecologica Sinica,2012,32(15):4793-4802.
[7] Rojo et al.,1994.An elementary,structural analysis of river phytoplankton.Hydrobiologia 289:43-55
[8] Reynolds and Descy 1996.The production,biomass and structure of phytoplankton in large rivers.Arch Hydrobiol.Suppl.113:161-187
[9] Istvánovics V and Honti M,2011.Phytoplankton growth in three rivers:The role of meroplankton and the benthic retention hypothesis.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56(4):1439-1452
[10] Tavernini S,Pierobon E and Viaroli P.Physical factors and dissolved reactive silica affect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ynamics in a lowland eutrophic river(Po river,Italy).Hydrobiologia,2011,669:213-225
[11] Hillebrand H,D?rselen C D,Kirschtel D,Pollingher U,Zohary T.Biovolume calculation for pelagic and benthic microalgae.Journal of Phycology,1999,35:403-424.
[12] Van den Hoek,C D G Mann and H M Jahns,1995.Algae.An Introduction to Phyc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3] Bahnwart M,Hübener T and Schubert H.Downstream changes in phytoplankton composition and biomass in a lowland river-lake system(Warnow River,Germany).Hydrobiologia,1999,391:99-111.
[14] Holmes N T H and Whitton B A.Phytoplankton of four rivers,the Tyne Wear,Tees and Swale.Hydrobiologia,1981,80:111-127.
[15] Schmidt A.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toplankton of the Southern Hungarian section of the River Danube.Hydrobiologia,1994,289:97-108.
[16] Unni K S and Pawar S.The phytoplankton along a pollution gradient in the river Mahanadi(M.P.state)India a multivariate approach.Hydrobiologia,2000,430:87-96.
[17] O'Farrell I,Lombardo R J,Pinto P T,Loez C.The assessment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Lower Luján River(Buenos Aires,Argentina):phytoplankton and algal bioassays.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2,120:207-218.
[18] Descy J P,Leitao M,Everbecq E,Smitz J S and Deliège J F.Phytoplankton of the River Loire,France:a biodiversity and modelling study.Journal of Plankton Research,2012,34(2):120-135.
[19] Descy J P.Ecology of the phytoplankton of the River Moselle: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Hydrobiologia,1993,249:111-116.
[20] Devercelli M.Phytoplankton of the Middle Paraná River during an anomalous hydrological period:a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pproach.Hydrobiologia,2006,563:465-478.
[21] Lakshminarayana J SS.Studies on the phytoplankton of the River Ganges,Varanasi,India,Part II“The seasonal growth and succession of the plankton algae in the River Ganges”.Hydrobiologia,1965,25:138-165.
[22] Train S and Rodrigues L C.Temporal fluctuations of the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of the Baía River floodplain,Mato Grosso do Sul,Brazil.Hydrobiologia,1998,361:125-134.
[23] Hoetzel G,Croome R.Population dynamics of Aulacoseira granulata(EHR.)SIMONSON(Bacillariophyceae,Centrales),the dominant alga in the Murray River,Australia.Archiv fuer Hydrobiologie,1996,136:191-215.
[24] Odebrecht C,Abreu P C,M?ller O O,Niencheski L F,Proen?a L A,Torgan L C.Drought effects on pelagic properties in the shallow and turbid Patos Lagoon,Brazil.Estuaries,2005,28:675-685.
[25] Salmaso N and Braioni M G.Factors controlling the seasonal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in the lowland course of a large river in Northern Italy(River Adige).Aquatic Ecology,2008,42:533-545.
[26] Carvajal-Chitty H I.Some notes about the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phytoplankton of the middle Orinoco River.Hydrobiologia,1993,249:117-124.
[27] Piirsoo K.Phytoplankton of Estonian rivers in midsummer.Hydrobiologia,2001,444:135-146.
[28] Townsend SA,Przybylska M,Miloshis M.Phytoplankton composition and constraints to biomas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an Australian tropical river during base flow.Marine and Freshwater Research,2012,63:48-59.
[29] Swale E M F.Phytoplankton in two English rivers.Journal of Ecology,1969,57:1-23.
[30] Hudon C,Paquet S,Jarry V.Downstream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in the St.Lawrence River(Québec,Canada).Hydrobiologia,1996,337:11-26.
[31] Ha K,Kim H W,Joo G.J.The phytoplankton succession in the lower part of hypertrophic Nakdong River(Mulgum),South Korea.Hydrobiologia,1998,369/370:217-227.
[32] Zalocar de Domitrovic Y.Structure and variation of the Paraguay River phytoplankton in two periods of its hydrological cycle.Hydrobiologia,2002,472:177-196.
[33] Devercelli M.Changes in phytoplankton morpho-functional groups induced by extreme hydroclimatic events in the Middle Paraná River(Argentina).Hydrobiologia,2010,639:5-19.
參考文獻:
[5] 王超,李新輝,賴子尼,譚細暢,李捷,李躍飛,龐世勛.西江廣東魴產卵場浮游植物群落差異分析.廣東農業科學,2010,4:156-160.
[6] 王超,賴子尼,李躍飛,李新輝,Sovan Lek,洪頤,譚細暢,李捷.西江顆粒直鏈藻種群生態特征.生態學報,2012,32(15):4793-4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