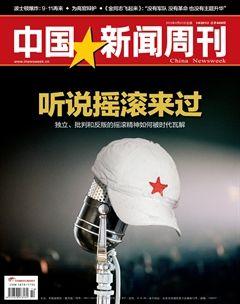米蘭·昆德拉如何進入中國
楊敏
幾年前,接力出版社總編輯白冰去了趟捷克首都布拉格。徜徉于布拉格大道上,看著街道兩邊開著的窗戶,他想,哪一扇會是托馬斯的窗?
托馬斯,即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主人公。
白冰第一次聽說米蘭·昆德拉這個名字,還是近20年前,那時他是作家出版社的編輯。1985年,在國家出版局于西雙版納召開的一次青年編輯培訓班上,有專家提到,東歐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是米蘭·昆德拉。
“當時我想,東歐跟我們有歷史性的相似,知識分子命運、社會精神一致,所以我們肯定早晚要引進他的作品。但不知道誰對他比較了解。”在接力出版社的總編輯辦公室里,白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回北京后,白冰四處打聽,得知確實有人正在翻譯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并且正是他熟悉的作家韓少功。
“政治煽動性大”
在白冰找到韓少功之前,昆德拉作為一個有爭議的捷克流亡作家,在中國只被極少數文學圈內人知曉。
1977年,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外國文學動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刊介紹捷克作家伐措立克和昆德拉》,作者是《世界文學》編輯部副編審、捷克語翻譯家楊樂云。這篇文章中,簡單介紹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但由于刊登在內部學術刊物上,影響并不大。
1984年,正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研究生的高興從同學那借到了昆德拉的英文版小說《可笑的愛》,這是他第一次接觸這個陌生作家的小說。
“跟其他小說感覺很不同,《可笑的愛》是那種極為機智又十分好讀的小說。表面上看,都是些情愛故事或干脆就是情愛游戲,實際上卻有著對人生、對世界的精深的思考。”《世界文學》現任副主編高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昆德拉被正式介紹進中國,是在1985年。文學評論家李歐梵在《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了《世界文學的兩個見證:南美和東歐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啟發》,介紹了南美作家馬爾克斯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以及他們各自的代表作。
“昆德拉寫的是小人物,但運用的卻是大手筆,不愧為世界文學的一位大家,足可與馬爾克斯(1982年憑借《百年孤獨》獲諾貝爾文學獎)媲美。”李歐梵寫道。他認為,昆德拉沒能獲獎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煽動性大,也較年輕”。
1986年,在武漢大學英文系進修了一年之后,韓少功以湖南作協專業作家的身份赴美公干,偶然從一位美國作家那里得到一本英文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他一看之后,立刻產生了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沖動。“不僅在于它表現的歷史和思想對中國人有一定的啟發性,而且作者那種輕巧的‘片斷體,夾敘夾議的手法,拓展了文學技巧的空間。”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韓少功的二姐韓剛在湖南一所高職學校任英語老師,也是文學愛好者,于是兩人決定合作翻譯。
大概半年之后,譯稿初成,由韓少功統稿完成。
他聯系了幾家出版社,都遭遇退稿,不過他并不認為是出于政治原因。“1986年的中國已經逐步打開國門,氣氛相對寬松。出版社拒絕這本書,可能只是覺得這個作者沒什么名氣。”韓少功回憶。
內部發行
其時,從西雙版納回來的白冰打聽到韓少功已翻譯了一部米蘭·昆德拉作品,立刻與他聯系。
“看完韓少功的譯稿后,覺得非常好。我感覺昆德拉的寫作有一個龐大的哲學理論系統支撐,比如對‘輕與重的思考。同時,他把故事寫得很吸引你。你感覺,他的那些故事都是冰山之一角,留給你品味琢磨思考的,是水面下沒法看到的部分。而且,他很注重人物的情感糾葛、碰撞和命運的描寫。”白冰說。
白冰所在的作家出版社第三編輯部,負責文化類作品出版,當時除了出版銷量火爆的瓊瑤、岑凱倫的言情小說之外,還在出一套“作家參考叢書”,介紹各種流派的代表著作,作為透視世界思潮和文學潮流的一個窗口。昆德拉的作品也被安排在這個叢書之列。

但昆德拉身為捷克的異見者,被東歐學術界貼上“反共”的標簽,引進他的作品,畢竟具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當時第三編輯部的副主編亞芳(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鮑昌的夫人),也看到了昆德拉小說的價值。她與白冰一起,跑了一趟新聞出版署(1987年1月由國家出版局改組而來),詢問出版的可能性。對方建議他們,最好先去中國社科院咨詢專家。
他們去社科院,找到了外國文學所東歐文學研究室的專家。專家看后稱,就文學價值本身來說,沒有任何問題。但專家建議他們,政治方面最好去問問外交部。因為當時捷克總理要訪華,昆德拉是捷克持不同政見者,如果在他訪華前出那么一本書,恐怕對外交工作不利。

小說作品
《玩笑》(1967 年)
《好笑的愛》(短篇小說集,1968年)
《生活在別處》(1969年)
《告別圓舞曲》(1976年)
《笑忘書》(1978 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4 年)
《不朽》(1990 年)
《慢》(1995 年)
《身份》(1998年)
《無知》(2000 年)
他們又去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態度很堅決:此書現在不能出版。
1987年4月,捷總理什特勞加爾訪問中國,這是30年來捷克斯洛伐克總理首次正式訪華。同年6月,中國領導人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總理的訪華結束之后,白冰再次嘗試與外交部溝通,并表示可對小說作一些刪改。
最后,刪了三千來字,主要是托馬斯和特麗薩之間的性描寫,還有一些敏感詞匯,比如“當局”“主義”等。
韓少功也認為,刪掉的只是一點點,書的原貌大體得以保全,還算好。
對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一書名,白冰與韓少功討論來討論去,覺得有點繞,不太利于傳播,但也沒有更好的名字蹦出來,只好用它。
“他引用的是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的觀點。事物都有兩級,黑暗與光明,輕與重,溫暖與寒冷等。從我們的習慣來說,重是不能承受的,但其實輕也是不能承受的。”白冰說。
最后,新聞出版署批準,此書以內部發行的方式面世。憑司局級以上的證件,可以在新華書店的內部書柜臺買到(《金瓶梅》也是如此)。
1987年9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首印24000冊。1989年,此書獲準公開發行,第一年發行了70萬冊。
這一發行量,雖然比不上瓊瑤,但在文學作品中也算翹楚了。“‘布拉格之春后,捷克傳統的價值觀被摧毀,新的價值觀還沒建立,人在精神上非常空虛。這與中國當時的國情非常相似,所以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白冰說。
捷克使館抗議
就在韓少功翻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剛剛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留校任教的景凱旋偶然看到了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
由于比較關注當代文學,景凱旋較早知道了西方現代派的代表人物卡夫卡、薩特等。剛好有位認識的美國學者來南大訪問,隨身帶了一本《為了告別的聚會》,就將書送給了景凱旋。
看完之后他感覺,此書既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誕小說,亦不同于中國當代的反思、尋根小說。
“我們受的審美教育是由西方19世紀浪漫主義思潮定義的一種精英文學觀,追求崇高的事物。昆德拉表現的卻是價值的反諷,同時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對我來說,就好像是打開了另一道思維之門。”景凱旋后來回憶。
在朋友的鼓勵下,他著手開始翻譯。大概四個月之后,小說一稿完成。
景凱旋先與上海譯文出版社聯系,但編輯沒有聽說過昆德拉。與韓少功的經歷一樣,他被委婉地回絕了。
景凱旋的太太徐乃建認識韓少功,當時正與他商談籌辦一本同人雜志(即后來的《海南紀實》),得知韓少功也翻譯了昆德拉的書,并正在跟作家出版社談合作。
經韓少功介紹,1987年4月,景凱旋在作家出版社的辦公室里見到了編輯白冰和崔艾真。
景凱旋后來回憶,自己當時的樣子很可疑,“土里土氣的,手里提著一個提箱,里面裝著一本全是寫性愛與政治的書”。崔艾真說他“看上去挺學生氣的”,讓他多少有些沮喪。
但第二天,崔艾真就給他打來電話,說決定出版這本書,她來做責編。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樣,作為“作家參考叢書”,內部發行。
編輯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幾乎沒有作任何刪改。8月,《為了告別的聚會》出版。
1988年11月,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外國語學院聯合召開了東歐當代文學討論會。其間,米蘭·昆德拉作為東歐代表作家,首次在國內的學術會議上被提及。
一種意見認為,昆德拉的作品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譯介時應持謹慎態度;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昆德拉的作品從哲學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復雜的人生,具有相當的藝術深度。
此后,作家出版社繼續和景凱旋合作,于1989年1月出版了《生活在別處》中譯本。本來《玩笑》也將緊接著出版,但就在即將出版之際,捷克使館提了抗議。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說,1967年未經刪改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連續再版三次,均被搶購一空,成為當時重大的文化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的作品被列為禁書。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一直到現在。
多年來,“反共”一直是貼在昆德拉身上的意識形態標簽。但他自己卻認為,這是理解他的小說“最陳腐的方式”,自己的作品對人性的探索遠在政治之上。在1980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有人稱《玩笑》是對斯大林的有力控訴,昆德拉當即聲明:“別拿斯大林為難我了,《玩笑》是一本愛情小說。”
不過,因為牽扯到外事,作家出版社不得不暫停《玩笑》的出版發行工作。一直到1991年1月,《玩笑》才在國內公開出版。
但在譯者景凱旋的印象中,在中國,《玩笑》的影響并不及《生活在別處》大。“《生活在別處》的主題契合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人們反思革命激情、回歸世俗情感的思潮。到了90年代的商業大潮,這種契合就更不用說了。”景凱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與米蘭·昆德拉聯系
90年代初,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參考叢書”又相繼推出了盛寧翻譯的《不朽》和唐曉渡翻譯的《小說的藝術》。時任編輯部主任柳萌后來回憶,“出版了昆德拉幾部作品后,這套‘作家參考叢書真正名實相符,成為讀書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
昆德拉很快在中國成為一個時尚。景凱旋記得,有一段時期,幾乎人人言必稱昆德拉,到處都在討論他的小說形式、小說理論。論者大都用流行的存在主義話語去解讀他。
199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余杰發表了《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擔什么?》,像一記炸彈擲入文學界,引起火花無數。文中稱:“昆德拉有一種很強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戲的態度。而哈維爾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圣人。”趨前者、避后者,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層面的盲點”。
對此,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撰文回應,認為在歷史罪責并未得到公開徹底清算的語境下,要求知識分子遵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觀,是走向另一種極端,也是危險的。
1992年7月30日,中國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按照公約規定,出版境外作家的作品,必須征得作家本人同意,或取得原作出版商的中譯授權。
1996年,作家出版社曾經策劃出版昆德拉全集中文版,與昆德拉的經紀人取得了聯系。
白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經紀人所提的條件是:第一,支付從前的版稅;第二,從法文版本翻譯;第三,不能做任何修改。前兩點都沒有問題。按出版時的版稅6%~10%計算,這筆錢并不算多。但就是第三點,出版社無法保證。
據白冰所知,國內許多家出版社都曾通過各種渠道與昆德拉聯系,但都沒有結果。
這期間,市場上開始出現各種盜版,較常見的有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的馬洪濤的譯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的李元芳所譯的《米蘭·昆德拉精品集》。
2002年5月,上海譯文出版社終于一舉購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國大陸的中文版權。出版授權中對于發行等作了近乎苛刻的規定,包括每半年報告一次印刷、銷售和庫存數字,以及下一步的計劃等。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出版前言里,韓少功寫道:“我們希望國內的捷文譯者能早日從捷克文中譯出這部小說,或者,有更好的法文譯者或者英文譯者來干這個工作,那么,我們這個譯本到時候就可以擲之紙簍了。”這一天終于來了。
200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由南京大學法語教授許鈞從法文版重譯,并增補了小說中被刪節的部分,書名改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為了告別的聚會》由《世界文學》主編余中先從法文版重譯,書名改為《告別圓舞曲》。《玩笑》和《生活在別處》等均由法文版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