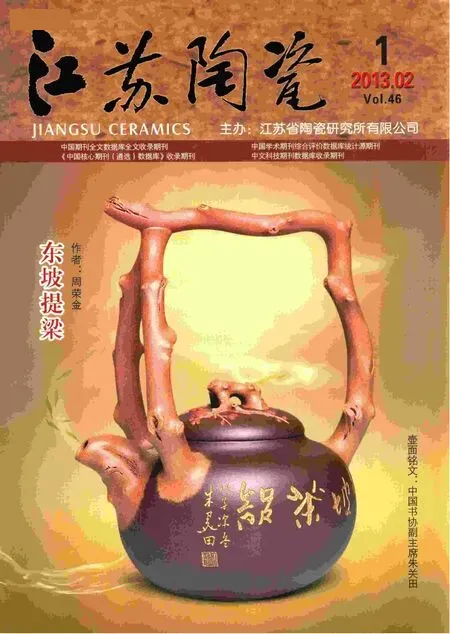紫砂陶刻——書法與陶藝孕育的明珠
胡春福
(宜興 214221)
從春秋時期“陶朱公”起訖,紫砂藝術的萌芽便如星星之火開始燎原。及至宋代,紫砂藝術開始了“直掛云帆”式的長足發展,一路行至明、清時期已是大盛。而隨著詩詞、繪畫、雕刻、金石等等藝術的加入,紫砂藝術的生命力更見強勁。及至今日,已形成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蔚為壯觀的局面,紫砂的生命得到了永恒。這期間有紫砂藝人的辛苦鉆研,也有文人雅士們文學、書法、繪畫等全方位技藝的錦上添花之功。譬如,陶刻的加入就很大層次地提升了紫砂的藝術價值和魅力。
紫砂陶刻,通俗說法即是在紫砂器皿上進行的書畫展示,這需要陶刻者具有很高的書法、繪畫功底。據史料記載,紫砂陶刻在明代萬歷年間就已風行,時大彬之秀麗、沈子澈之渾樸、陳子畦之飄逸,在當時皆有盛名。到了清代,陳曼生的橫空出世更是造就了紫砂陶刻史上的一座豐碑。著名的“曼生十八式”不僅造型精美、制作精良,是飲茶品茗之上層良品,更是在壺器中契合了制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悟,并集詩、書、畫、印于一壺,很大地影響了后來者的制壺匠心及風格。之后,像鄭板橋、吳昌碩、任伯年等一大批書畫金石名家,也都紛紛涉入紫砂制壺的行列,用自己渾厚的書畫修養為紫砂的藝術魅力添磚加瓦。一時之間,紫砂陶刻作品花樣百出、精彩紛呈,極大地提升了紫砂壺器的藝術品位。
1 紫砂陶刻是對制壺者書法筆法功底的考驗
書法藝術是我國人民獨創的表現形式,自形成便廣受人們喜愛,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書法的魅力,即在于以寥寥可數的線條傳達出書寫者了無痕跡的無形“靈心”,可謂“化簡為繁”的典范。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到東漢、魏、晉的草書、楷書、行書,書法的形體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使是同一時期、同一書體,作者不同,字體傳達的意蘊也大不相同。故而,書法的魅力堪稱無窮無盡、了無涯際。
紫砂陶刻,書法的書寫載體有了很大的不同,故而對陶刻藝人的書法筆法功底極為考驗。中國的刻字有著悠久的傳統,最早的文字就是用刀筆刻出來的,繼而刻石、刻碑、刻磚、刻陶、刻玉、刻瓷、刻匾、刻竹、刻木、刻銅等等發展龐雜。而紫砂刻字,由于紫砂特定的材料、工具、技法、表現內容和欣賞所形成的獨特風格特征,又與一般的刻字藝術有著不同的表現手法。紫砂為泥制成坯,故易于刻劃,但對于泥坯的干濕程度卻有要求,并且砂之粗細也大有講究,難以把握,因此刻字一般用薄刃快口之尖刀;刻石章用平口鈍刀,石轉刀不轉;而紫砂坯體有平面,并且更多的是弧面,體大易損,一般就只能以刀就坯,在這樣的諸多限制下,要把傳統書法的神韻和風采充分而完整地傳達出來,刻字者沒有渾厚的書法功底顯然是不成的。如作品“天地玉壺”(見圖1),在四方而圓平的壺身上部用娟秀流轉的小楷雕鏤了“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個小字,環延壺肩,使整個壺透著清秀的雅致,很有些“冰心”的味道。同時,又于壺蓋上鐫刻了“天地玉壺”四個大字,粗短方正的字體很能體現天地初開時的那份混補。兩種字體粗細對比、大小呼應,更好地體現了“冰心”的真誠和天地的渾樸。

圖1 天地玉壺
2 紫砂陶刻是對書法藝術素養的考驗
蔡元培先生曾說過:“中國之畫與書法為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可見,無論書法還是繪畫都不僅僅是線條、結構和章法的技藝,其間還包含著文學的素養和趣味,書法和文學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文學,靠書法這一載體傳世;書法,靠文學這一形式體現價值。如我國古代著名的書法著作《蘭亭序》,不僅體現了王羲之書法的精妙之處,而且辭藻華美、文采斐然,堪當寫景文學的典范。故而,紫砂陶刻也只有做到壺藝、銘文、字畫、鐫刻結合俱佳,融為—體,方能“壺隨字貴,字隨壺傳”。
“曼生石瓢壺”(見圖2)采用傳統“石瓢壺”的傳統造型。壺身呈梯形,曲線柔和流暢,造型渾厚樸拙;足為釘足,呈三角鼎立狀支撐,給人以輕靈而穩重之感;壺身八字造型,造成一個主視角度內的呈型表面,亦曲亦直,皆顯現簡樸大方的氣度;直流,簡潔見力度,為暗接處理,融于壺身整體;壺把呈倒三角勢,與壺身之型互補,形成和諧的美學效果;平壓蓋、橋鈕干凈利索、比例恰當,充分體現出“石瓢壺”秀巧精工的特點。

圖2 曼生石瓢壺
《論語·雍也》里有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贊美的就是孔子的弟子顏回生活簡樸、安貧樂道的精神節操,也是后人對士子、文人、有識之士雖處陋室仍氣節不改的贊許。故而,基于這樣的文化背景,在“曼生石瓢壺”的壺身刻以筆法渾樸的“安居”二字,以期能為壺器“畫龍點睛”,使其精神內涵得到更大程度的體現。
無論是為適應壺器特點而加以錘煉的書法雕刻功底,還是為體現壺器韻味而加以點綴的只言片語,紫砂陶刻已經成為紫砂壺器制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在今日紫砂壺器精品紛呈的時代,紫砂藝術如果沒有陶刻的加入,將會顯得蒼白無力。而好的陶刻藝術的滲入,不僅能作為壺器裝飾,給整個壺的造型錦上添花,而且紫砂陶刻本身“刻字”的內涵,就足以使壺器欣賞者品味良久,極大地增加紫砂壺器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