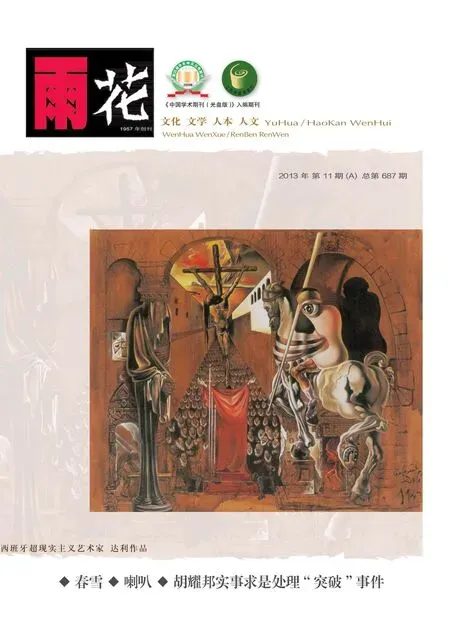一個人的四季
●石淑芳
一個人的四季
●石淑芳
我攀援的好身手為我的種蘋果打下了很好的伏筆,疏花套袋,摘蘋果,哪一樣活兒都是丈夫望塵莫及,他驚嘆我金雞獨立地站在果實累累的枝頭,隨風搖擺。
掌里的春天
上蒼輕輕地翻轉一下手掌,雪花打著一觸即融的調皮旋轉,在村莊上空漸化為黏濕的春雨。我從地堰上走過來,手里提著一個舊竹籃,腰背挺直,深呼吸,我聞見春的氣息——原初嬰孩那樣的稚嫩香甜。我的春天就要從我的掌心,從我的竹籃開始。不寒的山風躡腳過來,輕輕把我山花一樣吹開。低頭撿著地軟,經年累月生活在這兒,我知道哪塊斜坡上有白蒿,誰家荒地生小蒜,哪片谷底長著蕨菜,順著節令順著自己的指尖,采摘上天賜予人間最鮮潤的野菜。
不用查看日歷,憑著本能跟著季節的節拍,接過母親傳下來的提籃,把一個個采摘的日子裝下。只是我的采摘,從母親手里傳過來的時候,已經更改主題——母親為生計,我為情趣。有文友央我幫他把山間植物的節令記下,以備寫作之用。我哈哈大笑——的確,對于山間植物的枯榮,我比他這個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有著實踐大于理論的識見。初春灑在枯草上的地軟撿過,就要去挖伸出嫩紅尖尖的小蒜。二月小蒜,香死老漢。路邊的小車上常有路人下來挖小蒜,山里人進城,城里人上山。過去都是農人挖野菜,現在農人進城了,孤寂的山鄉偶爾走來嘗鮮的城里人。不止一次從別人的文字間讀到,年輕時對村莊選擇逃離,年長時選擇回歸。人類的感情世界在很多事物上,具有外在和內在的相似和必然性。我在想這些問題的時候,已經爬上了一個小山包,從這兒望下去,小村凌亂而荒涼。村子里的人越來越少,小賣部的老人抱怨生意太冷清。采青的人更少了,大山坳里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在一起。“上河里的鴨子下河里的鵝,一對對毛眼眼望著哥哥。”隨口喊出悠揚的信天游,恰到好處地供我在上坡時,自由舒展地吐納山鄉清冽純凈的空氣。
一棵柿樹枝椏蒼勁,它已經很老了,從我爺爺的爺爺那會兒站到現在。樹比人年輕,它很輕巧地跨越幾代人。柿樹底下是一個大斜坡,長著眾多的藥材:蒼術,黃芩,血參和柴胡。對于它們的習性用途,我再熟悉不過,我幾乎從年少挖到現在,只要村里來了收藥材的,山坡上就爬滿了人。山風吹動我紅色的紗巾,吹裂了我的嘴唇,我和女孩們說笑著,聊起了打麥場上露天電影里面優雅的女主人公,爭論不休。粗糙的小手從泥土中扯出了一根根鮮潤的藥材,脆笑吵鬧和民間小調把個山坡翻騰得沸沸揚揚。
可是仿佛一夜間,村里人隨著春運的人流奔赴北京上海廣州或者深圳。山野成了鳥兒的陣地,一塊玉米地里,站滿了覓食的喜鵲,四五丈高的楊樹梢是它們排練歌聲的舞臺。喳喳的叫聲本來是傳遞喜氣,可是沉寂的小村沒什么可以歌唱的理由,幾個在城里住到彌留之際的老人,回到家里的土炕上,等待著生命的終止符,所以村子最近幾天回旋著貓頭鷹的嚎叫。以前以為這不過是迷信的說法,現在親歷動物叫聲的預言,相信這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交談和感應,動物異于我們人類的敏銳功能。
拐過一道山梁,下了一個斜坡,是一片蘋果園。村里有蘋果的人家已經很少了,只有山道邊這一片果園,主人看得命根子一般。他有一個弱智的兒子,愚鈍的兒媳和上學的孫女,一家人靠種蘋果生活。他的果園地勢高,通風排澇,何況他用加倍的勤勉來抵抗病蟲害的入侵。我走近他果園的時候,他正在給果樹修剪枝條,小心地用刀片剔除樹身的病灶。我一眼看見樹下一片片破土而出的嫩紅小蒜,這樣鮮嫩的野小蒜是做湯和攤煎餅的好佐料。他一邊和我嘮著家常,一邊拿手中的鐵锨給我鏟出好多。
今年春季的氣溫偏低時間長,對面還沒有粉紅的山桃花和黃燦燦的連翹花扮靚山坡,也沒有一個采藥的人影。我的鄉鄰們紛紛去城市的叢林覓食,白凈許多的膚色和內斂的微笑,定是掩藏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閱歷和滄桑。而山村,是永不背叛地守候著,無論你見還是不見,它就在那里,不離不棄;你念或者不念,熟悉就在那里,不來不去……
從山道上跑下來的時候,我健步如飛。山鄉女人的春天,從手掌心開始,年年歲歲。
一個人的河岸
我的村莊因穿村而過的山溪,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們,比如慕名遷入的外來戶和山區支教的老師。傍水而居的普通村落,有一個無比吉祥的名字,柔情的水,是她頭上最高貴的王冕。
夏日,我如吐著舌頭尋找清涼的蛇,將自己的腿腳埋在河水里。高挽褲腿蹚來蹚去,是我最尋常的消遣,從少年到中年。村莊戶口冊上的人口一直在添加,可實際居住人口卻在減少。考學,打工,定居城市,年輕人拋棄村莊義無反顧負債累累地沖向現代文明。老人婦女兒童是最后城堡的守候者,守候村莊孤寂的鳥鳴。村子很靜,靜得我聽見自己化身高爾基筆下的海燕,期盼一場暴風雨的洗禮。我在暴雨中的亢奮無人能解,每一顆細胞恰似不遠處山頭冒出的防雹彈。暴雨喚起我孤單枯燥里的麻木,還免費洗刷了窗鏡外積攢許久的塵埃,在前面的山坳掛了一道奇險的瀑布,最酣暢的是帶來地動山搖的山洪。山洪激昂的歌聲不可阻擋地削平村人心頭的寂寞,順勢銜走上游山坳兩根木頭搭成的小橋,席卷了老鼠的家園,擊昏了小魚和螃蟹。打翻草叢從各個山頭匯聚蜿蜒而來的河水,攜帶斷頭的泡桐小雞的尸體和半熟的西瓜怒吼著大江東去,河岸散站著幾個打著雨傘展覽河流豐富物產的人。暴漲的河水輕易地搬走一塊礙事的山石,清掃了河岸的垃圾,奮力把一棵陳年老槐連根拔起。河水的每一個波紋里都藏著無形的刀劍,它一路披荊斬棘,一改溫柔的手臂生出威猛的力量。人們以敬畏的目光注視著河水的一往無前,并且堅信:河水愿意帶走什么就可以帶走什么。
河水也會留下什么——拓展疆域后的河床上滿是亮麗的石塊。一塊小小的陶片,沉淀陶身的土銹訴說著它歷史的久遠,陶身的花紋鐫刻那個時代的文明,它泅水而來,安臥在我的手心。它是古人的一只手,攜帶祖先的溫度跨越時空和我相握,雖說我只是一愚鈍農婦,然上蒼之恩寵不勝驚喜,不無雀躍。
赤腳走過沙灘,是我在影視劇里無數次體會到的浪漫。也許我終生也沒有機會去海邊,可是我可以赤腳穿過小河。彎腰的柳樹倒伏的水草和改了河道的水流,是小河新梳的妝容。一夜之間河水爛漫隨意地把河床的版圖收拾得面目皆非:這邊一片細沙沒有雜質,那邊一片淤泥是廣袤的沼澤,中間給洗澡的孩子挖了一個天然的澡池。運沙的三輪車奔突不停,車主疙瘩叔的瘦臉上喜氣洋洋,像得了天大的便宜。暑假的孩子滿河灘跑,每個人手里都有不一樣的撿拾,河灘是他們開門的阿里巴巴大寶藏。我赤腳在淤泥灘上拓下自己的腳模,略略干硬的河泥在足底的踩踏下,如和熟的面團一樣滲出水潤和勁道來,黃泥按摩腳底的舒服,只怕是只有我這等癲狂的人才可以享受。炎熱的盛夏正午,伴著不遠處洗澡孩子的嬉鬧聲和樹叢陣陣蟬鳴,河灘淤泥是我大大的畫布,率性的雙足在上面劃拉下簡約的花草,配上一行不知寫給誰的I love you。
勞煩我牽掛的是回流逃生的小魚,這些倉皇的奔逃者選擇一條水小的河溝棲息。我一般都養著這些小可愛,喂蟲喂饃,可這些家伙不領情,不斷地尋找機會逃脫我的水盆。大大的水盆里我放了細沙和水草,仿造小魚的家,可還是阻止不了一條小魚對自由的極端渴求,竟然冒險一躍,摔在水泥地上啪啪有聲,我及時發現把它救起。我揣測生活中大多數的仿造和模擬,不過是一廂情愿式的臆想,根本不可能解決心靈本真的飛躍。
一天早上我發現水盆走失了一只螃蟹,隔了幾天,在我徹底忘了它時,小家伙出現在我的床前地上,其時我正美夢笑醒。它灰頭土臉羞怯地抖摟著爪子,我讓它端坐笤帚小心地把它捧近水盆,那一刻,我端詳著它離水的憔悴和怏怏的可憐,決定放生。水盆里的小魚沒有自由已經損失不少,我沒有權利踩著它們不斷漂移起來的尸體,泛濫自己自娛自私的愛。當我的小魚小蝦小螃蟹們迫不及待地撲棱進河水,長翅膀似地在河水里飛,我生出離別的惋惜和放手的欣慰,感謝這些天它們生趣盎然的陪伴。
暴雨帶來的山洪,送給我的禮物太多。站在我一個人的河岸,我企盼單調無波的心靈下起暴風驟雨,暴漲的河水中會沖走什么,也會留下什么。
一個人的秋天
地堰上的野薔薇果紅了,摘一把穿起來戴在脖子上,頭上別著野花,田埂上顯擺的女孩,是童年的我。母親說生我時漫山遍野開滿了黃燦燦的野菊花,鋪天蓋地的藥香彌漫著小村莊。秋天云淡風爽,花艷果靚,當我一年又一年坐守在斑斕的秋色中,我很慶幸自己選擇在秋天來臨,并有我香薰的村莊熱情的守候。我不想表達我對秋天的感覺,喜歡已經不言而喻,所以更愿意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我展示在秋天面前的臉孔是奔放的,熱烈而直白。山坡上的樹葉在初秋的風中,微微有些凋零,這是風霜的痕跡,也更真實。如同一個很歡欣的人,她偶爾悄悄的眼淚。
樹梢有個鳥兒捉軟的柿子嗎?別愁,看我的,哪怕這顆柿樹長在懸崖,我也能身輕如燕地攀上去。我火紅的襯衣在樹梢飄搖,母親老遠就吆喝:我的饞嘴乖乖,你要我的命呀?快下來吧。母親的罵在我童年并無多少震懾力,她無數次地揚言要捶我,卻沒有正經八百地實踐過一回。
母親是知道的,我的腿腳有多么利索,從東山到西山。
榛子李子酸葡萄五味子,它們在秋天以多么飽滿的激情充實過我的嘴巴。滑爽的秋風掠動我的長發,溫暖的秋陽撫照著我被酸汁甜液喂飽的肚皮,崖畔上,我周身被陽光觸摸的亢奮,嘴里隨便飛出篡改了歌詞的歌曲兒。野酸棗沒誰敢吃,摘不著手要被扎,可是我想摘多少就摘多少,我剛才還在山頂,一溜煙又出現在坡底。我攀援的好身手為我的種蘋果打下了很好的伏筆,疏花套袋,摘蘋果,哪一樣活兒都是丈夫望塵莫及,他驚嘆我金雞獨立地站在果實累累的枝頭,隨風搖擺。一個蘋果只要在我手心掉個,立馬分出等級,蘋果樹下一筐一筐泛著紅潤光澤的蘋果,全部接受過我輕快地檢閱。它們整裝待發,越過崇山峻嶺,飛到山外無數個客廳的水果盤里,這也讓我愉悅,不是嗎?我的勞動頓時有了歌唱的理由。
現在我不爬山也不攀樹了,可是山間還是我最愿去的地方,身姿多了幾分歲月滑過時留下的持重,母親催我干活,丈夫外出打工,留給我要干的活確實太多了,不僅蘋果要摘,玉米要掰,還有快熟炸的豆子沒拽,母親看著我沉靜的笑容說,你這孩子,早先的好腿腳哪里去了呢?我說,明天又是一個好日頭呢。母親不知道,這其中固然有歲月賦予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現在農人漸漸少了,山野上的果實更豐厚了,我無須太過奔忙。玉米地里,我幫一只羽翼不太豐滿的小鳥尋找走散的媽媽;和覓食的野兔碰面,我急慌慌地追它到地堰;摘蘋果累了,我把自己倒掛在蘋果枝上,仰看晴空半閉眼睛,晃晃悠悠做開了秋夢。母親以充滿擔憂的口吻說,你啥時長大呀?我沖著我的嘮叨媽媽笑,我的笑適合開在曠野,一層又一層,追逐著迷霧和流云。
我的開心沒有偽裝,快樂是一天,不快樂也是一天,我為什么不讓自己很快樂呢?這些道理不是我從書上讀來的,而是我在笑的時候就知道的。有的人說他很喜歡山村生活,以前我覺得矯情,現在我認為是真實的,沒誰在文字里對著自己的心說謊吧,喜歡山鄉,喜歡山鄉物產豐富的秋天。何況我本來就在這兒,本來就愛這兒的一切。
時雪彼時雪
曾經寫過一首詩,《愛是一種病》。這樣的詩不愿示人,在生活節奏如此之快的今天,連偶爾翻曬的機會也沒有。可是不期然的心靈瞬間,一個雪花飄飄的靜夜,關于詩的種種細微情節不由自主泛上來。
我會寫漢字不久就會寫詩,在今天看來,最初的詩歌沒能逃過類似口號的厄運。可是無知者無畏,盲目者自大,其時賀年卡盛行,即使腰包干癟,也要偷雞蛋賣錢打腫臉充胖子,買了一沓賀年卡分發給同學。不屑那些現成的泛濫的祝詞,親力親為給每個人都寫上別具一格的祝福,顯擺一下咬文嚼字的本事。不敢回首當年的字體和句子有多么蹩腳,踩著淺一腳深一腳的積雪,一家家小賣部去尋找,能夠接近內心意愿的卡片。
有一個小賣部的櫥窗上掛著一張日歷畫,一個嬌媚的女孩,側目蹙眉,下面幾行俊麗的文字:此情無計可消愁,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可是那張該死勾魂的畫,竟然要兩塊錢。我木木地站了一下午,小賣部的主人表情明顯地煩我,我在他鄙夷的眼神中不停地咀嚼和反芻這些字句的情和境。
我當時可能是病著的,但自己并不覺察,我花費半宿熬夜點燈地寫了一封長信,以賀年卡為由頭夾雜著對生活的自以為是寄了出去。可想而知我沒有收到任何回音,我病著時對方很清醒。清醒的人給我狠狠一擊,我需要感謝他的清醒,我把這種清醒看做藐視,在以后的生活中加倍搏殺,奢望付出和收獲成正比的未來,能為我的日子和自尊帶來一線生機,我的動力來源于我痛心疾首的缺失。
我在別人的文字間讀到過,特別是路遙的《早晨從中午升起》,作家需要忍受心靈的煎熬和生活的不堪,但卻絲毫不影響我既定的信念,在當時的我來說,從事寫作是自己為自己定下的宏遠目標。我幻想著,有朝一日,我會寫出一本書,然后把我的書送給他。多年以后,我真的寫了一本書,可是送書的念頭和理由竟然一點也找不到。寫作并沒有我想象的如何崇高,在無數的勞動者那里,只不過是從事一種很普通的勞作。年齡也逐漸平復我的狂熱,現在就算我當街看見他,或者會場握手,抑或他是局長也罷科長也罷,我心靜如水。雪夜徘徊在小街,為了一張體面的信紙,敲開一家又一家的門,寫錯一個字就更換一張信紙的那個女孩,現在在哪里?此時非彼時,那個季節的雪和現在的雪畢竟時過境遷。
和我擦肩而過的人像那漫天的飛雪,其中有無私溫厚的兄長,陽光單純的大學生,銀須飄飄的伯樂恩師,或幽默或奇崛或眼淚都笑出來的開心,生活打開了豐富的異性資源和窗口,我的詩歌也飛躍到廣闊的深度和高度。我還會記起彼時的明月和熾熱的雪夜嗎?
突然記起讀過史鐵生先生的一篇長散文《命若琴弦》,老瞎子對小瞎子說,要彈斷1000根琴弦才能看見世界,其實這不過是給他活下去走下去的美好憧憬,一個永遠也夠不著的夢幻。我也做了類似的一個夢,時光告訴我的答案是,書送給一個其實不需要送的人。我以此為理由消磨十幾年的光陰,天天寫日記,鐵棒磨針水滴石穿,只不過是一個美夢的支撐罷了。

昨夜的雪很寂靜,窗簾外恍然的一片白,讓人以為是月光。早上推窗的欣喜涵蓋在一聲不由自主的驚嘆中。很多年沒有認真地對待一場雪了,特地順村中水泥小路踏雪而行,幾乎沒人早起,雞犬也畏寒似地噤了聲。三米寬的小路留下我處女的腳印,一首多年前歌唱雪花的校園歌曲在耳邊響起,那是我的心在說話,在哼唱。那些年是我的心游走茂盛的季節,不著邊際的事常常冒出來,和我的理性進行固執地對抗。我那些規格不同紙張不一的舊日記本,記下了我的臆想和囈語,此時翻開,不過是翻開一個已成結局的答案,沒有懸案也當然沒有吸引力。感謝昨天的他為我充當跋涉的理由。那么明天呢?因為未知總還是有一點新奇。路邊的地里矗立著行行蘋果樹,沒有掉下來卻干枯的樹葉承載了雪的負重,這是雪布置的風景,開出的匠心獨運。雪覆蓋了我的腳印,也覆蓋我曾經的浪漫和晶瑩。可是,對于明天,雪花,還是賜我繼續做美夢的動力吧。
人生其實是無字的結局,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彈響每一根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