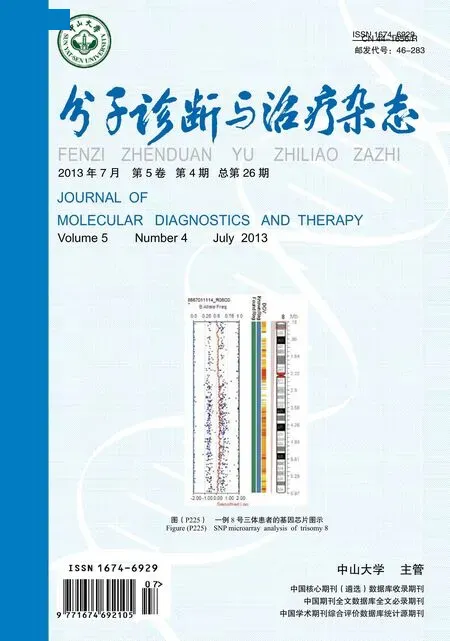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分子遺傳學及其在臨床診斷與防治方面的意義
吳曉昀張杰郭奕斌★
?綜 述?
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分子遺傳學及其在臨床診斷與防治方面的意義
吳曉昀1張杰2郭奕斌1★
MAN2B1基因突變導致α-甘露糖苷酶缺乏或活性降低是引起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根本內因。對MAN2B1基因、LAMAN酶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基因型與表現型的相關性研究以及診防治方面的研究近年來都取得了諸多新進展。本文重點圍繞這幾方面作一綜述。
α-甘露糖苷貯積癥;MAN2B1基因;α-甘露糖苷酶;溶酶體α-D-甘露糖苷酶;分子遺傳學
α-甘露糖苷貯積癥(Alpha-Mannosidosis,OMIM 248500)又名溶酶體α-D-甘露糖苷酶(Lysosomal α-mannosidase,LAMAN,EC 3.2.1.24)缺乏癥(lysosomal α-D-mannosidase de fi ciency)或α-甘露糖苷酶B缺乏癥(α-mannosidase B de fi ciency),是由于MAN2B1基因發生突變導致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MAN2B1(alpha-mannosidase,MAN2B1,EC 3.2.1.24)缺乏或活性降低而引起的一種罕見溶酶體貯積癥[1]。本病呈世界性分布,不同種族、不同地區都有病例報道,但發病率很低,挪威報道為1/750 000,澳大利亞報道為1/500 000[1,2],國內僅有零星報道,至今仍無統計數字。該病是一種以免疫缺陷,面部骨骼畸形,聽力障礙和精神發育遲滯、智力低下為特征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3]。根據臨床癥狀輕重的不同,本病早期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肝臟腫大伴隨嚴重感染后較早死亡的重型(一型),另一種是聽力喪失,精神發育遲滯可存活到成年的輕型(二型)[4]。目前,比較新的觀點認為,該病應分為三種臨床類型,即:I型:輕型,無骨骼異常,病情進展非常緩慢,通常在10歲后才被識別;II型:中間型,在10歲左右可看出骨骼異常并緩慢惡化,在20~30歲慢慢發展為進行性的共濟失調;III型:重型,出生不久即可看出骨骼異常,病情進展迅速,通常早夭于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紊亂或神經性肌病。臨床上常見的,大多屬于II型[3,5]。為了更好地理解本病診防治的研究進展,有必要先了解一下MAN2B1基因與LAMAN酶的結構和生化代謝途徑。
1 MAN2B1基因和LAMAN酶
人溶酶體MAN2B1基因(OMIM 609458),也稱為laman基因或MANB基因[6],定位于19號染色體(19 p13.2~p13.11)上,橫跨21.5 kb基因組DNA(gDNA),含有24個外顯子,cDNA含有1個2 964 bp的閱讀框。轉錄起始位點(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sites)主要有3個,分別位于起始密碼子ATG上游的-309 bp,-196 bp以及-191 bp位。在轉錄起始位點上游的134 bp序列中,沒有特征性的CAAT或TATA序列,但是其5'端區域含有多個富含GC、可與轉錄因子SP-1,AP-2,ETF結合的位點[6]。將缺失5'端區域的MAN2B1基因導入細菌CAT基因中,發現150 bp的5'端序列可以促使MANB基因在COS-7細胞的表達。Gotoda等[6~7]分析人MANB基因mRNA的5'端區域,發現其轉錄部位是位于距離起始密碼子“ATG”-28 bp和-20 bp的位置。已測出的MAN2B1基因序列目前已超過2000種,主要存在于人、牛、鼠、禽類等生物的溶酶體、內質網、高爾基體、胞漿和其他細胞器中[8~10]。該基因的轉錄初始產物約為3.5 kb,編碼一個由988個或1011個氨基酸組成的前體。編碼988個或1011個氨基酸的多肽鏈,取決于翻譯起始位點所在的位置[6,11]。在經過轉染的細胞中,α-甘露糖苷酶是由120 kDa的前體修飾形成,其中一部分經過分選后分泌到胞外發揮作用,另外一部分進入溶酶體后加工修飾成多肽“abc”,“d”和“e”[12~13]。三個多肽大小分別為70 kDa,42 kDa和15 kDa。編碼988個氨基酸的多肽,前26個氨基酸為潛在的前導序列,成熟多肽的分子量約為111 kDa,具有11個潛在的N-交聯糖基化部位。用逆轉錄病毒介導法導入患者細胞后,該cDNA可表達高活性的α-甘露糖苷酶。此cDNA與已發表的人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cDNA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在第2 315位堿基處發生了T>C轉換,可能與控制酶活性有關[14]。通過Northern印跡雜交可知,MAN2B1基因的表達水平在肺、腎臟、胰臟和外周血白細胞中是最高的。而在中樞神經系統(CNS)中,似乎是在胼胝體和脊髓中最高,而在小腦、大腦皮層、額葉和顳葉中表達水平則較低[14]。這種差異的意義目前還不清楚。
由MAN2B1基因(或laman基因)編碼的α-甘露糖苷酶(alpha-mannosidase,MAN2B1或LAMAN)多具有糖苷水解酶38、47家族保守序列。若以酶發揮最佳活性的pH條件分,α-甘露糖苷酶可分為酸性、弱酸性和中性三類;若以所在亞細胞器分,則主要分為細胞質的、高爾基體的、溶酶體的、內質網的、細胞膜的五類。但目前多以基因保守序列進行分類,根據該基因保守序列的不同可將此酶分為三類,即“I類”、“II類”和“未分類”[15]。II類α-甘露糖苷酶具有糖苷水解酶38家族保守序列[16],主要分布于溶酶體、內質網、高爾基體和胞質等,參與糖蛋白的合成和降解[17~19],此類α-甘露糖苷酶包括MAN2B1、MAN2B2兩種。其中,MAN2B1(也稱LAMAN)是人溶酶體酸性α-甘露糖苷酶中最常見的。此酶的異常除了引起α-甘露糖苷貯積癥外,還會引起先天性紅細胞生成異常性貧血II型等[20]。
2 生化代謝途徑
α-甘露糖苷酶主要參與蛋白質糖基化的修飾和糖蛋白聚糖水解的修飾。糖基化和糖蛋白聚糖水解與新生糖蛋白的折疊、成熟、運輸、構象維持、半衰期和生物活性關系密切,可對細胞的黏附作用、炎癥反應、激素活性、關節炎、免疫監視和癌細胞轉移等發揮作用[21]。當MAN2B1出現異常時,低聚糖代謝出現功能紊亂,糖蛋白水解無法進行,導致低聚糖蓄積于溶酶體中,病理組織學變化主要表現為細胞出現廣泛空泡變性,臨床表現為神經、骨骼發育不全,面部粗糙、聽力障礙、反復感染、肝脾腫大等癥狀。若患先天性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功能障礙,就會引起嬰兒踝骨畸形、發育遲緩、運動失調、智力障礙,甚至死亡。本病一般無法治愈[5]。MAN2B1是糖蛋白降解途徑的主要外切糖苷酶,參與寡聚糖N端的降解,可以切開高甘露糖和混合型低聚糖中的α(1→2),α(1→3)和α(1→6)糖苷鍵。對患者尿液糖蛋白降解成分的分析結果顯示,主要的溶酶體貯積物是低聚糖Man(α1→3)Man(β1→4)GlcNac,Man(α1→2)Man(α1→3)Man(β1→4)GlcNac和Man(α1→ 2)Man(α1→2)Man(α1→3)Man(β1→4)GlcNac[5]。另外一些含量較少的尿低聚糖在還原端還有N-乙酰葡糖胺。在人體正常代謝過程中,糖蛋白在溶酶體中會被蛋白酶和糖苷酶逐步消化、分解成小分子成份,然后分泌、運送到胞質中以被重新利用。MAN2B1缺乏會導致各器官、系統中未消化的物質如寡聚糖特別是富含甘露糖的寡糖貯積在細胞的溶酶體中,引起溶酶體膨脹,繼而造成細胞嚴重的功能損害,使機體發生廣泛的病理變化。然而,溶酶體貯積癥的病理生理學機制十分復雜,存儲物質的累積并不能完全解釋疾病的發生。
3 診斷研究進展
對本病的診斷,早期主要通過外周血檢查和尿液中的低聚糖測定做出診斷。前者主要是通過光學顯微鏡和透射電子顯微鏡(TEM)來觀察重型患者骨髓涂片和外周血淋巴細胞中是否有空泡,從而做出診斷[22]。后者是通過檢測尿中富含甘露糖的低聚糖分泌是否增多,可以由薄層色譜法和高效液相色譜法證實,但此法僅可作為輔助診斷[1]。近年來主要是通過酶活性測定和基因突變檢測的分子診斷方法進行快速確診。
3.1 酸性α-甘露糖苷酶活性測定
α-甘露糖苷貯積癥最有效、最可靠的診斷方法之一是測定酸性α-甘露糖苷酶(LAMAN)在白細胞、纖維母細胞或其他有核細胞中的活性。這種熒光測定是以4-甲基傘形酮基-α-D-吡喃甘露糖苷為底物,在低pH值(通常在pH4)環境中進行。在患者外周血白細胞中LAMAN活性是正常的5%~15%。殘留酶活性可能為來自其他細胞器如高爾基體或胞質的甘露糖苷酶活性。由抗LAMAN多克隆抗體的免疫沉淀反應可知患者LAMAN的活性范圍是從正常的0.1%到1.3%[23]。采集胎兒的絨毛細胞或羊水細胞,檢測胚胎細胞中的α-甘露糖苷酶活性,可以產前診斷患病胎兒。攜帶者的LAMAN酶活性可能同正常對照組有重疊,因此對攜帶者的檢測不可靠,需要采用下述的基因檢測。
3.2 基因檢測
基因突變檢測目前都是采用基于PCR的各種檢測方法。最常用的是,擴增MAN2B1基因的24個外顯子,然后對擴增產物進行直接測序,對所發現的新突變再進行功能學鑒定,這樣即可檢測DNA的致病突變[24]。父母的攜帶者分析必須在懷孕之前進行,方可用于后續的產前基因診斷。目前,對MAN2B1基因進行突變分析,已經成為確診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又一種最有效的方法。我室近年來在診斷一家α-甘露糖苷貯積癥時就是采用了這一方法并成功鑒定了兩種致病性突變。
3.2.1 基因突變類型
如上所述,α-甘露糖苷貯積癥是由編碼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的MAN2B1基因發生突變所致。2011年12月,挪威學者里瑟·斯特蘭德報道了其在北歐30個國家的130例甘露糖苷貯積癥病人中發現的83種新突變并且做了鑒定及病理分析,確定了其中80種突變為該病的致病性突變[3]。截至本文投稿之日(2013年1月14日)為止,HGMD突變數據庫收錄的和文獻報道的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致病突變類型已達126種(見表1),包括70種錯義/無義突變,18種拼接位點突變,18種小缺失、16種小插入,4種大片段丟失(http://www.hgmd.cf.ac.uk/ac/all.php)。在所查患者中,除少數幾個日本裔患者和阿拉伯裔患者外,其他均為歐洲裔[6,7,11,25~28]。且大多為II型,I型只占少數,III型更為罕見。

表1 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致病突變類型Table 1 Pathogenic mutation types of alpha-mannosidosis
在已報道的致病性突變中,大多數都是獨立存在的,即多數突變只發生在不同患者身上或少數幾個家庭中[我室近年來在對本病的基因診斷過程中,也查到了一些罕見的突變類型,其中有國外已報道的,也有新發現的突變(待發表),也證實了這一點]。但其中有一個錯義突變[c.2248C>T,導致“精氨酸”(R)替換成“色氨酸”(W),即發生p.R750W錯義突變]出現頻率甚高,此突變曾于來自50多個不同國家的118例病人中出現,在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13個病人身上也都有發現。經過研究統計,此位點發生的頻率大約為27.5%[1],占所有來自歐洲患者所檢測到的突變類型的30%以上,這一位點很可能為突變熱點。基于此位點在人群中具有較高的突變頻率,先后有多國學者對存在此突變位點的病人進行了單體型分析。北挪威的學者里瑟·斯坦斯蘭德對來自于16個國家的50例在此位點存在錯義突變的病人做了同源性分析。選擇5個單核苷酸多態性(SNP)位點作為標簽進行單體型分析,結果顯示:芬蘭、波蘭和意大利純合子患者都具有同一種單體型[3]。這些結果顯示:p.R750W等位基因的高頻率和廣泛地理分布可能與始祖效應和復發突變事件有關。
3.2.2 突變檢測技術
早期主要采用先經SSCP篩檢,然后對可疑標本再用測序進行驗證。隨著測序成本的降低,現多采用PCR擴增后直接測序技術,既快速又實惠。但對發現的新突變,就需采用一系列方法對突變的致病性進行鑒定。這些方法涉及DNA,RNA和蛋白/酶水平的結構和功能的鑒定。就DNA水平來說,為了排除SNP多態性變異的可能,通常需要對100例以上的正常對照組進行篩檢,由于樣品量較大,此時可用ARMS法、RE法、DHPLC法等進行快速鑒別鑒定。就RNA水平來說,可采用RT-PCR、cDNA測序法、q-PCR定量鑒定法;而在蛋白/酶水平,可通過Western blotting法、細胞培養、分子克隆和酶活性鑒定等方法。
4 預防研究進展
由于本病屬于先天性、遺傳性代謝病且至今仍無有效的根治療法,因此,對本病的最佳應對策略主要重在預防,在孕前、產前、癥狀出現前做好各種防患措施,包括:產前診斷、選擇性流產、攜帶者檢出、遺傳優生咨詢、再發風險估計、癥狀前檢查等。其中,產前診斷結合選擇性流產是目前最為重要和有效的預防手段。
產前診斷的目的主要是預防患胎出生。由于此病胎兒在孕期沒有形態結構的改變,產前超聲檢查無法作出診斷,因此主要是通過產前酶學診斷或/和產前基因診斷。
根據常染色體隱性遺傳規律,攜帶者父母所生的后代每一胎都有25%的患病風險,另有50%為無癥狀的攜帶者。產前診斷可在妊娠期10~13周取絨毛,或在15周后抽羊水,分析胎兒細胞中酸性α-甘露糖苷酶的活性或直接進行產前基因診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攜帶者與正常人的酶活性測量值存在交叉,難于鑒別、確診,故最好是通過突變分析(基因型檢測)。一旦查出患胎,在知情同意的基礎上盡早終止妊娠。父母的基因型分析嚴格來講,都必須在懷孕前進行,除非有意外受孕的特殊情況出現,才可考慮在孕期突擊檢測,但必須告知各種可能的結果并征得孕婦的知情同意。
5 治療研究進展
對本病的治療,早期主要采用對癥治療,但該法只能治標無法治本。隨著醫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新的療法已逐步應運而生并逐漸從實驗室走向臨床。目前正在研究和應用的治療方式有三種: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酶替代療法(ERT)和基因治療(GT)。其中,HSCT是目前最為可行且有望普及的一種治療手段,其早期階段主要是通過骨髓移植。
5.1 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
對本病患者進行治療的研究始于1987年。1987年威爾等[29]對一名患者進行了HSCT。然而,成功移植18個星期后竟死于其他并發癥。驗尸結果顯示:移植雖然減少軀體細胞α-甘露糖苷的貯積,但并不能減少腦組織溶酶體內α-甘露糖苷的貯積,因此認為HSCT可能不是一個合適的治療方法。然而,大腦的零效應可能與來自母親(攜帶者)的供體細胞只有50%的活性有關,還與血腦屏障影響HSCT對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有關。1994年史蒂文[30]報道,早期進行HSCT可以阻止一只動物模型貓的神經退化。這可能與HSCT將供體的衍生細胞遷移到患貓的中樞神經系統有關。1998年沃爾等[31]報道了一個HSCT病例,聲稱在治療的2年內解決了復發性傳染病和器官巨大癥以及改善了骨病和神經認知功能。1999年Frostad等[26]報道,一例MANB基因型異常患者在接受正常捐獻者的骨髓后存活,并且于一年后檢測到該患者的白血球與捐獻者完全一致,表明骨髓移植獲得了成功,也表明骨髓移植可用于本病的治療。
隨后科研人員又進行了多例HSCT(未發表)。2004年Grewal等[32]報道了四名3歲~23歲患者的結果,聲稱有三人的智力水平穩定,適應能力和口頭記憶功能有所提高。尤其是聽力可提高至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語音頻率)。2012年又報道了17名1.1歲到23歲的患者的治療情況,其中有兩人移植后5個月內死亡,剩余的15人中,平均隨訪5.5年,其中有2人發展成嚴重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癥(≥ II級),6人發展為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癥,3人需要再移植。移植治療后,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發育進展且大部分患者的聽力都有改善[33]。
有報告表明,移植成功后,軀體特征的矯正通常伴有神經癥狀不再加重。因此,HSCT帶來的益處,必須權衡整個治療過程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風險。并發癥出現前,HSCT對年幼患者更有益,而年長患者移植手術的相關并發癥則更頻繁和嚴重。因此提倡盡可能早期移植,以減少神經損傷并得到最大化效果。2007年Crawley和Walkley從動物模型得出的數據也支持這一觀點[34]。這使得患者早發現、早診治成為成功的關鍵。
另外有研究表明,質子核磁共振光譜(MRS)可以檢測出與患者腦中糖類分子一致的波峰,是一個監測α-甘露糖苷貯積癥治療效果的有用方法[35]。
5.2 酶替代療法(ERT)
酶替代療法(ERT)是溶酶體貯積癥如高雪氏癥、粘多糖病、龐貝病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治療方式。α-甘露糖苷貯積癥患者都有MAN2B1基因的缺陷和α-甘露糖苷酶活性的異常。早期的觀察表明,產生α-甘露糖苷酶的細胞能夠將酶轉移到貯積甘露糖苷的細胞中,從而達到治療的目的。對于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ERT來說,最早是在1976年,Jolly等首先在動物實驗中嘗試酶替代療法,他們利用純化的牛α-甘露糖苷酶來治療患病牛,但此實驗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2004年Roces等,2006年Crawley等,在一個人工基因敲除純合子小鼠模型和一個自然發生突變的豚鼠模型中完成ERT實驗[36~38]。這兩個模型中幾乎所有組織的貯積物都得到明顯減少。然而,第一個研究模型發現在大腦中含甘露糖的低聚糖的減少量比患甘露糖苷貯積癥的對照小鼠少30%[36],在豚鼠身上也沒有發現腦功能的改善[37~38]。2007年Sedel等,2009年Matzner等,2011年Damme等,2012年Borgwardt等報道,將α-甘露糖苷酶早期植入到患者體內,結果顯示此種酶替代療法對患者的病情有緩慢而持續的效果[39~43]。
5.3 基因治療(GT)
對于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基因治療研究近年來也日益引起重視并有相關報道。目前已建立有編碼α-甘露糖苷酶MANB基因缺失的動物模型,包括鼠,貓科動物及荷蘭豬等模型[44]。1999年中國學者報道對α-甘露糖苷貯積癥患者的基因治療進行了初步研究。他們將編碼人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的cDNA導入病貓皮膚的成纖維細胞。結果顯示:人源cDNA在病貓細胞內表達出高活性的α-甘露糖苷酶,重組酶的pH活性范圍與正常酶相同。2011年有學者成功將人α-甘露糖苷酶基因轉入煙草植物細胞中并獲得大量表達,純化后顯示該蛋白與人體中α-甘露糖苷酶有相似的生物學活性[45],該蛋白有望應用于本病病人的治療。此外,科學家們還在深入探索基因治療的可能性。目前,研究人員正致力于該酶基因的分子克隆,已有文獻報道,其cDNA序列的克隆已獲初步成功,這將為此病患者帶來福音。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基因治療的難關一定會被攻克!
6 展望
近年來關于通過調節LAMAN酶實現腫瘤治療也有文獻報道,這為人類戰勝腫瘤提供新的研究方向。LAMAN活性受苦馬豆素(swainsonine,SW)抑制,但抑制程度不同,其部分受dMNJ抑制。隨著苦馬豆素對LAMAN抑制作用機制的揭示,研究人員已成功利用苦馬豆素誘導建立了牛和小鼠α-甘露糖苷貯積癥模型,從而為進一步探索α-甘露糖苷貯積癥的機制和治療方法提供了新的途徑。
[1] Nilssenφ, Stensland H M, Malm D. Clinical utility gene card for: α-mannosidosis[J]. Eur J Hum Genet, 2011, 19(7).
[2] Meikle P J, Ranieri E, Simonsen H, et al. Newborn screening for 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s: clinical evaluation of a twotier strategy[J]. Pediatrics, 2004, 114(4): 909-916.
[3] Riise Stensland H M, Klenow H B, Van Nguyen 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83 novel alpha-mannosidosis-associated sequence variants: functional analysis of MAN2B1 missense mutations[J]. Hum Mutat, 2012, 33(3): 511-520.
[4] Gutschalk A, Harting I, Cantz M, et al. Adult alphamannosidosis: clinical progr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demyelination[J]. Neurology, 2004, 63(9): 1744-1746.
[5] Malm D, Nilssenφ. Alpha-mannosidosis[J]. Orphanet J Rare Dis, 2008, 3: 21.
[6] Riise H M, Berg T, Nilssen ?, et al. Genomic structure of the human lysosomal alpha-mannosidase gene(MANB)[J]. Genomics, 1997, 42(2): 200-207.
[7] Gotoda Y, Wakamatsu N, Kawai H, et al. Missense andnonsense mutations in the lysosomal alpha-mannosidase gene (MANB) in severe and mild forms of alpha-mannosidosis[J]. Am J Hum Genet, 1998, 63(4): 1015-1024.
[8] Shashidhara K S, Gaikwad S M. Class II alpha-mannosidase from Aspergillus fischeri: energetics of catalysis and inhibition[J]. Int J Biol Macromol, 2009, 44(1): 112-115.
[9] Dohi K, Isoyama-Tanaka J, Misaki R, et al. Jack bean α-mannosidase digestion pro fi le of hybrid-type N-glycans: effect of reaction pH on substrate preference[J]. Biochimie, 2011, 93(4): 766-771.
[10] Intra J, De Caro D, Perotti M E, et al. Glycosidases in the plasma membrane of Ceratitis capitata spermatozoa[J]. Insect Biochem Mol Biol, 2011, 41(2): 90-100.
[11] Pittis M G, Montalvo A L, Heikinheimo P, et al. Fun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four novel MAN2B1 mutations causing juvenile onset alpha-mannosidosis[J]. Clin Chim Acta, 2007, 375(1-2): 136-139.
[12] Berg T, King B, Meikle P J, et al.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lysosomal alphamannosidase[J]. Mol Genet Metab, 2001, 73(1): 18-29.
[13] Hansen G, Berg T, Riise Stensland H M, et al.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of human lysosomal alpha-mannosidase and alphamannosidosis-related mutants[J]. Biochem J, 2004, 381(Pt 2): 537-546.
[14] 孫懷昌. 人溶酶體α-甘露糖苷酶cDNA的克隆與表達[J].中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報, 1999, 15(5): 692-698.
[15] 劉紅霞, 蘇衛, 張連峰. α-甘露糖苷酶研究進展[J]. 中國比較醫學雜志, 2006, 16(11): 697-720.
[16] Cobucci-Ponzano B, Conte F, Strazzulli A, et al.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GH38 alphamannosidase from the crenarchaeon Sulfolobus solfataricus revealed its ability in de-mannosylating glycoporteins[J]. Biochimie, 2010, 92(12): 1895-1907.
[17] Hossain M A, Nakano R, Nakamura K, et al.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plant acidic alpha-mannosidase, amember of glycosylhydrolase family 38, involved in the turnover of N-glycans during tomato fruit ripening[J]. J Biochem, 2010, 148(5): 603-616.
[18] Shashidhara K S, Gaikwad S M. Conformational and functional transitions in class II alpha-mannosidase from Aspergillus fi scheri[J]. J Fluoresc, 2010, 20(4): 827-836.
[19] Uno Y, Hashidume S, Kurita O, et al. Dioscorea oppositaThunb. alpha-mannosidase belongs to the glycosyl hydrolase family 38[J]. Acta Physiol Plant, 2010, 32(4): 713-718.
[20] 王姍姍, 徐向軍, 路浩, 等. α-甘露糖苷酶研究進展[J]. 動物醫學進展, 2012, 33(1): 92-97.
[21] Moremen K W. Golgi alpha-mannosidase II efficiency in vertebrate 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asparagines-linked oligosaccharide processing in mammals[J]. Biochem Biophys Acta, 2002, 1573(3): 225-235.
[22] Sun H, Wolfe J H. Recent progress in lysosomal alphamannosidase and its deficiency[J]. Exp Mol Med, 2001, 33(1): 1-7.
[23] Berg T, Riise H M, Hensen G M, et al. Spectrum of mutations in alpha-manosidosis[J]. Am J Hum Genet, 1999, 64(1): 77-88.
[24] Kuokkanen E, Riise Stensland H M, Smith W,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alphamannosidosis mutations[J]. Hum Mol Genet, 2011, 20(13): 2651-2661.
[25] Lyons M J, Wood T, Espinoza L, et al. Early onset alphamannosidosis with slow progression in three Hispanic males[J]. Dev Med Child Neurol, 2007, 49(11):854-857.
[26] Frostad Riise H M, Hansen G M, Tollersrud O K,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alpha-mannosidosis-causing mutation and its use in leukocyte genotyping afte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J]. Hum Genet, 1999, 104(1): 106-107.
[27] Beccari T, Bibi L, Ricci R, et al. Two novel mutations in the gene for human alpha-mannosidase that cause alphamannosidosis[J]. J Inherit Metab Dis, 2003, 26(8): 819-820.
[28] Sbaragli M, Bibi L, Pittis M G,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i ve novel MAN2B1 mutations in Italian patients with alpha-mannosidosis[J]. Hum Mutat, 2005, 25(3): 320.
[29] Will A, Cooper A, Hatton C, et 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lpha-mannosidosis[J]. Arch Dis Child, 1987, 62: 1044-1049.
[30] Walkley S U, Thrall M A, Dobrenis K, et 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corrects the enzyme defect in neuron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a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4, 91(8): 2970-2974.
[31] Wall DA, Grange D K, Goulding P, et 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lpha-mannosidosis[J]. J Pediatr, 1998, 133(2): 282-285.
[32] Grewal S S, Shapiro E G, Krivit W, et al. Effective treatment of alpha-mannosidosis by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J Pediatr, 2004, 144(5): 569-573.
[33] Mynarek M, Tolar J, Albert M H, et al.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CT for alpha-mannosidosis: an analysis of 17 patients[J].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12, 47(3): 352-359.
[34] Crawley A C, Walkley S U.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CNS pathology in the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 alphamannosidosis[J]. J Neuropathol Exp Neurol, 2007, 66(8): 687-697.
[35] Avenarius D F, Svendsen J S, Malm D. Prot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detection of oligomannosidic n glycansin alpha-mannosidosis: a method of monitoring treatment[J]. J Inherit Metab Dis, 2011, 34(5): 1023-1027.
[36] Roces D P, Lüllmann-Rauch R, Peng J, et al. Efficacy of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alpha-mannosidosismice: a preclinical animal study[J]. Hum Mol Genet, 2004, 13(18): 1979-1988.
[37] Crawley A C, King B, Berg T, et al.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alpha-mannosidosis guinea-pigs[J]. Mol Genet Metab, 2006, 89(1-2): 48-57.
[38] Blanz J, Stroobants S, Lüllmann-Rauch R, et al. Reversal of peripheral and central neural storage and ataxia after recombinant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alphamannosidosis mice[J]. Hum Mol Genet, 2008, 17(22): 3437-3445.
[39] Sedel F, Turpin J C, Baumann N. Neurological presentations of lysosomal diseases in adult patients[J]. Rev Neurol(Paris), 2007, 163(10): 919-929.
[40] Matzner U, Lüllmann-Rauch R, Stroobants S, et al. Enzyme replacement improves ataxic gait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histopathology in a mouse model of 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J]. Mol Ther, 2009, 17(4): 600-606.
[41] Damme M, Stroobants S, Walkley S U, et al. Cerebellar alterations and gait defects as therapeutic outcome measures for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α-mannosidosis[J]. J Neuropathol Exp Neurol, 2011, 70(1): 83-94.
[42] Borgwardt L, Dali C I, Fogh J, et al.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lpha-mannosidosis[J]. Mol Genet Metab, 2012, 105(2): S21 .
[43] Borgwardt L, Dali C I, Fogh J, et al.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lphamannosidosis[J]. J Inherit Metab Dis, 2012, 35(1): S10.
[44] Crawley A C, Jones M Z, Bonning L E, et al. Alpha-mannosidosis in the guinea pig: A new animal model for 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s[J]. Pediatr Res, 1999, 46(5): 501-509.
[45] De Marchis F, Balducci C, Pompa A, et al. Human α-mannosidase produced i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is processed in human α-mannosidosis cell lines[J]. Plant Biotechnol J, 2011, 9(9): 1061-1073.
Molecular genetics diagnosis of alpha-mannosido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WU Xiaoyun1, ZHANG Jie2, GUO Yibin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 Sun Yat-sen Medical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80, China; 2.Clinical Medicine (Eight Year Program), Grade 2009, Zhongshan School of Medicin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80, China)
The basic cause of alpha-mannosidosis is the de fi ciency of alpha-mannosidase resulting from theMAN2B1gene mutation. In resent years, there are plenty of research progress with 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MAN2B1gene and LAMAN enzy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otype and phenotype,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se aspects to make a summary.
Alpha-mannosidosis;MAN2B1gene; Alpha-mannosidase(MAN2B1); Lysosomal alpha-D-mannosidase(LAMAN); Molecular genetics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o.30772069);閩粵橫向課題基金(No.7101025)
1.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醫學遺傳學教研室,廣東,廣州 510080
2.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臨床專業2009級八年制直博生,廣東,廣州 510080吳曉昀和張杰為并列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郭奕斌,E-mail: guoyibin@mail.sysu.edu.cn和zpgyp@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