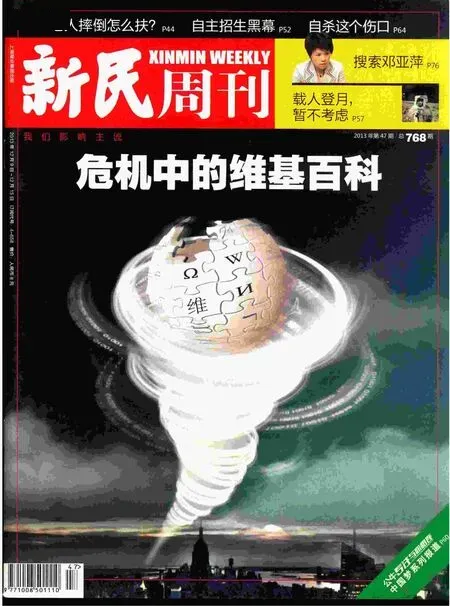日常的“現代感”
顧丞峰

在當下,“現代”已經不是一個時髦的字眼,而且其前衛意義似乎也大打折扣;人們現在口中談論更多的已經是“當代”。細心體會一下,“現代”似乎意味著一種態度;而“當代”則更多具有一種時尚的感覺。我更愿意從“現代”的意義上來解讀張友憲的“芭蕉”系列。
中國水墨繪畫需要走向現代嗎?這個問題在一百年前的康有為、陳獨秀那里就有過斬釘截鐵的答案;徐悲鴻則是一個親身實踐者,他不僅以自己的水墨人物、動物繪畫實踐對中國畫敞開了一條后人多行效仿的道路,而且在美術教育上身體力行,改變了幾代人的水墨繪畫認知的視覺和技法。
中國的“現代性”正是涂上了濃重的自身色彩,中國美術的“現代性”之路至少有三分之一強的內容是通過水墨繪畫的變革體現出來的。
總結中國水墨繪畫走向現代的幾種路徑,大致上有徐悲鴻式、林風眠式和劉國松式。其實,當代社會還存在著大量為數眾多的不屬于上述幾種類型的中國畫家,他們注重筆墨,多采用傳統中國畫題材作畫,他們同樣有西式教育的背景,他們的繪畫實踐(這里我稱之為“實踐”,是因為“實踐”具有非固定和隨機性以及階段性特點)中,有時也會體現出受到現代觀念的影響。只是這種“現代”更為日常化,更為和緩,更注重內心表達。
張友憲“芭蕉”系列正是這一群體的“日常”顯現。12月2日,張友憲的個展《蕉·慮》在南京先鋒藝術中心開幕,可以讓我們再次感受他內心的從容與包括他在內的現代人的焦慮。
作為一種“日常”,張友憲的西式教育背景是清晰的,大學時代他的出色素描、白描功底至今還令許多人印象頗深,但他并沒有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切入,而是沉浸在筆墨的表達上,用一句話就是喜歡“那刀刻一般的力量”。
另一種“日常化”是他的才能的多樣。山水、人物、花卉無不精到,據說在美術院校教中國畫的教師中,能夠同時教此三科的人極少,同時,焦墨、淡墨、彩墨山水人物,行、隸、篆、草,亦無不精。張友憲正是這樣一個全才。當然,“全才”也有另一面,就是可能主特長反不易彰顯。他的南藝周邊同儕們,一個個正因特長和圖式的昭著,早已在國內80年代后期興起的“新文人畫”潮流中蜚聲揚名,而全才的他卻似藏在“蕉叢”中,深隱不露。
然厚積終有薄發甚至噴發時,張友憲此次向人們展示的鋪天蓋地的芭蕉,還是讓人們感受到一種打動人心的震撼。
這些芭蕉枝葉,一反傳統芭蕉的藝術造型在人們頭腦中的“扶疏似樹,質則非木,高舒垂蔭”的印象,要么枝垂凋零、殘葉敗枝,要么野、亂、擠地簇擁一團,或者濃密黑蔭,宛如一團心緒不寧的亂絮。張友憲在一幅蕉葉畫上題畫詩中言:“蕉魂挾風霜,玉管訴衷腸。莫道頭被折,來年又上揚。嫩紅是芽端,汁綠葉葉長。與君情義篤,日日新模樣。”從詩中表達的情感看,與古人徐文長的“墨葡萄圖”題詩的心境并無本質區別,都是文人不平則鳴的產物。
現代感的構成,從內容上說是關注現代生活,作為知識分子的藝術家用藝術表達出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思考;在形式上融入現代構成因素,或打破技術的陳規乃至采用破壞、顛覆性的技術材料語言組成畫面,形成視覺沖擊。 這種現代感當然是溫和的,其實也不是畫家的有意追求,就像許多其他中國畫家一樣,只是日常實踐了一種潛移默化的“現代”經歷。這種經歷對一些人來說可能促使他們義無反顧地投向“現代”乃至“當代”的表達當中;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也可能僅僅是一種對其教育和環境的自然彈射,彈射之后,仍可能會堅守在他們所熟稔的傳統表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