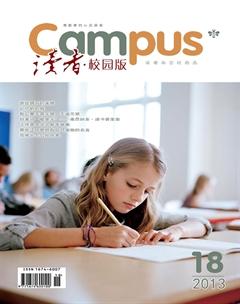那年那月
麥家
1964年1月5日
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里的,村莊的名字叫蔣家門口。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灘建筑的3層樓房,寬敞的回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臺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嘆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仿造這棟來自上海灘的3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忘返。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里,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么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么說是有深刻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那也是一棟3層樓,但似乎沒有那么考究,沒有那么多純粹出于審美需要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3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墻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么高,這么擺放(屁股對著我家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奇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后,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建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于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范圍之內。于是在10年后的1982年,我們家又建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斗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后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象,父親為什么要這么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經久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寂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圣殿的門。
兩個重要時間
這里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日至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至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
我的少年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沉重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極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貌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5年,我當了3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么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那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兩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并把這種機會歸結為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后,父親在新屋里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里,并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只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復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涂,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只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從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后,我開始發憤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5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憤讀書,我雖然也發憤,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于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線高出不多,屬于險勝。盡管如此,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么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3天,后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