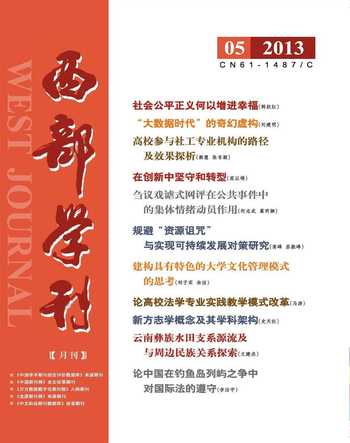檢視啟蒙:閏土之于魯迅的獨特意義
韓明港 高顏平
摘要:少年閏土是魯迅《故鄉》中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但是,如果認為魯迅只是借閏土來懷想曾經的少年歲月就將問題過于簡單化了。閏土,作為一個內心純白的少年,正符合魯迅對“立人”——或說“國民性改造”——前提的設定。魯迅試圖以《故鄉》對啟蒙之路進行檢視,少年閏土身上寄托了魯迅對喚起民眾的可能性的期待。閏土的變化,深深地動搖了魯迅對啟蒙的信心,因而,對故鄉的親近與逃離,構成了作品的基本敘事結構,吶喊與質疑的混響,希望與絕望的復調成為作品的獨特風貌。
關鍵詞:閏土;魯迅;啟蒙之夢;檢視
中圖分類號:I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故鄉》中,“我”冒著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似乎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為了搬家。但在敘述中,搬家顯然不是主要內容,大量的筆墨最終落在了閏土身上,而魯迅的希冀也伴隨著對閏土的懷想和與之相見而發生著變化。
閏土,不僅是魯迅尋找的舊友,也是魯迅尋找的啟蒙之夢。
一、魯迅的啟蒙之夢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道,“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1]P437這未被忘卻的夢,就是魯迅的啟蒙夢。
面對家國危難,魯迅和那個時代的青年一樣,在努力探求著救亡強國之路,而魯迅的設計是比較獨特的。
在南京求學時,年輕的魯迅已深受嚴復、梁啟超的影響,到日本后,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日漸成熟。1902年,魯迅東渡日本。據許壽裳回憶,魯迅在日本弘文學院時經常思考三個相關聯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P487后來魯迅明確提出“立人”的解決辦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在魯迅的設想中,中國的危機根本上是“人”的危機,而解決的方式是人的重建,首要的問題是“改變他們的精神”,也就是國民性改造,因此魯迅決定“首推文藝”,不是“黃金黑鐵”的實業興邦或“托言眾治”的制度變革。只要“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1]P57
啟蒙的關鍵是讓人皆獲此“自性”,“人各有己”,“群之大覺近矣”,“國民精神發揚”,“大其國于天下”。其方式是,首先由“先覺者”發為雄聲,振起國民。民眾聞此妙音“靈府朗然”,“發揚踔立”而后“邦國亦以興起”。顯然這是一條由“首在立人”而終在“立國”的啟蒙之路。
但是,并不是所有國民皆可以“立”。在魯迅看來,真正的人之“本心”,或被統治者“不攖人心”的“治心”政策湮滅了,或被“物欲”遮蔽了,不但失其本心,甚至參加了“吃人”的行列,故而難見“真人”。但是,有兩類人應該還保存著這份純白之心,一是“沒有吃過人的孩子”,一是“氣稟未失之農人”。[3]P30
少年閏土,應當是有如此“純白”之心的孩子,而成年的閏土,也應當是一位“氣稟未失之農人”。
二、與閏土相遇:啟蒙之基的動搖
魯迅是抱著對少年閏土的良好懷想來到故鄉的。他要尋找的是人內心的“純白”,而這種“純白之心”正是啟蒙得以展開的前提。少年閏土健壯、勇敢、樸素、單純,正符合魯迅所設定的啟蒙前提。在《故鄉》灰色的調子和灰色的人物之中,少年閏土無疑是最鮮亮的,月下戴著銀項圈的閏土是魯迅深刻的記憶。魯迅不惜用大量筆墨描寫少年閏土,這不只因為閏土是魯迅的鄉情的寄托,更是因為,閏土寄托著魯迅啟蒙的夢想。
但閏土的出現擊碎了魯迅的想象。
閏土到來了,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卻又不是“我”記憶中的閏土了。“我”回到了故鄉,悲哀地發現閏土已經由一個“小英雄”變成了一個“木偶人”。“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是原因,但最讓魯迅失望的莫過于閏土的沉默與順從,那一份健壯、勇敢、單純、樸素的“純白”之心已蕩然無存。
正如前述,在魯迅的想象中,由“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的“摩羅”詩人“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詩人”、“握撥一彈”,國民“心弦立應”,“靈府朗然”,而 “得是力,乃以發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極點”。以此“先覺之聲”,“破中國之蕭條”,終“國民精神發揚”,自覺至,內曜外華,“人各有己”,必“自覺勇猛發揚精進”,“知人類曼衍之大故,暨人生價值之所存……而張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懷大希以奮進,與時劫同其無窮。” [1]P45-120
但這里并沒有魯迅想象的“上征”之力,沒有“白心”與“內曜”。“木偶人”的閏土,是麻木的、衰弱的、讓人失望的。這并不是魯迅要找的,有些內在真誠、純白、樸素品格的閏土,這不是“氣稟未失”的閏土,而恰是氣稟皆失。當閏土叫出一聲“老爺”時,“我”便知道彼此之間的對話已經不可能了,“我也說不出話”,因為“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
“白心”、“內曜”是魯迅設定的啟蒙的前提,“握撥一彈”,“心弦立應”,“靈府朗然”,是魯迅想象的啟蒙的方式與效果。沒有“純白”之心和未失之“氣稟”,麻木閏土與“我”已無法交談,對話的必要與可能也就不存在了,啟蒙無以立基,方式效果,也無從談起。
“我”要離開故鄉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故鄉,確切地說,是故鄉的閏土,曾經不但牽扯著我的鄉情,也寄托著我的夢想。而現在,“……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忽地模糊”了的閏土形象,正是魯迅忽地模糊了的啟蒙之路,這種“悲哀”并非只是鄉情的潰散,而更是啟蒙想象的破碎。
故鄉,是魯迅試圖親近的地方,也是魯迅尋找啟蒙之基和建構希望與夢想的地方,夢想潰散時,故鄉自然“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而本有的希望也正在動搖之中,于是魯迅只好逃離。
“我”忽然害怕起來,“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魯迅的“希望”,是打破“鐵屋子”的希望,是啟蒙,而此時這個希望卻因閏土的出現似乎已經變得“茫遠”了。
三、閏土之于魯迅的獨特意義
魯迅的設計是一條由“立人”而“立國”的啟蒙之路。
人性善或可以向善是“人國”建立的必備條件,如果人性惡,那么“沙聚之邦”不可能“轉為人國”,正如儒家哲學中必須設定人有“四端”——仁、義、禮、智——作為性善的保證,也是道德理想國的保證,荀子設定“人性惡”,但必須可以“化性成偽”,也就是改惡遷善,才能夠保證他的國家邏輯的建立。
本善之人性和民眾的“心弦立應”直接決定著啟蒙的成敗。在《故鄉》中我之所以要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就是要尋找記憶中的“純白”之心,找到那種“內曜”和“上征之力”。可以說,閏土身上寄托了魯迅的啟蒙想象。
與閏土的現實相遇,動搖了魯迅的啟蒙設計。魯迅自己本十分確信的小英雄閏土能夠確證自己的啟蒙之路,而閏土的出現卻從根本上否定了魯迅的啟蒙想象,滿懷的希望與期待也就變成了惶惑與失落。
閏土,是魯迅設定的對啟蒙的一個驗證者,當然,他本希望讓閏土確證自己的啟蒙想象,然而閏土卻最終拆解了啟蒙,拆解了魯迅的夢想。
長期以來,對《故鄉》尤其是對閏土形象的解讀,并沒有從魯迅的啟蒙理想和啟蒙之路來解讀,所以并不能很好地領會到《故鄉》的豐富性和魯迅的復雜性。
四、“吶喊”與“質疑”:魯迅啟蒙小說的雙重意味
在日本時的魯迅就曾試辦《新生》,但是很快“逃走了資本”,離散了同志,不能“縱談將來的好夢了”。《新生》的失敗使魯迅明白,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
如果說《新生》的失敗,魯迅只是對自己的能力的懷疑的話,多年之后在北京的魯迅,則是對啟蒙之路充滿了疑慮。
曾經,魯迅“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對啟蒙非常地確信,但經過太多的人生變故和社會經歷之后,顯然魯迅變得更加深沉。
面對老朋友錢玄同的力邀,魯迅最終答應請求,但他給自己的定位,中介一個“吶喊”者。一方面,自己“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而另一方面自己對啟蒙并不像以前那么確信。“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雖然答應了錢玄同,但是魯迅并未放棄自己的懷疑,“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魯迅之所以答應寫文章,一方面是因為“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一方面也為著自己擺脫無聊與寂寞。但是,魯迅并未表現出對啟蒙之路的學理意義上的贊同。
“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1]P439魯迅的確信就是他的“懷疑”。
正因如此,《吶喊》與之后的《彷徨》,不只有魯迅呼喊的聲音,也有魯迅質疑的思索,魯迅試圖用小說來驗證啟蒙。
首先要驗證啟蒙的前提。《狂人日記》將啟蒙的希望寄托于“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在《故鄉》中則進一步在這個健壯的孩子身上尋求“白心”不泯、并且健康成長的可能,而閏土的出現,的確讓魯迅深深地失望了。在另一篇作品《孤獨者》中,魯迅似乎要進行再一次的驗證。“我”曾跟魏連殳討論過孩子的問題。魏連殳說:“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而“我”隨便地否定了,“那也不盡然。”魏連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孩子,他說“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而“我”提出了反對的理由:“不。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含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才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何嘗是無端……”三個月后,魏連殳似乎微露悲哀模樣,半仰著頭道:“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奇怪。我到你這里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4]P88“白心”、“內曜”渺不可聞,而“壞根苗”卻已昭然,魯迅的啟蒙失卻了內在的依據與前提。
其次,即便有“白心”、“內曜”作為基礎,啟蒙的成功還需要一個條件:啟蒙者與民眾之間的心靈共振。“……如反響之森林,受一呼聲,應以百響者也。”[1]P70但事實并非如魯迅設想。
“我”與閏土相見,“接著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涌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么擋著似的,單在腦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說不出話”,否認了啟蒙者與民眾之間對談的可能,“握撥一彈,心弦立應”,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的想象了。正如在《藥》中,革命者的血最終并未能喚起民眾的覺醒,而是被做了治病的饅頭。
閏土的出現,不但否定了啟蒙的前提,也質疑了啟蒙的方式。這種質疑和否定,也是魯迅自身對啟蒙的疑慮。它表明,隨著經歷的豐富,熱情漸冷的魯迅更加走向了深刻與成熟。
魯迅不少小說,如《藥》、《祝福》、《孤獨者》等,都如《故鄉》一樣,一面是魯迅試圖為慰藉不憚前行的猛士所發出的吶喊,同時又包含魯迅對啟蒙的質疑和更深層的思考。這種質疑與析解,又讓魯迅感受到一種希望潰散的痛楚,正因為如此,魯迅的小說往往是吶喊與質疑的混響,希望與絕望的復調。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許壽裳.魯迅回憶錄(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