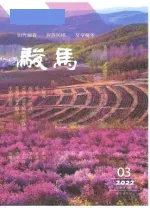紙上的根河
周聞道
四川省散文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眉山市文聯(lián)副主席、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漢語(yǔ)寫(xiě)作第一個(gè)自覺(jué)的散文流派——在場(chǎng)主義創(chuàng)始人和代表作家。先后獲得孫犁散文獎(jiǎng)、首屆(1979-2009)中國(guó)西部年散文獎(jiǎng)、四川文學(xué)獎(jiǎng)、新散文獎(jiǎng)等。
本來(lái)是要親臨的,走近大興安嶺北段西坡,走近那片蟄伏于鄂倫春、額爾古納、牙克石、漠河和塔河之間的神秘土地。一個(gè)突如其來(lái)的身體不適,竟改變了一切,莫名奇妙地。
我說(shuō)的是根河之旅,就在這個(gè)孟夏。
似乎恍若夢(mèng)幻。行李早打理好,除了簡(jiǎn)單的衣物,主要是心情;機(jī)票也已買(mǎi)定,那個(gè)叫CA4111和MU2891的接力航班,將搭載我的夢(mèng)與向往,從成都出發(fā),經(jīng)北京直達(dá)海拉爾,再驅(qū)車(chē)根河;甚至已經(jīng)換好登機(jī)牌,經(jīng)過(guò)安檢,登上飛機(jī)。旅程既然啟動(dòng),心情早已抵達(dá)。展開(kāi)的想象之翅,已超越時(shí)空,遨游于那片遙遠(yuǎn)的草原。內(nèi)容主人已經(jīng)安排好,一切只是依序而行。先要探訪探訪鄂溫克族使鹿部落,親吻親吻根河源濕地的水草,品嘗品嘗地道的好里堡山珍;再看一臺(tái)原汁原味的《敖魯古雅》;然后,在草天一色的呼倫貝爾草原撒撒野,摘幾朵金蓮花,或格桑花、苜蓿花之類(lèi),貼近大地,深深吸一口帶著草腥味的空氣;再然后,帶著一副怡然,帶著些微的不舍,乘興而歸。
然而,一切都幾成泡影。
確實(shí),世間有許多意想不到,一次簡(jiǎn)單的旅程,就是一段濃縮的人生。只是,人出發(fā)了,可終止旅程;心情出發(fā)了,卻覆水難收。走近是不可避免的了,不是身體,而是靈魂;不是借助飛機(jī)汽車(chē)等現(xiàn)代交通工具,而是幾張紙,和紙上的文字。這些業(yè)已發(fā)黃,卻仍然鮮活的文字,不僅記載著一個(gè)古老民族的滄桑史,而且見(jiàn)證著根河的前世今生,或者說(shuō)根河之根。
神思被絆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一種敬畏,對(duì)根的敬畏,本原的敬畏,對(duì)一個(gè)偉大民族歷史的敬畏。
又想起在場(chǎng)主義的發(fā)現(xiàn):“命名即是創(chuàng)世,說(shuō)出就是照亮。”盡管,專(zhuān)家們說(shuō),“根河”一詞,是由漢語(yǔ)和通古斯語(yǔ)交融生成的,“根”是通古斯語(yǔ),直直的,沒(méi)有分叉的之意;“河”則表河流,自然是漢語(yǔ)。我還是認(rèn)為,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簡(jiǎn)單,何況對(duì)一方水土的命名,一定有比表象更深的原因。什么語(y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命名背后的文化之根。然后,循著一根生命的臍帶,走進(jìn)一個(gè)民族的精神之魂。
去路和來(lái)路,都是一條河,根河。
盡管這里有很多河,除根河外,還有激流河、金河、烏魯吉?dú)夂印㈩~爾古納河等等,但我的目光,還是一下聚集在了根河。不因別的,只因那個(gè)根字。據(jù)說(shuō),根河是蒙古語(yǔ)“葛根高勒”的諧音,意為“清澈透明的河”。我相信,這里的清澈透明,不僅僅指河水,還包括一條河與一個(gè)民族的品質(zhì)。資料介紹說(shuō),根河發(fā)源于東經(jīng)122°37′、北緯51°16′,海拔1241米的大興安嶺伊吉奇山西南側(cè)。河長(zhǎng)427.9千米,自東北向西南,流經(jīng)根河市、額爾古納市和陳巴爾虎旗,在四卡北12公里處,匯入額爾古納河。好一個(gè)額爾古納河,一個(gè)多么熟悉而神圣的名字!去年我才去過(guò),對(duì)那里的歷史人文略知一二——那可是蒙古民族的發(fā)祥地啊;而匯入,則表明了根與主干的關(guān)系。原來(lái),根河與額爾古納河,本就是一體,擁有共同的根系。
并不是每一次尋根,都是一次輕松快樂(lè)之旅。此刻,我的感覺(jué)正是這樣。比如蒙古,比如根河。
草原浩瀚,天地相接,牛羊?yàn)樾牵n鷹不過(guò)是穹宇中的一顆塵粒。惟有追溯是狹窄的,幾乎每一次的追溯,都難免追溯到慘烈的爭(zhēng)奪、廝殺和刀光劍影。叢林法則和叢草法則,都是一個(gè)道理。本是同根,相煎何急?原因很簡(jiǎn)單,人為財(cái)死,鳥(niǎo)為食亡,何況那時(shí)草原資源稀缺,人們常常食不果腹,衣難遮體。弱肉強(qiáng)食下,可能有你就沒(méi)我。道德疏離,秩序迷亂,仇視瘋長(zhǎng)下,弓箭就是法治。一切都是為了生存和擴(kuò)張,爭(zhēng)奪,廝殺,征戰(zhàn),血腥,因人性而毀滅人性,沒(méi)有什么正確與錯(cuò)誤之分。“饑寒起盜心”,這些古老而殘酷的遺訓(xùn),與地域和族群無(wú)關(guān),只與人性的劣性相聯(lián)。說(shuō)不定,有的類(lèi)似古訓(xùn),就產(chǎn)生于這樣的背景里。蒼鷹飛過(guò),天空沒(méi)有留下翅膀。無(wú)論勝者還是敗者,個(gè)體都是渺小的。草原只記住了成吉思汗,記住了綿延不斷的族姓,蒙古族,還有與之同生共在的鄂溫克、漢、回、藏、苗、彝、壯、朝鮮、滿(mǎn)、土、錫伯、達(dá)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俄羅斯等民族。
好在,根是最大的黏合劑,總是把對(duì)立連接在一起,讓其若即若離,相生相克,爭(zhēng)而不奪,奪而不滅。
最大的消解對(duì)立仇視之力,就是根。
面前有一本書(shū)——《鄂溫克族簡(jiǎn)史》,紙頁(yè)已經(jīng)微微發(fā)黃,作者為鄂溫克族歷史學(xué)家烏云達(dá)賚。作者以古地名為經(jīng),以不同時(shí)期的稱(chēng)呼,如鄂溫克、索倫、烏素固、弘吉剌、安居、沃沮等為緯,然后經(jīng)緯交織,將歷史的碎片拼接成網(wǎng),鎖定了自己的判斷。我背上行囊,隨著作者認(rèn)定的軌跡,從根河出發(fā),一路追根而去,順著哈拉哈河、洮兒河、松花江西岸、長(zhǎng)白山北麓、圖們江流域、綏芬河、烏蘇里江、錫霍特山脈南段,一直追溯到西漢河平元年之前(公元前28年)烏蘇里江上、中游流域的“沃沮”人,追到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沿岸的土著,追到公元前2000年的銅石器并存時(shí)代,那遙遠(yuǎn)高寒地帶的游牧民族。
事實(shí)上,早期的鄂溫克人和蒙古人,都同屬于北方游牧民族,同屬阿勒泰語(yǔ)系;而直至元代以后,“蒙古”二字才固定下來(lái)。換句話(huà)說(shuō),對(duì)于這片土地,鄂溫克族祖先的到來(lái),比蒙古族的正式命名,至少早了一千多年。另有考證,在公元9-13世紀(jì),根河地區(qū)居住的弘吉剌部鄂溫克族人,原本就是蒙古族人,或蒙古化的通古斯人;在他們中有一個(gè)daayil(daakil)部落,很可能就是后來(lái)的達(dá)斡爾族源。
一切似乎都清楚了,關(guān)于根,根河之根。
同根當(dāng)相惜。什么原本不原本,同根的血脈與包容,才是真正的原本。其余都是流動(dòng)的,交融的,變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shuí)能否認(rèn),當(dāng)年游牧于廝殺于這片草原的部族,從毛割石、蒙兀室韋、篾劫子、毛揭石,到孟瓦室韋、萌古子、梅古悉,等等,本身就很難按后來(lái)劃定的族姓一一對(duì)接。他們有的可能成了后來(lái)的蒙古族,有的也許成了后來(lái)的鄂溫克族,或者草原的其他民族。開(kāi)放的鄂溫克族人本身,就禁止族內(nèi)通婚,倡導(dǎo)異族通婚。誰(shuí)能否認(rèn),在成吉思汗強(qiáng)大的金戈鐵馬面前,部族間的征服、統(tǒng)一、歸順,甚至通婚、融合,壯大與削弱,已超越了以族為界的秩序。誰(shuí)能否認(rèn),分分合合是歷史,草原,才是大家唯一永恒的母親;而根河文化,則是一脈相承的地域人文之魂。
是的,對(duì)于母儀的草原,林林總總的族性,都只是符號(hào),只是過(guò)客。無(wú)論是匆匆地來(lái),還是匆匆地去;無(wú)論停留的,還是走失的,都像草原上繁盛的花草,或同一父母膝下的兒女。他們雖然綻放在不同季節(jié),來(lái)到的時(shí)間有早有遲,擁有不同的名字和民族習(xí)俗,但都有相同的不可拒絕的血緣和根系。因此,要感謝草原。是草原的博大安靜,讓這些廝殺的部落變得包容,安靜下來(lái),和睦而處,相依為鄰。要感謝根河。是這方純凈的草和水,讓鄂溫克族在顛沛中得以安頓,不僅繁衍生息族群,還繁衍生息美好的日子。要感謝敖魯古雅。這個(gè)具有“北極村”之稱(chēng)的圣地。是這里的茂林繁草,讓這支肩負(fù)使命的戍邊之旅,能夠安下心來(lái),開(kāi)始安定的生活,一留就是300多年。鄂溫克是他們的自稱(chēng),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們”。至今,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里,仍有鄂溫克人的腳印與炊煙。他們與世無(wú)爭(zhēng),自得其樂(lè),過(guò)著桃源式的日子。要感謝生命。有了草原上這些生生不息的生命,廝殺與共生,敵對(duì)與通婚,都是形式。重要的是存在,海德格爾“此在”式的存在,鑄就了草原的永恒之根。
無(wú)疑,爭(zhēng)奪、仇視與廝殺,乃痛苦之源。而包容、尊重與發(fā)展,才是安穩(wěn)之根。一個(gè)馬背上的民族,遭遇了太多的顛沛戰(zhàn)亂,廝殺爭(zhēng)奪,最大的祈求,莫過(guò)于安穩(wěn)。這才是最珍貴的精神之根。它植之于人心,系之于根河,浸潤(rùn)于呼倫貝爾。
然而,歷史的根河,讓人怎堪觸摸。
仍是紙,就在面前。我剛從電腦上下載的文字,就篤守在紙上。我輕輕一翻,就走進(jìn)了一座浩瀚而神秘的宮殿——敖魯古雅鄂溫克族獵民鄉(xiāng)博物館。循著紙中墨跡,我翻閱這個(gè)民族的興衰史。從戰(zhàn)國(guó)、秦時(shí)的東胡駐地,漢時(shí)匈奴左賢王庭的屬所,到三國(guó)、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東部轄地,隋、唐蒙兀室韋部落駐地,及清代呼倫貝爾副都統(tǒng)轄;從過(guò)去的遷徙廝殺,到近代的戰(zhàn)爭(zhēng)疾病。在漫長(zhǎng)的歲月里,這個(gè)地區(qū)和這里的民族,艱難曲折地、顫顫巍巍地一路走來(lái),沒(méi)有走失,就是最大的慶幸。到1945年,這里的鄂溫克族僅存1000余人。不斷的血脈,是不滅的生命之火,只要在燃燒,根就在,生命就要繁衍。
我走進(jìn)一個(gè)獵戶(hù)人家,以文字的方式。
這是一個(gè)入贅家庭,兩老兩中一小,三代五口,棲居于一座寬敞的蒙古包里,過(guò)著亦牧亦游的小康生活。小孫孫馬上要小升初了,主人已作好打算,小孫孫一升初中,老兩口就搬進(jìn)城里。為了照顧孩子學(xué)習(xí),家里已在城里買(mǎi)了房,并已裝修好。這一切,與過(guò)去封建牧主式的“尼莫爾”,及漂泊不定的“撮羅子”,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yǔ)。去年和前年,我曾兩次到過(guò)呼倫貝爾,走進(jìn)過(guò)一些蒙古包,只是沒(méi)有細(xì)問(wèn)主人,是蒙古族還是鄂溫克族。但我知道,這里的許多牧民,都構(gòu)建了這種城鄉(xiāng)兩棲式的生活方式。
我以同樣的方式,完成了食與觀的體驗(yàn)。
食品是典型鄂溫克族式的,稀奶油、黃油、奶渣、奶干和奶皮子。主人既自食,又常常用來(lái)招待客人。最常見(jiàn)的吃法,是將奶油涂抹在面包或點(diǎn)心上,就著香醇的奶茶,一吃就是半天。據(jù)說(shuō),居住在北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里的鄂溫克族,則以肉類(lèi)為日常主食,鹿肉、熊肉、罕達(dá)犴肉、野豬肉、灰鼠肉,及狍子肉、野雞、烏雞、魚(yú)類(lèi)等,都是他們的餐上珍品。食法也與牧區(qū)略有不同,其中罕達(dá)犴、鹿、狍子的肝、腎一般都生食,其它部分則要煮食。這樣的食肉習(xí)慣,有點(diǎn)讓我敬而生畏。欣賞的,是舌尖上的幸福。如今,根河除了傳統(tǒng)農(nóng)牧業(yè),綠色食品、木材加工、礦產(chǎn)開(kāi)發(fā)、生態(tài)文化旅游,甚至現(xiàn)代通用航空業(yè)等,都落戶(hù)于此,正成為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主業(yè)。小康之根如此堅(jiān)固,還愁衣食安穩(wěn)?
如游客較多,主人還要進(jìn)行精彩的表演。阿罕拜、愛(ài)達(dá)哈喜楞舞、哲輝冷舞,或“斡日切”。鄂溫克族人崇尚天鵝,以天鵝為圖騰。鄂溫克族婦女們閑暇時(shí),喜歡模仿天鵝的各種姿態(tài),自?shī)识瑁瑒?dòng)作拙樸自信,富有生命的質(zhì)感。宗教式的崇拜與勞動(dòng)中的歡愉結(jié)合,逐漸演變成一種民族獨(dú)有的舞蹈——天鵝舞。如果要追溯,可能追溯到族源中那個(gè)纏綿悱惻的愛(ài)情故事,讓我們走進(jìn)那場(chǎng)王子齊格弗里德成年之日,宮中為他舉行選妃的那場(chǎng)舞會(huì),追到美侖美奐的天鵝湖。現(xiàn)在,天鵝舞成了鄂溫克族人在客人面前展示風(fēng)姿的拿手戲。也展示他們的祭祀儀式。鄂溫克族人崇尚多神崇拜,瑪魯(總神)、白那查(山神)、火神、吉雅奇(牲畜神)、敖卓勒(祖神)、奧米(嬰兒神)、阿隆(馴鹿神)、毛木鐵神等,都是他們心中的守護(hù)者,每一個(gè)祭拜,都專(zhuān)注而虔誠(chéng)。且食且舞,且歌且祭,物質(zhì)與精神的富足,誰(shuí)還愁安穩(wěn)無(wú)根?
原來(lái),紙上的根河,依然如此美麗。
翻開(kāi)旅游地圖,蜿蜒的根河美麗而妖嬈,夢(mèng)幻般流淌在我的視野里。也許是大興安嶺的融雪與清流,注入了生生不息的靈氣;也許是陳巴爾虎的茂草繁花,呵護(hù)住一路的行程;也許是高遠(yuǎn)的藍(lán)天白云,折射著陽(yáng)光的倩影;也許是額爾古納河更浩大悠遠(yuǎn)的召喚,激勵(lì)著意志;也許,還有許多也許。總之,我分明感到,一條有根之河與庸常之河,竟有如此大的區(qū)別。
我明白了,根是生命的神奇。
責(zé)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