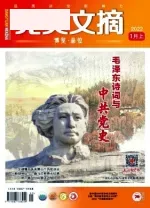“我們村是怎么沒(méi)的”
柯實(shí)
紀(jì)彥峰的老家在陜西省子長(zhǎng)縣南溝岔鎮(zhèn)南家焉村,如今只剩十來(lái)戶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戶,200多人。
過(guò)去幾十年,和許多農(nóng)民一樣,紀(jì)彥峰和家人把離開(kāi)農(nóng)村當(dāng)作成功的重要標(biāo)志。他們成功了,可是,這成功還有另一面……
30年了,紀(jì)彥峰一直在遷徙。他一直希望找到的安穩(wěn),總是會(huì)棄他而去,如同他“拋棄”家鄉(xiāng)。
2005年冬天,紀(jì)彥峰的爺爺去世,家里的東西包括牛羊一類的大牲口全都變賣(mài)了,只給唯一還生活在村里的奶奶留下一個(gè)小菜園,20多只雞和一頭豬。這一年,家里的耕地荒了。
沒(méi)過(guò)幾年,家里人再次變賣(mài)了家產(chǎn)——80多歲的奶奶一個(gè)人住在村里,這讓家里所有人都不放心,奶奶被接到了延安市,住在二爸家里。
最開(kāi)始,紀(jì)彥峰對(duì)家的概念沒(méi)那么強(qiáng)烈。由于父親是小學(xué)老師,頻繁的工作調(diào)動(dòng),使得紀(jì)彥峰上了四所小學(xué)。初中住了兩年校后,父母終于在鎮(zhèn)上安了家。一年后,紀(jì)彥峰去縣城讀高中,從那時(shí)起,家就變成了一個(gè)回去探望的地方。
從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后,紀(jì)彥峰放棄讀研,想找一份賺錢(qián)的工作。他應(yīng)聘到山東一家房地產(chǎn)公司做銷(xiāo)售。幾年下來(lái),有了一定積蓄,在淄博市貸款買(mǎi)了一套房子。2007年底,他搬進(jìn)這套房子,結(jié)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承接項(xiàng)目,紀(jì)彥峰被調(diào)到了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來(lái),他已經(jīng)過(guò)了30歲,也到了要孩子的時(shí)候了。
去年,紀(jì)彥峰買(mǎi)下了自己所在房地產(chǎn)公司在郊區(qū)開(kāi)發(fā)的樓盤(pán),付了首付。春節(jié)之后,紀(jì)彥峰回了一趟山東,出租了那套已經(jīng)沒(méi)人居住的公寓。
這是他經(jīng)歷的第三次變賣(mài)家當(dāng)了,只是這一次,不是在陜北農(nóng)村老家,而是城市里。雖然不用賣(mài)糧食,不用殺豬,但同樣的場(chǎng)景讓紀(jì)彥峰感覺(jué)空落落的。“我為什么對(duì)家這么在意……我真的沒(méi)有家。”紀(jì)彥峰念叨著。
從小,父親就告訴紀(jì)彥峰一定要走出大山。家鄉(xiāng)自然環(huán)境惡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飯,作為小學(xué)老師的父親,知道窩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紀(jì)彥峰從小就愛(ài)看一切有文字的東西,那時(shí)候,看書(shū)是他唯一“走出去”的方式。
父親有兩個(gè)弟弟在城里打工,他們則是紀(jì)彥峰看到外邊世界的另一個(gè)“窗口”。
六歲時(shí),紀(jì)彥峰第一次去延安市里。“雖然沒(méi)什么意識(shí),但對(duì)城里也留下一些光怪陸離的印象:汽車(chē)、火車(chē),第一次喝汽水,像吃辣椒一樣,第一次暈車(chē),都是很獨(dú)特的體驗(yàn)”。
農(nóng)村里的人走出去,一般就是指到縣城,或者延安、西安,很少出省。紀(jì)彥峰覺(jué)得,到西安并不算是走出去。所以當(dāng)山東那家房地產(chǎn)公司來(lái)校園招聘時(shí),他選擇了比陜西發(fā)展程度更好的山東。
可是淄博這樣的三線城市依然沒(méi)有讓紀(jì)彥峰感覺(jué)到自己走出去了,總覺(jué)得淄博平臺(tái)還是太小,和自己的夢(mèng)想仍有差距。
工作兩年后,紀(jì)彥峰去上海出差時(shí)見(jiàn)到了一個(gè)大學(xué)同學(xué)。短短兩年時(shí)光,已經(jīng)讓他明顯感覺(jué)到了兩人之間的差距,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或者收入上。
當(dāng)公司準(zhǔn)備派人去北京時(shí),紀(jì)彥峰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個(gè)機(jī)會(huì)。
這些年,親戚們都成功地“拋棄”了村子。
在上世紀(jì)80年代,作為全家公認(rèn)“有想法”“愛(ài)折騰”的二爸,就在農(nóng)村待不住了。
二爸高中成績(jī)很好,如果當(dāng)年沒(méi)退學(xué),紀(jì)彥峰可能不會(huì)成為村里第一個(gè)大學(xué)生。
一直想干點(diǎn)兒什么的二爸,忍耐不了學(xué)校單調(diào)的生活,便回家務(wù)了農(nóng)。可種地的枯燥令他更加受不了,幾年之后,20歲出頭的二爸去了延安市。
在延安市,二爸在建筑工地干過(guò),開(kāi)過(guò)拖拉機(jī),倒騰過(guò)服裝,販過(guò)煤。這些營(yíng)生都沒(méi)干長(zhǎng)。幾年后,二爸帶著二媽和兩個(gè)孩子回家了。
這一回家,就是十年。二爸承包過(guò)幾百畝土地,以機(jī)械化耕作的方式,種植藥材、向日葵等經(jīng)濟(jì)類作物,還販賣(mài)過(guò)土豆。而這些致富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一次,二爸得知一個(gè)遠(yuǎn)房本家親戚在延安市里做起了賣(mài)面皮的生意。憑著多年“折騰”的經(jīng)驗(yàn),他再次離開(kāi)村莊,跑去延安市給這個(gè)遠(yuǎn)房親戚打工。
這回,二爸終成正果。在打工一兩年后,自己開(kāi)起了面皮作坊。爾后,又把家里的很多親戚帶到延安市。
如今,延安市三分之一的面皮生意都被紀(jì)家做了。
今年過(guò)年回家時(shí),大姑家的大兒子和二爸再次討論了家里生意的前途。
大姑家的大兒子是紀(jì)彥峰的大表哥,頭腦靈活。高中畢業(yè)后,大表哥去當(dāng)了兵。幾年后,大表哥躊躇滿志地回到村里,準(zhǔn)備競(jìng)選黨支部書(shū)記,可是事與愿違。大表哥“從政”不行,只得外出務(wù)工,去山東、廣東東莞的刀具廠、造鞋廠當(dāng)工人,甚至搞過(guò)傳銷(xiāo)。
在外四處碰壁后,大表哥選擇回延安跟著二爸干,雖然理念上總是有沖突,但總算有個(gè)正經(jīng)活計(jì)做了。
今年春節(jié),紀(jì)彥峰基本把家里人都見(jiàn)到了。他的平輩人基本都上了大學(xué)、大專,在子長(zhǎng)縣里開(kāi)大貨車(chē)的二姑家老三也由家里出錢(qián)在縣城買(mǎi)了房,娶妻生子了。
三爸在寶雞做值夜保安,白天打另一份工,經(jīng)過(guò)多年,也在寶雞扎根扎得很穩(wěn)了。20年前,他被迫離開(kāi)村子。作為最小的兒子,他本想在家侍奉父母,但是由于生在陜北大山里,是不會(huì)有姑娘嫁過(guò)來(lái)的。三爸深知,不出去,就意味著找不到媳婦。
只有父親總念叨著要回老家。為了給二爸幫忙,父親在學(xué)校辦了內(nèi)退。父母幾年前搬到延安市,在農(nóng)貿(mào)市場(chǎng)開(kāi)了個(gè)以面皮為主的主食攤子,但這幾年做得并沒(méi)有什么熱情。父親在城市里沒(méi)有朋友,在延安,他過(guò)得不舒服。
父親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女兒。高考前夕,由于學(xué)業(yè)壓力過(guò)大,紀(jì)彥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癥。之后這幾年,父親帶著妹妹去了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親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說(shuō)到回農(nóng)村,“我覺(jué)得這不可能,連奶奶都沒(méi)做到”。紀(jì)彥峰認(rèn)為這不現(xiàn)實(shí),因?yàn)榧依锸裁慈硕紱](méi)有了。
今年春節(jié)紀(jì)彥峰回老家時(shí),又走了一兩戶人家,“沒(méi)有新的人回來(lái),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長(zhǎng)大出去掙錢(qián)”。每個(gè)村子只剩下四種人:老頭兒、老太太、隊(duì)干、憨憨(形容笨人)。
在陜北農(nóng)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意味著上墳。
紀(jì)彥峰的一個(gè)詩(shī)人朋友譚克修在題為《潛伏者》的詩(shī)中,將蕭條的村莊比作一個(gè)巨大的充電器。
古同村有黑暗的木房子和鮮艷的紅磚房子
每座房子里有人秘密潛伏
他們化裝成老人、婦女和兒童
他們勤快地掃地,擦拭門(mén)窗、桌凳、柜子上的灰塵
喂養(yǎng)家畜和家禽,曬發(fā)霉的被子和新的傳言
據(jù)說(shuō)這些都是幌子
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制作充電器
他們要把房子制作成一個(gè)巨大的充電器
每到年關(guān),充電器能給長(zhǎng)途汽車(chē)運(yùn)來(lái)的電池
那些疲倦的電池、快耗盡的電池
快速地充滿電
讓電池不管出門(mén)多遠(yuǎn),電量至少能用上一年
可是,越來(lái)越多的人,不再需要回鄉(xiāng)充電了。看起來(lái),他們拋棄了鄉(xiāng)村,或是被趕出了鄉(xiāng)村。
紀(jì)彥峰特別羨慕生在城鄉(xiāng)接合部的人,“不用背井離鄉(xiāng),同時(shí)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希望能夠均衡發(fā)展,不要把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鄉(xiāng)二元化給這個(gè)國(guó)家?guī)?lái)的巨大裂縫,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農(nóng)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補(bǔ)。
城市里的壓力從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紀(jì)彥峰和所有人一樣,要考慮房子、車(chē)子、工作,以后也要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問(wèn)題。他計(jì)劃將來(lái)把父母接到北京。母親在老家上有新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保險(xiǎn),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還需要自己掏錢(qián)。跨地域的醫(yī)療保險(xiǎn),還在政府手里攻堅(jiān)。不太遙遠(yuǎn)的將來(lái),是一個(gè)巨大而叵測(cè)的黑洞。
(摘自《中國(guó)新聞周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