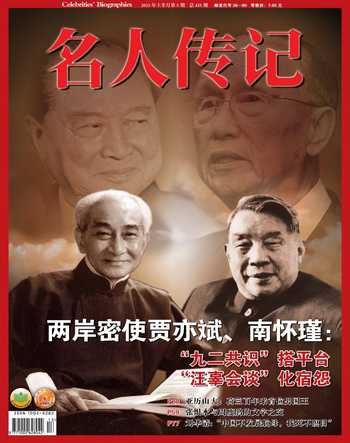將軍戰傷背后的故事
顧保孜
我軍第一代戰將都經歷了血與火的鑄造,靈與肉的熔煉,他們多數人是帶著傷殘的身軀站在了授銜臺上,可以說閃耀在他們肩頭的星花,是將軍們用鮮血換來的,他們無愧于那金燦燦的將星和金燦燦的最高榮譽
粟裕的頭顱骨灰中發現三塊殘碎的彈片
當粟裕率領只有數千人的部隊在蘇北車橋殲敵逾千的捷報傳到延安窯洞時,慧眼識將才的毛澤東當場說了一句極有預言性的話:“這個從士兵成長起來的人,將來可以指揮四五十萬軍隊。”后來,毛澤東的預言真的變成了現實。
然而從士兵到將軍,粟裕走的卻是一條灑滿鮮血、荊棘叢生之路。他半世戎馬,六次負傷。
第一次負傷是在南昌起義失敗之后。
粟裕在周恩來、朱德、葉挺等人的領導下投入了激烈的戰斗。三天后,敵人大軍壓境,起義軍主動撤兵南下。在潮汕失利后,部隊向閩粵贛邊境轉移。而敵人窮追不舍,一直把起義軍逼至閩西南的武平城下。為保存革命火種,朱德令粟裕所在的連隊掩護大部隊轉移。班長粟裕在排長的帶領下,在西門外一座山岡英勇頑強地阻擊如飛蝗般撲來的敵人。
夜幕降臨,連隊完成掩護任務后正準備撤退,忽地,一顆子彈從粟裕右耳上側穿過,頓時血流如注,粟裕昏迷過去。排長奔過來猛搖,見粟裕沒有一點反應,以為他犧牲了,便拿了他的槍,三鞠躬后帶領剩下的戰士默默地撤走了。
粟裕從昏迷中醒來,發現沒有槍聲,也沒有喧嘩聲,周圍死一般的寂靜,再一摸,槍也沒有了。他忍著劇痛,順著山坡滾下去,艱難地爬行到路上,后來在路過此地的幾個同志的幫助和攙扶下趕上了部隊。
身負重傷的粟裕那時剛滿二十歲,之后,他跟著朱德上了井岡山。
在粟裕六次負傷中有兩次傷及胳膊。
1933年2月,紅一方面軍進行整編,粟裕由紅四軍參謀長改任紅十一軍參謀長。
紅軍按照王明“左”傾錯誤路線“不停頓地進攻”,與國民黨軍隊硬碰硬。1933年 5月,紅十一軍進至硝石,要與守敵一決雌雄。
硝石,位于江西省東部,是一個較大的村鎮,駐軍是湖南“馬日事變”的劊子手許克祥的一個師。許曾殺害過許多革命志士。仇人相見,仗打得分外激烈。兩軍對峙,槍彈紛飛,粟裕正揮動左臂指揮,敵人的一顆子彈飛過來,擊中他的左臂,動脈血管被擊破,鮮血噴出一米多遠,他昏死過去。
“粟參謀長!”警衛員撲上去,為他止血。
蕭勁光大喊:“擔架,快送參謀長到救護所。”
粟裕剛躺上擔架,大雨就“嘩嘩”襲來。道路泥濘,山路崎嶇,一行人經三四個小時的艱難行軍,才到達救護所。由于一路淋雨,粟裕的手臂傷口感染,戰地救護所沒辦法治,便派人將他轉送到軍醫院。
軍醫院的醫生一會診,發現子彈是從左前臂的兩根骨頭中間打穿過去的,兩邊骨頭都傷了,還傷了神經,而且已經感染,出現壞死現象。醫務主任難過地說:“粟參謀長,看來你的左臂得鋸掉!別無好法。”
“不!我不!”粟裕的頭“嗡”地膨脹起來,他連連反對。
“不鋸會有生命危險!”醫生的口氣也很堅決。
但他還是說:“就是死了,我也不鋸!”
手臂不讓鋸,但感染了的傷口需要開刀排膿。
當時沒有麻藥,醫護人員搬來凳子,拿來麻繩,將他的左臂牢牢實實地綁在凳子上。接著,醫護人員又將他的右臂、頭、肩死死按住,讓主刀醫生施行手術。別看粟裕瘦小,卻是一條硬漢子,盡管痛得牙齒咬得咯咯響,滿身冒汗,卻始終不喊一聲。
謝天謝地,手術總算做完了。誰知,隨后的傷口護理讓他就像進了鬼門關。
為了防止傷口再次感染化膿,醫生們就地取材,將蚊帳布剪成二指寬、五寸長的布條子,先在鹽水里浸泡,頭一天早晨將布條子從子彈進口處捅進去,第二天早晨抽出來,再捅進一條浸泡過鹽水的新布條,循環往返。結果捅來捅去,傷口不僅長不攏,而且還生出了一層頑固性的肉芽子。醫生無奈,思量再三,不知從哪里找來一個小耙子,捅在傷口里,轉圈兒地摳,要把肉芽子耙掉。就這樣,一會兒布條子捅進捅出,一會兒小耙子耙來耙去,粟裕的傷口整整治了五個多月。每次治傷,粟裕雖嘴里不叫疼,但時常疼得昏死過去。醫生唏噓,護士落淚,他卻說:“只要能保住左臂,我能受得住。”
后來他的手臂還真的奇跡般地保住了。
真是禍不單行,沒有想到第二年一顆子彈又擊中了粟裕的右胳膊。那時,紅軍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下,無力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而被迫轉移。 1934年7月,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率先北上。 9月24日,敵人向紅七軍團宿營地鮑家村、陳村截擊,軍團參謀長粟裕在指揮作戰時,被敵彈擊中右臂。他用布包扎后,忍著劇痛繼續指揮戰斗。在給了敵人沉重打擊后,他指揮部隊趁著夜色突圍而去。
他的右臂雖然沒有喪失功能,但這顆子彈頭在右臂中一直藏了十七年。直到1951年11月,右臂疼痛難忍的粟裕經毛主席批準,才入北京醫院治療,由沈克非教授動手術把彈頭取了出來。
在粟裕六次負傷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要數1930年的那次了。
那年3月,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圍殲國民黨獨立第十五旅。剛剛擔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第二支隊政委的粟裕,想打一個漂亮的殲滅戰。可事與愿違,幾次沖鋒都未奏效。他急了,奪過一挺機槍,就往前沖,但被敵人的火力壓住了。他猛然甩掉帽子,高呼:“不怕死的,跟我沖啊!”
話音未落,一發炮彈在他身邊爆炸,粟裕只覺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戰斗結束后,戰友們把昏迷不醒的政委抬到后方醫院,發現一塊銳利的彈片深深地嵌進了他的顱骨。因醫院條件簡陋,無法進行大手術,醫生只好用紗布將他的頭部緊緊纏住。
這個彈片伴隨粟裕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淮海戰役時,他日夜守候在指揮所,曾經連續七天七夜沒有睡覺。頭疼得受不了,他就讓警衛員反復摁頭,或用涼水沖頭,或者用看地圖來分散疼痛,帶病指揮作戰。
后來醫生給他做了一個簡陋的“健腦器”。頭皮熱了,就把它戴上幫助頭部散熱。但這還是解決不了問題,他的頭部還是又燙又痛。他總是不言不語地用冷水澆頭,警衛員問道:
“首長,你頭痛是啥感覺?”
他說:“不好受,頭昏目眩,每根頭發像鋼針往里扎,手都不敢碰。”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毛主席點將,粟裕是候選人之一。可這時,粟裕的身體狀況很不好,每天頭痛頭暈難忍。他不得不向毛主席報告病情,懇請主席另選主帥。
如果不是這害人的彈片,也許我們會看到粟裕大將軍在朝鮮戰場再創輝煌。
五十四年過去了,1984年2月15日,粟裕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在火化爐上撿掃骨灰時,負責火化爐的老師傅和粟裕大將的長子粟戎生特別仔細。他們忽然從頭顱骨灰中發現一塊直徑約有黃豆大小和兩塊直徑有綠豆粒大小的烏黑色薄片,拿起一看,是三塊殘碎的彈片。
當時,粟戎生特別吃驚,難道父親生前的頭痛病,就是這三塊彈片引起的?他立刻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悲痛之中的母親楚青。楚青用顫抖的手捧著三塊彈片,翻來覆去看個不停:終于找到了丈夫多年頭痛的真正原因。
九次負傷的徐海東與周少蘭的情緣
在大將的行列中,有一位從大別山走出來的窯工,他身經百戰, 九次負傷,他的眼睛、大腿、胳膊,以及胸口、肩膀、臀部等,留有十七處傷痕。國民黨曾先后殺了他的母親,逼著他的妻子改嫁。敵人血洗徐家窯,徐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包括剛滿周歲的嬰孩共六十六顆腦袋掉地,但蔣介石卻拿不到他的腦袋。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東。
徐海東是紅二十五軍的創始人。負傷在徐海東看來就是“小菜一碟”,他常說能打死他的子彈還沒有造出來呢。
那是紅二十五軍北上長征的時候。部隊行至方城縣獨樹鎮,突遭敵軍攔截。緊要關頭,徐海東躍馬揚鞭趕到,揮刀沖入敵陣,硬是殺開一條血路。第二天,部隊又遭突襲,又是他一馬當先,率部反復沖殺。
沒想到在激戰中,一顆子彈射進他的頭部,他當即倒地昏死過去。這是他第九次負傷,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來時,他問身邊的人:“現在幾點了?部隊該出發了吧?”軍政委吳煥先告訴他,部隊安然無恙。
在這令人焦急的四天四夜里,有一位美麗的少女一直守候在軍長徐海東床前,等待著軍長醒來,她就是護士周少蘭(后來改名周東屏)。
看見徐海東醒過來了,周少蘭激動得掉下了眼淚。
清醒過來的徐海東,看見一個淚眼模糊的女護士守在自己床前,手里還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面條。
“小同志,不要哭嘛!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過是睡了個痛快的覺嘛!”
看見軍長傷勢這么重,竟然還這么樂觀詼諧,周少蘭心中頓時涌起一種像親人起死回生、失而復得的幸福感,臉上立刻蕩起了笑容。
這是周少蘭第二次近距離地接觸徐海東。她第一次接觸徐海東是在1934年11月。當時,蔣介石的殘酷“圍剿”,使紅二十五軍不得不暫時告別大別山這塊英雄的土地。
隊伍要過平漢路了,前有阻敵,后有追兵,形勢異常險惡。部隊決定把一些老弱病殘的同志留在原地。為了軍部醫院女護士的安全,也決定把她們精簡下來,每人給了八塊大洋。誰知女護士們坐在地上生氣,賴著不走。周少蘭大膽潑辣,猛地站起來,把銀圓往地上一摔,哭著對政治部的干部說:“你讓我們回去,往哪兒去?我是逃出來參加紅軍的,難道還要我重新去當童養媳嗎?”
這位干部講了許多道理,姐妹們就是聽不進去,要求去見軍參謀長。參謀長一見面就嚴肅地說:“政治部的意見是對的,你們就留下來安家吧!”
正好時任副軍長的徐海東騎馬過來,女護士們像見到了親人,不約而同地圍上去,詳細地訴說了事情的經過,并表示堅決要求跟隨紅二十五軍遠征。
別看徐海東是一個硬漢子,可望著面前這七個即將被遣返的可愛的姑娘,他知道等待著他們的命運將是什么,他的心開始軟了……
沉思了一會兒,徐海東對參謀長說:“這幾個女孩子,都是經過艱苦斗爭考驗出來的,她們革命的決心很大,就讓她們和我們一起走吧! 再說我們打仗也還需要護士嘛!”
聽到徐海東的表態,七個姑娘破涕為笑,對著徐海東深深地鞠了一躬:“謝謝軍長!”
“這有什么好謝的。上前方不是要你們去玩,是要去照顧傷員的,懂嗎?”
“是,首長。等將來你負傷了,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周少蘭話一出口,馬上覺得說錯了,把個小舌頭伸得老長。
真沒想到一句玩笑話,竟成了真。這時的周少蘭開始后悔起來,我為什么要說那晦氣的話呢?
醒過來的徐海東經周少蘭提及,才從那段往事中依稀找到了記憶。
想不到一年前哭著鼻子要跟紅軍走的小護士,如今成了一個成熟美麗的大姑娘。徐海東不禁怦然心動。
說實在的,徐海東這次負傷,還多虧了周少蘭的細心照顧。他負傷那天,頭上臉上全是血,喉頭被血和痰堵著,呼吸極為困難,情況萬分危險,醫生們急得不知怎么辦才好。這時,周少蘭站過來說:“讓我試一試。”說著,就伏在徐海東床前,口對口地吸出了堵在他喉頭的血痰,險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東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她替他打針換藥,擦洗身子,換洗衣服,還不時地往他嘴里潤點水,照護得細心周到。
在朝夕相處中,徐海東知道了周少蘭的身世。他開始喜歡上這個聰慧的女護士。而徐海東詼諧樂觀的性格也感染著周少蘭。
在周少蘭的精心護理下,徐海東終于痊愈要回到自己的崗位上了。要走了,徐海東還真有一種難分難離的眷戀心情。徐海東離別的話竟是:“下次負傷,還請你來照顧我好嗎?”
“看首長凈說不吉利的話。”周少蘭噘起小嘴。
從相互鐘情到結為夫妻,他們又走過了一段風雨歷程,直到長征到達陜北后才舉行婚禮。
婚后,徐海東傷痕累累的身體得到了周少蘭的精心照顧,因此徐海東常常感嘆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是一個因禍得福的人。
許光達外出療傷逃離“肅反”黑名單
許光達也是一個因禍得福的人,他的禍和徐海東一樣,也是在戰場上身負重傷。那“福”是什么?
1932年3月,瓦廟集血戰進行了七天七夜,這是湘鄂西蘇區歷史上最輝煌、最慘烈的一仗。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集中了五個旅的兵力瘋狂“圍剿”,王明“左”傾路線代表在反“圍剿”中大力推行“不許部隊后退半步”的“新戰術”,并且大搞“火線肅反”,濫殺無辜,使紅三軍內外交困。已是紅二十五團團長的許光達也上了“肅反委員會”的黑名單。
這時戰斗正在激烈地進行著,而保衛干部卻蹲在團部要抓人,許光達說:“著什么急,打完這一仗我就跟你們走,頂多個把鐘頭。” 說著,他就沖進了火海。
戰斗結束,許光達身負重傷,昏迷不醒,被直接送到了洪湖瞿家灣的紅軍醫院。師長段德昌一身炮火硝煙味打馬趕來,向醫院余學藝院長懇求:“許光達不可多得呀,你們一定要救活他,一定一定救活他……”
這時,醫生楊鼎成對段德昌說:“別做大指望,子彈離心窩子近得很,動刀子,危險性很大。”
“那怎么辦?不動刀能救活嗎?”段德昌急切地問。
“不動刀子,命就沒了!”
“那還等什么?就開刀吧!”段德昌急得頭上直冒汗。
“動?怎么動?麻藥都沒有。這么大的手術,要開膛破肚啊!”
段德昌一聽急了,開膛破肚的事誰忍受得了啊!這時躺在地上的許光達開了口:“沒麻藥,不要緊,里外是個痛!”
見許光達說話,段德昌驚奇不已,撲上去問:“光達,你醒啦……”
“炮樓打掉了嗎?”許光達虛弱地問。
段德昌直點頭,眼里發潮:“柳枝集打下來了!瓦廟集也打下來了!”
許光達嘴角微微含笑:“那好,先不忙動刀子,先把我送到肅反委員會去吧。”
“誰說的?”段德昌憤怒地問。
“不用問了,師長,我接受組織審查……”許光達態度堅決。然而,他說完眼皮一合,又昏死了過去。
“不管什么肅反不肅反,救人要緊!”段德昌對醫生命令道。
初步檢查確認,許光達體內的彈頭離心臟只有一公分左右,手術分秒不能耽誤!余學藝和楊鼎成說干就干。
于是,一張簡易的長條木桌,一堆刀刀剪剪搬進來了。這些剪刀只有少數幾件是通過地下組織從上海、武漢搞到的正式用品,大多數是鐵匠鋪打的。楊鼎成又抬來了一桶滾開的鹽水浸泡著半桶棉花,還有一個可以洗澡的長形木盆,放在條桌底下。這就算是手術設備。
因為沒有麻藥,楊鼎成的牙齒咬得咯咯響,就是不忍心下刀。
“沒關系,我吃得住,干吧!”許光達瞪著雙眼催促醫生,并把一條毛巾塞到嘴里咬住。
手術整整折騰了三個多鐘頭。然而,由于子彈進得太深,手術沒有成功。
這時,賀龍聞訊趕來了。他決定派人送許光達去上海,那兒有家中共地下組織控制的醫院,全國各紅色游擊區高級指揮員負傷,都可秘密送去治療。
歷盡千難萬險,傷勢嚴重的許光達終于被送到了那家上海醫院。但想不到的是那家醫院遭到了敵人的破壞,許光達又只好經地下組織安排,輾轉去了蘇聯治療。
在莫斯科,那顆距心臟只有一公分的子彈頭被取了出來。
1937年,許光達從蘇聯傷愈回國,見到賀龍。賀龍說:“國民黨打了你一槍,卻救了你一條命。別人挨一槍是禍,你挨一槍是福。”
這話雖然幽默卻含有深意。的確,如果許光達不是因為負傷到蘇聯治病,極有可能也和段德昌、孫德清一樣被“肅反”的夏曦殺害。他外出治傷逃過了這一劫。
一張照片上的三個獨臂將軍
這是一張在戰爭年代普通紅軍干部的合影照片,照片上三個年輕紅軍干部個個英姿勃發,洋溢著青春的活力。但仔細一看,你會發現,三個人每人都只有一只胳膊,三只袖子空蕩蕩地下垂著。
這三個年輕紅軍干部分別是彭清云、左齊、晏福生。
三軍統帥毛澤東曾驕傲地說過:“中國從古到今,有幾個獨臂將軍?舊時代是沒有的,只有我們紅軍部隊,才能培養出這樣的獨特人才!”
彭清云十六歲就當上了紅十七師五十三團二連政治指導員,他二十歲升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七一九團一營教導員。
沒有想到才二十歲的他,就在這年的一場對日作戰中失去了右臂。
那年 9月,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為了摧毀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糾集數萬兵力,分二十五路,對以五臺山為中心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圍攻。
10月 25日,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獲悉日軍北線指揮官常岡寬治中將率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部分人員,由張家口進至蔚縣、廣靈方向,遂令七一九團在廣靈城南二十里處的邵家莊地區伏擊。
七一九團團長賀慶績得令,即任命彭清云為突擊隊長,帶領他任教導員的一營擔任向敵人沖擊的任務。 28日午夜,突擊隊進入伏擊地域。
第二天上午 10時,鬼子在炮擊了一陣后,便從廣靈向邵家莊開過來。
待鬼子進了埋伏圈,戰士們在彭清云的指令下,投入了戰斗。
彭清云率領的突擊隊員一個個像下山的猛虎,向敵人猛撲過去,橫挑豎刺,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日軍士兵全部消滅了。
“快,搬戰利品,撤!” 彭清云急促地命令道。
突擊隊員立刻跳上汽車,搬走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就開始撤退。
突然,“嗒嗒嗒”的機槍子彈飛過頭頂,原來,日軍增援部隊趕了過來。彭清云和張有仁班的戰士立刻趴在報廢的汽車下,掩護戰友撤退。張有仁為掩護戰友,在連續刺死三個日軍士兵后,中彈犧牲。彭清云想沖上去搶救張有仁,結果右肘關節被子彈打穿。
戰斗結束后,彭清云被送到三五九旅衛生部前方醫院搶救。但由于八路軍缺醫少藥,醫療條件不好,他的傷勢日趨惡化,傷口嚴重糜爛。
醫院實在無能為力,立即組織民兵用門板將他抬到七十里外的靈丘縣河浙村三五九旅后方醫院第一衛生所,請白求恩大夫給他手術治療。然而不巧,白求恩到前方去了。一直等了四天,還是不見白求恩大夫歸來。
雖用各種辦法臨時救治,但彭清云怎么也支持不住,一次又一次昏厥過去。旅衛生部副部長潘世征心急如焚,只得向王震旅長打電話告急。
王震果斷決定:“立即送彭清云到前方找白求恩大夫手術治療!”
彭清云在戰友的護送下,冒著漫天大雪,終于在前線醫院找到了白求恩大夫。
彭清云在朦朧之中,見到了這位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白求恩用英語說道:“準備,馬上輸血,不然難以手術。”
可是醫務人員卻面面相覷,因為已沒有適合彭清云的血源了。
聽完護士的報告,白求恩擼起衣袖,伸出胳膊決然地說:“抽我的血!”
……
就這樣,白求恩的鮮血,徐徐地流進彭清云的血管里。白求恩為彭清云做截肢手術后,一直守候在他身邊,直到他蘇醒了才離開。
三個月后,彭清云傷愈出院。他向王震旅長要求仍回七一九團,決心奮勇殺敵,報答黨、報答白求恩大夫的救命之恩。
無獨有偶,還有一位年輕的八路軍干部,也是經過白求恩大夫的搶救保全了性命,丟掉一只胳膊,而且也是右臂。他就是左齊。
1938年11月 15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參謀長左齊獲悉日軍一個運輸大隊由蔚縣向淶源輸送物資。這是送到嘴邊的肥肉。左齊當即率部連夜奔進,于 16日拂曉進至淶蔚公路之間的明鋪村設伏。
塞外的冬天滴水成冰,八路軍戰士臥冰趴雪兩夜一晝。到17日晨,正凍得難以忍受時,忽聽“隆隆”的汽車馬達聲由遠及近,一股敵軍從蔚縣向明鋪駛來。披掛風霜的八路軍戰士頓時熱血沸騰,摩拳擦掌,要給日軍一點顏色看。
日軍汽車逐漸開近,為了確保伏擊戰的勝利,左齊雙目死死盯著車隊,小聲命令:“注意,拉雷,好!拉!”隨著他的命令,戰士們拉動繩索,駛入八路軍地雷區的日軍汽車被掀上了天。日軍前車炸毀,后車沒剎住,沖了上去,當即死傷一片,亂作一團。
左齊乘勢命令:“機槍,打,狠狠地打!”
頓時,“嗒嗒嗒”的機槍聲和“轟隆隆”的手榴彈爆炸聲震天動地。
日軍先是一陣大亂,隨即在指揮官的招呼下,集中起來,開始死命反擊。
在八路軍猛烈的火力打擊下,日軍只能收縮兵力,龜縮于汽車底盤下抵抗。
突然,我軍的機槍卡殼了。左齊焦急萬分,一個躍身,跳進機槍陣地去排除故障。就在這時,反撲的日軍一排子彈襲來,打中了左齊的右臂上部。頃刻,血如泉涌,染紅了山石、黃土、干草。
幾個戰士躍上去搶救他。他大喊:“別管我,快,朝鬼子狠狠地打!”
這次戰斗結束,全殲日軍二百多人,燒毀敵汽車三十五輛,還繳獲了一些槍炮。
而左齊終因流血太多,臉色蒼白,支持不住,暈了過去。
旅衛生部政委、主治醫生潘世征為了保住左齊的右臂,使出渾身解數,還是沒能成功,傷情在進一步惡化。
王震旅長得知后,堅決地對潘世征說:“不能再等,送左齊到下石樊村,請白求恩大夫動手術。”
臨行前,王震又對左齊親切地說:“你的右臂血液不流通,潘政委說無法保留,要做截肢手術,馬上送你到下石樊村,讓白求恩大夫給你醫治。”左齊默默地點了點頭。
白求恩大夫為左齊做了右臂截肢手術后,天天為他清洗傷口、換藥。當時八路軍藥品很困難,又趕上左齊的傷口發炎不愈合,白求恩大夫便拿出自己僅有的一小瓶磺胺給他用上,才使他的性命得保。
另一個獨臂將軍是晏福生,戰爭年代兩次“光榮”的他雖然最終安然無恙,但戰爭年代還是給他烙上了一個顯著的標記——沒有右臂。
(責任編輯/穆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