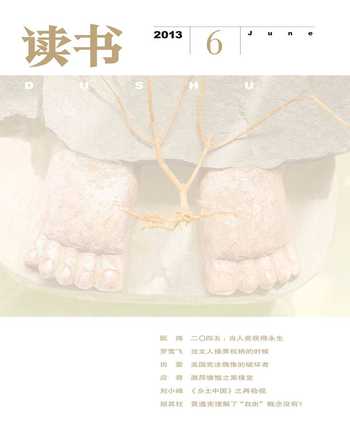讓價值穿透幽暗人性
李磊
作為電影研究的學者,崔衛平卻努力要成為伍爾夫那樣的“普通讀者”,看似低調的言說,實為更高的追求。這意味著沒有功利心,只受本能驅使,為電影而沉迷電影;表達也力爭擺脫專業的腔調,呈現生命的質感。這樣一來,毛尖估計會成為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但不同的是,形而上的思考是崔衛平學術的底色,就像她在《迷人的謊言》自序中所提:“什么樣的東西更容易吸引我呢?簡單地說,就是復雜的東西。”普通讀者的訴求、形而上的精神底色及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使她的電影研究始終彌漫著社會關懷。
收入本書中的二十八篇隨筆(本應二十九篇,另外一篇為《我稻田里的兄弟》,崔原以此題目命名該書稿,由于其他原因,成為現在這樣),是作者在《經濟觀察報》影評專欄的結集,為文平靜和緩,避開吶喊和呼吁,這自然不如龍應臺文氣強勢,但崔文在平靜中充滿張力和尊嚴,恰恰與卡爾維諾之輕吻合;論述也不是就電影談電影,而是從幾部電影故事中生發出一個主題,通過處理差異和談論差異促使這一話題“豐滿地展開”,讓人看到問題的內核。
越過電影的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直接切入深埋在電影中關于人的價值,是崔衛平電影研究的特色之一。價值探討的背后是人性思考,因此,她翻譯過《哈維爾文集》,酷愛阿倫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給她的思想“輸過氧換過血”,柏拉圖、濟慈、雪萊、里爾克很長一段時間在她頭頂盤旋,貢布里希的藝術系列成為她精神的另一個發源地,米奇尼克給她另外一個思維向度,伍爾夫也教她用一個語言為材料的精神世界與實際世界相匹配,如此等等,這同時也回答了一個崔衛平式的問題:有多少好東西才能成就一個有特色的學者?正是這背后的思想譜系,使她的文章中彌散著思想者的氣質,形而上的思考,這不同于富有小資情趣的毛尖,也區別于論著中充滿電影術語的戴錦華。
這種思想氣質與崔衛平的個人底色有關,也有賴于周遭世界的賜予,不論是《迷人的謊言》,還是此前出版的《我們時代的敘事》、《思想與鄉愁》、《積極生活》、《帶傷的黎明》等書,都屢屢出現一個詞:逼仄。逼仄的境遇,內心與現實的緊張迫使她質疑、探索、追問、反思,這如同穆奇爾代表作《沒有個性的人》中所寫:人們必須首先像一個小丑被他的緊身衣束縛那樣,在他們的種種可能性、計劃和感情中受到各種偏見、傳統、困境和局限的約束,他提出的東西,也許才有價值,才能生長和持久。可以說,思想家是時代造就的,作為時代思者的崔衛平也是這樣,時代束縛使她的表達呈垂直的介入狀態,觀點自然而不隔,且更徹底更具生命張力。進而她悟出:思想即處理自身的黑暗(《思想與鄉愁》,崔衛平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205頁)。處理自身的黑暗也是處理時代精神的黑暗,受到時代的偏見、束縛、壓抑、困惑、剝奪、羞辱,內心產生的蒼涼幽暗大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于是惡性循環起來,而思想就是自我剖析,自我教育。過程雖伴著痛苦焦灼,但可以“從黑暗中提取光明,從廢墟中建立起永恒的非凡力量”(《思想與鄉愁·代序》)。
思想如何處理這些黑暗?崔衛平說不僅要理解這個世界,還要同時感覺自身,抓住自己稍縱即逝的感覺。人對時代的反思總是與自我意識一起產生,但世人往往囿于現實利益的考慮,壓抑自己真實的感受去達到某種世俗目的,結果就是“將自己掩埋,永遠也不讓自己內心發出具體的聲音”(《思想與鄉愁》,206頁)。可是崔衛平將思想的目光投向迷蒙的暗處,敏感于那些晦澀和缺乏光線的地方,也就是學者張灝所說的人性幽暗之處。《迷人的謊言》中涉及的百余部電影,恰好也帶她到這幽暗之區去傾聽那些被壓抑、驅逐、忽略之聲:死亡的聲音、集權主義壓制的聲音、被傷害被剝奪者的呻吟與哽咽、內心世界的召喚等等,這些聲音促使她思考。
首先,思考人性之惡。崔衛平否認傳統的“善惡二元論”,認為惡不是一種遠離自身的力量,而是潛伏在身體內部。她在書中涉及五種惡:極端的惡與平庸的惡、瑣碎之惡、非人之惡與人性之惡。極端的惡與平庸的惡是阿倫特面對艾希曼的審判而提出的,崔衛平在電影《竊聽風暴》與《對話》(見《倫理學的想象力》篇)的比較中追問此惡: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能做什么?前者中的竊聽者衛斯勒,堅守良心與倫理的邏輯,在不為人知的暗處,改寫劇本改動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人性得到拯救;而后者中的竊聽者哈里工作出色,也從工作中受益,但是竊聽使他憂郁,無法相信人,落下人性的傷痕,“失掉了用來證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證據,成為一個純粹的物件”。而瑣碎之惡(見《瑣碎之惡》篇)是一種無心的暴行,一種沒有根基、沒有必要的惡,以一種瑣瑣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蝕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隨時可以爆發,令人防不勝防。此惡在電影《浪潮》和《稻草人》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更好的世界》是對此惡的超脫,而日本影片《告白》卻借一個變態故事呈現此惡,崔衛平毫不留情地在結尾評價:這部影片缺少一種價值的透視。在對影片《老無所依》與《黑暗騎士》(見《非人之惡與人性之惡》篇)的論述中,前者呈現非人之惡:希格仿佛從原野上涌出,代表著這片原野最為深沉和盲目的黑暗意志,像幽靈一樣,不知在何時何地出現,這種不確定、毫無由來之惡更加令人害怕;后者突出人性之惡:主角小丑洞察人性,然而卻瞄準人性中的低劣部分,他收集人性中的瑣屑,利用人性的弱項,進行瘋狂的敲詐腐蝕,“讓人作惡的理由比不作惡的理由更充分”,進而使人突破底線,于是人性變得更加低矮難堪。
其次,反思納粹集權主義。一種是反思納粹集權下導演的拍片心理,有里芬斯塔爾和黛德麗兩類:前者投入納粹懷抱,拍攝宣傳納粹的《意志的勝利》;后者不與納粹合作,拍攝《藍天使》與《摩洛哥》。崔衛平用兩篇長文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另一種是通過電影反思納粹集權主義,涉及電影《梅菲斯特》與《藝術家的抉擇》,前者說了一個人如何將靈魂抵押給魔鬼納粹,后者為藝術家辯護,揭露集權主義中“深揭狠批”思維方式的全部缺陷和黑暗。其他篇目也多有涉及集權主義的反思,如《瑣碎之惡》篇中的電影《浪潮》,反思納粹集權的思想仍潛伏在人內心深處,有卷土重來的可能。
第三,思考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思考人無法處理好自己與上帝、內心世界的關系所導致的悲劇,如電影《諾言》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講述失掉信仰后“即使將天堂之門打開,也不會有人認出來”的悲哀;導演布列松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的處死時被赦免的經歷,探討人類的罪與罰,把《罪與罰》改編為《扒手》,呈現人精神的焦灼不安;而《圣女貞德的受難》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將教會當作信仰,將教會的權力當作權威,放棄真正的信仰真理。
第四,思考“怎樣面對社會”。這種處理人與周圍世界的關系在《如何面對叢林社會》中有淋漓盡致的表達,該篇分析《讓子彈飛》中張麻子殺黃四郎與《雙虎屠龍》中斯托達德通過選舉戰勝強盜韋自由的異同,最后總結:“兩個惡人相爭,一般民眾并不能從中獲益。假如不是擁有新的起點和方式,新惡人與舊惡人相比并沒什么不同,新的惡人盡管此刻看起來面善,但是終有一天他會露出貪婪猙獰的面目,如果他自命享有逾越一切的特權。”對二者解決之道的分析可知:面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若沒有一套民主程序,便不能讓每個人的權益得到保護,而法律精神正是治理叢林社會的一劑良藥,否則依然會墮入舊意識形態的牢籠,擺脫不了輪回的命運,弱者依然是受害者,生命與尊嚴仍舊無法保障。
書中還思考了“殘酷和美”、“主創者與影片主人公關系”、“悲劇英雄與命運”、“戰爭與人性”、“死亡”、“在傷害與被剝奪之后”等主題。處理這些幽暗人性,不僅意味著要思考人性在現實中的異化與扭曲,還意味著要“將我們一分為二,自己觀照自己、審視自己”(《正義之前》,崔衛平著,新星出版社二○○五年版,170頁)。這種審視恰似契訶夫給蘇沃林的信中說過的一句話:“您該寫一篇小說,描寫一個青年,他原是農奴的兒子,做過店員和唱詩班的歌手,進過中學和大學,從小受到必須要尊敬長者、要親吻神甫的手、要崇拜別人的思想、要為每一小塊面包道謝的教育;他經常挨打;出去教家館時他沒有雨鞋穿;他常常打架,虐待動物;他喜歡在富有的親戚家里吃飯;他因為覺得自己渺小就毫無必要地在上帝和人們面前假充正經。請您寫這個青年怎樣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點一滴地擠出去,怎樣在一個美妙的早晨醒來時,他覺得他的血管里流著的已不是奴隸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了。”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點一滴擠出去,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其實就是將人內心的幽暗一點點穿透,努力過上一種“符合道德的生活”。
通過電影反觀人性的幽暗,是為了守護生成的價值;而對價值的思考守護恰恰是崔衛平學術生涯一以貫之的精神主線。當人們把《國王的演講》看成國王克服自身口吃缺陷的勵志故事時,崔衛平卻從中看出了當權力遭遇人性時的平等理念。批判納粹專制下導演里芬斯塔爾的文章標題,就是本書《迷人的謊言》之名,文中也引用桑塔格的代表性論文《迷人的法西斯主義》,可見作者是仿擬桑塔格,以傳達迷人的謊言背后是駭人真實的論點,正如畢加索所說:藝術是謊言,它教我們理解真理,至少是那種我們作為人能夠理解的真理。
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幾次強調,理論家應重視藝術的價值而非其價格;崔衛平很推崇克萊夫·貝爾在《文明》一書中關于價值的討論,也強調導演要審視電影的價值而非僅僅做人性書寫。將價值與人性放在一起思考,使崔的問題比伊氏的更讓人感興趣,她認為價值在人性之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神性力量及其光環已經消退,人的時代來臨,但不是那個大寫的人,而是各種小寫字體、小字號的人。在《我們時代的敘事》一書中崔衛平也說道:“人性意味著一種可能性,意味著一個生長和變化的空間,而不是現成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在人的名義下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能發生,人性需要匡正,對人性所擁有的黑暗、墮落、陷溺,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和估計,應該通過法律道德教育來改進和改善人性。而價值更多的是人們自己同意和認可的,是由人們自己來判斷哪些東西是有價值、有意義和美好的,而不是外部強加和規定的。比起道德,“價值”這個詞蘊含更多主動、能動的意味。它也是電影背后的夢想,這些人類向往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而導演將其放進電影之中,人們在觀影過程中拾起這些價值理想,找回信念,尋求其中思考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
近期電影《泰》的高票房背后恰恰是崔衛平電影研究一直反思的“價值缺失”。它以嘲笑底層弱勢族群的無知為爆笑點,王寶強飾演的王寶被看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奇葩”。雖然他促使徐朗反思,徐朗也圓了他的底層夢,但這種縫合式的大團圓是高高在上的施舍,也是中產階級優越性的展示。印度喜劇電影《三個傻瓜》也搞笑,但笑的同時,也有淚水——對僵化教育體制反思時的憂傷,可說是一種契訶夫式的帶淚微笑,連接這笑與淚水的恰恰是電影的價值關懷。
阿諾德說,藝術的目的在給人以光明與美好,但它不能以粗鄙人的品位為法則,任其順遂自己的喜好去裝束打扮,而是堅持不懈地培養關于美觀優雅和得體的意識,使人們越來越接近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樂于接受。《泰》是粗鄙低劣而不是優雅得體,它的光明與美好建立在底層無知之上,建立在弱勢群體受傷害之上。《泰》之于《三個傻瓜》,猶如搞笑之于幽默,傲慢之于慈悲。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在人世的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還有強者對弱者應盡的保護責任、安全的人對遇難的人應盡的救護責任、一切老人對一切兒童應有的慈愛!”這人道主義的言說就是電影背后應有的價值,也是崔衛平電影研究的終極關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