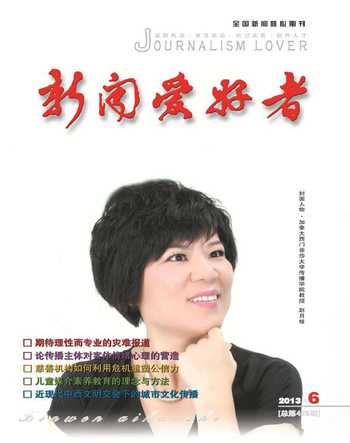論真人秀節目《我是歌手》的成功之道
王超然
【摘要】《我是歌手》節目作為近年來中國真人秀節目的佳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從受眾心理、明星現象、節目手法和內涵角度,分析了節目的成功要素,希望對同類節目起到借鑒作用。
【關鍵詞】電視真人秀;湖南衛視;明星;受眾;紀實手法;精英文化;大眾文化
《我是歌手》源自韓國MBC電視臺大紅大紫的同名節目,作為湖南衛視精心打造的年度大作,其從今年1月18日正式登陸湖南衛視,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收視狂潮,一直霸占同時段的收視冠軍,成了街頭巷尾人們熱議的話題,甚至有學者高呼“真人秀節目的又一個暖春來了”。俗話說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我是歌手》節目第一季以成功者姿態華麗落下大幕的時候,很有必要對其成功背后值得借鑒的原因加以剖析和探討。
一、節目創新:變則通,通則久
2000年6月,中國廣東電視臺《生存大挑戰》節目的開播,讓中國觀眾首次領略到了“真人秀”這種全球炙手可熱的電視節目的魅力。[1]如今,真人秀節目在我國已經走過了13個年頭,泛濫的真人秀節目給觀眾帶來不可避免的審美疲勞。中國電視界和中國觀眾急需一個全新的節目,用變化迎來一個柳暗花明的春天,因此《我是歌手》欄目呼之欲出。
(一)節目形式:明星成為參賽者。明星作為特殊的視覺符號,長期以來被各種電視節目所運用,旨在博取觀眾眼球,吸引該明星背后的特定觀眾。“崇拜明星能給崇拜者帶來極大的情感心理滿足。明星迷戀是一種撫慰空洞心靈的方式,它同樣也是對真實身份與社會角色的尋求。”[2]尤其是在選秀節目中,明星常常以評審的角色出現,對參賽的“草根階層”的舞臺表演和競技水平加以點評。該種節目的泛濫使得觀眾已經對這種缺乏創新的節目形式產生了“免疫力”,導致預計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為了引爆收視熱點,有些節目故意設置明星評審與參賽者的矛盾沖突,并用明星嘉賓的出格言行制造噱頭或是惡意炒作。明星本身的人格魅力和美學價值被掩蓋了,而成為滿足受眾“審丑心理”的“丑角”。
《我是歌手》節目打破常態,把明星歸還給舞臺,極力彰顯明星自身的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還原正常的明星與觀眾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順應了后現代社會的去中心化,消解權威的趨勢,藝術家、明星、名人、權威專家……本來是高高在上的,但在‘真人秀中他們也自然地降低到普通參賽者、普通觀眾的地位。”[3]183這種改變既滿足了觀眾對明星符號的渴望和期待,又使得觀眾完成了由習以為常的仰視視角向充滿交流感的平視視角的轉變。
(二)考核方式:觀眾獨攬“生殺權”。賦予觀眾決定選手去留的權利,作為吸引觀眾注意力、調動觀眾參與性的方法在很多娛樂類節目中都已被廣泛采用。但往往觀眾并不是唯一決定選手去留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觀眾只是作為配角依附于現場評委的選擇。而《我是歌手》節目第一次把這種權利毫無保留地交給了觀眾。在《我是歌手》節目中,500名來自5個不同年齡段的大眾評審是決定歌手淘汰與否的最終也是唯一的“審判者”。而專業樂評人和媒體人的點評只是以幕后采訪的形式出現,他們既不能直接投票又不能左右現場觀眾的喜好。這就使得原本掌握在或絕大部分掌握在專家評委手中的權利,第一次完完全全地下放到普通觀眾手中。權利移交的背后是對觀眾選擇權和個人喜好的最大程度的尊重。“觀眾在電視傳播過程中的主人翁地位,決定了他們具有主動參與的可能性,選擇適當的方式參與電視傳播活動成為不少觀眾的心愿和行動。”[4]20賦予觀眾權利,充分調動觀眾的參與性,觀眾不再只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而成為集傳者和接受者于一身的重要傳播環節,并在心理上獲得極大的滿足感。“明星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無意地去迎合大多數追星族的欲望期待,成為受眾欲望投射的對象。”[2]這種全新的互動和反饋方式,極大滿足了受眾的審美需要和個性偏好,使欄目更好地與受眾相貼合。
(三)節目內容:保持觀眾新鮮感。“觀眾的收視動機建立在人類基本需要的基礎之上,電視節目是為了適應觀眾的各種心理需求而設置的。”[4]13追求新鮮事物是人的本性,對于電視媒體來說,新鮮感是吸引觀眾收看、打開市場、維持觀眾收看、培養欄目忠誠度和收視習慣的不二法門,保持節目的新鮮度是維系欄目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是歌手》采用兩回合淘汰制,每回合皆由500名大眾評審投票決定歌手名次,兩回合票數累計產生最終排名,得票數最低的一位將離開舞臺。與以往其他同類型的真人秀節目不同的是,《我是歌手》節目沒有因為淘汰制的存在而減少參賽的明星人數,而是由另一位新晉歌手填補空缺,新任明星的不斷出現也將穩定吸引其追隨者加入收視群體。這樣的比賽規則,有效避免了觀眾的審美疲勞,不同的明星以及其本身所呈現的不同演繹風格和美學特征會給欄目帶來新鮮的視聽效果,也將牢牢抓住觀眾的注意力。由于復活賽的存在,欄目將明星淘汰所帶來的特定觀眾,尤其是該明星粉絲流失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與此同時,《我是歌手》注重節目內容的不斷變化。“轉盤選歌”增加了節目的懸念感,“齊秦專場”更是在規定的曲目中展現歌手的唱功,這些不定時加入的新鮮元素給予了節目新的看點,滿足了觀眾求新求變的心理訴求。
二、元素融合:取長補短之道
隨著電視娛樂節目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電視視聽藝術和娛樂元素被加入到節目中以期滿足日益挑剔的觀眾,從而使得節目的娛樂效果極大提高,收視爆點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多的節目希望通過豐富的表現手法和娛樂元素滿足各類特定受眾的獨特需求,使之緊緊抓住忠實觀眾的同時吸引更多的游離性受眾,彌補原本單一手法帶來的諸多缺陷和制約,揚長避短、精益求精,帶給節目以新的生命力。
(一)紀實手法和戲劇懸念的“聯姻”。從真人秀節目誕生之初,關于它和紀錄片之間的界定和區分就一直飽受爭議。真人秀節目作為一種娛樂節目類型,充分借用了紀錄片的紀實手法,尤其是在野外生存類和室內生活類的節目中,攝像機如同人的眼睛,會全景展現節目參與者的比賽歷程,從客觀冷靜的旁觀者角度滿足觀眾“窺視”的心理訴求。但是在通常的選秀節目中,紀錄片式的紀實手法如同可有可無的“調味品”,其重要的藝術價值長期得不到重視。《我是歌手》欄目打破常規,對紀實手法的運用在選秀節目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從明星駛抵開始進行全程跟蹤拍攝,包括后場、彩排直至上臺表演的一舉一動都在攝像機的監控之下,使得觀眾得以如此近距離地接觸到明星臺前幕后的言談舉止,極大滿足了受眾對明星的窺視和崇拜心理。更為重要的是,《我是歌手》節目加入了大量賽前和賽后的類似獨白的采訪,面對鏡頭的明星褪去環繞一身的光環,走下遙不可及的神壇,如同面對面般與觀眾進行交流,其中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時刻,產生了極強的帶入感。真實是真人秀節目的命門,尤其是對于以“真情”為節目立足點的《我是歌手》來說,其對紀實手法的重視給觀眾帶來了尤為強烈的真實感,使觀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體驗。
制造懸念作為戲劇創作最常用的基本手法,通過引起觀眾持續性的期待心理和緊張心情,從而激發并維持觀眾的興趣,產生引人入勝的戲劇化效果。《我是歌手》每期首回合競演都會邀請新的明星歌手參與,其候場、準備、排演的整個過程對觀眾是開放的,而對于同臺比賽的其他歌手卻是保密的。這種建立在觀眾對事態發展有所了解的狀態下而產生的期待心理被稱作“期望式懸念”。除此之外,由于節目采用末位淘汰制,因此每期節目結尾處公布結果的過程也成為最大懸念揭曉的時刻。觀眾被壓抑已久的期待以及對自我心理評價和最終結果的對照全部積聚在此處獲得釋放。節目通過大量的參賽者面部特寫鏡頭不斷強化緊張感,并且在揭曉結果時故意延宕增加了觀眾的期待心理。“當真人秀賦予觀眾決定選手去留的權利時,它既更牢固地鎖定了觀眾的注意力,同時也進一步增加了故事結局的變數,戲劇性更為強烈。”[3]184節目完全由大眾評審決定參賽者的去留,其本身就有極強的懸念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懸念的制造與欄目強化使用的紀實手法也有著密切的聯系。正是由于節目中貫穿始末的紀實手法,為懸念的制造奠定了真實可感、極富感染力的環境土壤。從表情的特寫鏡頭到獨白式的心理披露,無一不加深了整個過程的懸念感。
(二)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交融。大眾文化作為電視文化的主流長期占據電視的統治地位,并不斷壓縮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間。在夾縫中苦苦掙扎的精英文化正在不斷衰落,大眾文化逐漸成為一切娛樂化節目的制作樣本和范式。越來越多的娛樂節目成為簡單的復制品,在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精英文化所體現的終極關懷和批判精神備受冷落。《我是歌手》作為大眾文化產品,自然也具有商業化和娛樂化的屬性,并且與現代觀眾的世俗心理和文化品位相契合,“從而滿足大眾群體的精神愉悅,并不斷取悅大眾群體平庸的日常生活和消閑時光”[5]5。
但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不是絕然對立的,大眾文化(至少可以說有一部分大眾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會成為‘高雅的大眾文化,或者‘精英的大眾文化”[5]111。《我是歌手》節目與其他大眾文化產品相比,其本身就吸取并涵蓋了精英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這種文化不但具有嚴肅高雅的趣味,而且具有一種強烈參與社會重大問題的責任感和反思批判性”[6],社會責任感和反思批判性作為精英文化內核的體現也同樣被《我是歌手》節目所容納。在第八期節目中,歌手辛曉琪為了緬懷不幸遇難的小皓博,臨時把參賽曲目改為《親愛的小孩》,并身著素衣含淚演唱,這正是精英文化所倡導的社會參與和終極關懷。此外,《我是歌手》自覺擔負起傳播不同類型的音樂形式以及改變業界浮躁風氣的責任。在節目中民歌、搖滾、電子樂、藍調、爵士等風格迥異的音樂形式都被搬上舞臺,并重新煥發出光彩,而且通過樂評人專業中肯的點評和總結引領指導觀眾。與此同時,《我是歌手》欄目以真情為本,通過歌手現場演唱的方式,用真誠和質樸的表演體現了精英文化的高雅品位,傳遞著真善美的價值追求。這也是對傳統的類似節目中無厘頭的低俗噱頭和不斷觸及文化底線的惡意炒作的摒棄和批判。
(三)代際因素的混搭。不同受眾有不同的訴求,整合彌補受眾群體的差異,找到不同受眾群體間的共同之處,從而實現受眾規模的最大化,是電視欄目擴大社會影響力、實現節目的傳播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關鍵。“傳統的電視綜藝節目大都以某一年齡段或者擁有某一具體需求、愛好的受眾群體為目標受眾,受眾面相對狹窄,節目內容局限度較高。”[7]而《我是歌手》成功將年代因素融入節目中去,充分滿足受眾的懷舊心理,延展了整個欄目的收視群體。首先,參賽的明星歌手既有出道20年以上的齊秦、黃綺珊、黃貫中等人,又有出道10多年的羽·泉、彭佳慧,以及出道6年的尚雯婕和7年的楊宗緯,可謂老中青三代歌手齊聚。“演藝明星顯然具備了彌合不同受眾群體需求差異的天然素質,能夠在節目中擔當起吸引不同層面觀眾眼球的任務”[3]99,不同年代的歌手作為一種年代標志,很容易勾起觀眾的青春記憶和懷舊心理,并在情感上和認知上與有著相同背景的觀眾形成共鳴和互動。電視觀眾可能只是因為對一首歌、一個明星產生的認可,最終會上升為對節目的認可,從而對節目本身產生依賴性。其次新生代歌手可以唱老歌,而新歌也可以被中老生代的歌手演繹,這種明星與歌曲年代的脫離與混搭,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舞臺時空,使得不同年代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也為節目增添了更多的娛樂性。此外通過經典歌曲的現代化改編,又使得經典和流行相得益彰,不同的代際元素在不同年代的受眾群體間有效貫通,激發了受眾群體間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產生了強烈的文化共鳴,使節目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
《我是歌手》節目中來自5個不同年齡層面的大眾評審,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欄目對不同受眾群體的極大包容性。與以往選秀節目只針對青少年受眾群體有很大的不同,該節目通過引入年代因素,從而使不同年齡層次的觀眾的興趣得到了迎合和滿足,并將兩代人甚至三代人鎖定在電視機前,改變了長期以來國內電視娛樂節目受眾過于單一的問題。《我是歌手》通過“代際因素”的疊加,使得老、中、青三代人可以在相同的時空獲得彼此不同的心理體驗,共同找到契合彼此內心感受、實現內心愉悅的收視點。不同年代的情感和觸動融合在一起,充分實現了代際之間感情的傳遞和溝通。受眾群體的擴大和黏性的增強,強化了不同受眾群體在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中的巨大作用,并借助新型媒介使得節目的影響力呈現倍增式擴散的態勢,使得受眾群體在數量和層級上得到擴大和延展。
《我是歌手》自開播以來在收視率上的一路高歌猛進以及在社會上引起的廣泛共鳴,并不是曇花一現的偶然現象。只有創新才能保持節目旺盛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也只有真誠才能在打動觀眾的同時緊緊地抓住他們的心。《我是歌手》無論是在節目內容還是節目形式上都處處展現著新穎的變化以及遠遠超出同類電視節目的立意與制作水準。在國內電視節目大量同質化和低俗化的今天,眾多電視節目都把視線轉向了國外的電視熒屏,對他國的同類電視節目或照搬或改造,以期在國內的電視競爭中獲取一席之地。《我是歌手》作為“舶來品”在國內市場所獲得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的節目創新和元素融合的手法值得中國電視人好好地體會和思考。
參考文獻:
[1]端木凡昌.電視真人秀節目的發展困境及對策[J].新聞愛好者,2012(6上).
[2]蔣寧平.根源、功能與動力——傳播心理視角下的明星崇拜現象[J].學術論壇,2009(12).
[3]莫林虎.電視文化導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4]劉建鳴.電視受眾收視規律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5]吳世彩.大眾文化的和諧價值[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6]榮耀軍.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研究〓多維話語系統的競爭與共生[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136.
[7]馮丹陽,毛東東.代際元素在電視綜藝節目中的傳播效果——以深圳衛視《年代秀》節目為例[J].新聞愛好者,2012(12).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