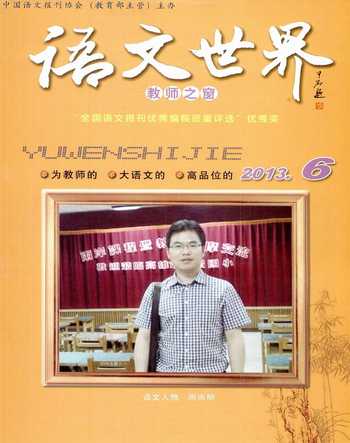語文:含英咀華,怡情養(yǎng)性
葉水濤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有一段精彩的臺(tái)詞:“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yōu)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dòng)!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gè)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gè)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zhǎng)!”
這段名言常常被引以歌頌人類的偉大。然而人之為人,人之區(qū)別于動(dòng)物,并不完全是自然選擇的結(jié)果。哲學(xué)家賀麟說:“人是能讀書著書的動(dòng)物。故讀書是劃分人與禽獸的界限,也是劃分文明人和野蠻人的界限。”人的優(yōu)美的儀表、文雅的舉動(dòng)、智慧的談吐均來自后天的學(xué)習(xí),主要是語言文字的陶冶。昭明太子蕭統(tǒng)說,讀了陶淵明的文章,“馳競(jìng)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是說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能使讀者心靈得到凈化,精神得到升華,文化得以傳承。
毛澤東同志1916年在游學(xué)路上寫。給友人的信:“今朝九鐘抵岸,行七十里,宿銀田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fā),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圖畫。”駢散相間,錯(cuò)落有致,田園風(fēng)光,躍然紙上,讓人有一種情景交融的美感,也使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世說新語》中魏晉名士的那種神情風(fēng)采。顧愷之從會(huì)稽回來,有人問他山川之美,顧回答說:“千巖競(jìng)秀,萬壑爭(zhēng)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極盡簡(jiǎn)練的言詞,勾勒出江南山水之美妙。日常的書信和談吐對(duì)話竟能如此雅致,這充分說明文學(xué)作品能很好地陶冶人的性情,培育和展示人的氣質(zhì)與風(fēng)度。
“修辭立其誠”是中國(guó)文化的傳統(tǒng),中國(guó)古代即使是公文類的文體都極其重視辭藻的修飾。《論語》中說,鄭國(guó)的政令要經(jīng)過四道手續(xù)才能寫。定。對(duì)此,孔子深表贊許。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策士游說、諸侯皆論辯滔滔,文采斐然,諸侯卿大夫都有賦詩言志和以詩為證的時(shí)尚。所以,孔子說:“不學(xué)詩,無以言。”唐代的科舉制度規(guī)定,取得進(jìn)士資格以后,必須經(jīng)過吏部詮試才能委派官職,詮試的標(biāo)準(zhǔn)有四條:叫做“身、言、書、判”,其中“言”要求“言辭辯證”,“判”要求“文理優(yōu)長(zhǎng)”。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判”即撰寫訴訟案中的“判詞”,它也要求用華麗精致的駢文寫成。這種重視辭藻句章和詩教的傳統(tǒng)對(duì)后世語言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與教學(xué)影響很大。
文學(xué)作品的境界取決于作者的境界。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解讀與學(xué)習(xí),孟子主張“知人論世”。王國(guó)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尚處于低潮時(shí),即以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yù)示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jīng)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yuǎn)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dòng)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gè)嬰兒。”氣吞山河的豪情溢于言表,磅礴凌厲的氣勢(shì)力透紙背。毛澤東的政論文建樹了新的藝術(shù)典范,這既是文學(xué)修養(yǎng),也是人格境界,它有著巨大的人格感染力量。
讀書何以陶冶性情?中國(guó)古典文論以“去俗”為作家修養(yǎng)的重要原則,黃庭堅(jiān)論書琺時(shí)說:“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也。”所謂“去俗”便是多一點(diǎn)書卷之雅氣,少一點(diǎn)市井之俗氣。書卷之氣來自文學(xué)名著的滋養(yǎng),增國(guó)藩提倡“涵泳”,即沉浸在語言文學(xué)的意境里,韓愈《進(jìn)學(xué)解》倡導(dǎo)“沉浸濃郁,含英咀華”說的是同樣的意思。沉浸其間,感同身受,潛移默化,便有豁然開朗的感悟,也能醞釀出妙手偶得的辭章。這也告訴我們:語文固然是工具;但不純粹是工具,起碼它是一種特殊的工具,絕不是世俗應(yīng)試的敲門磚,語文教育不僅是語言文字、語法章法的教學(xué),它關(guān)乎著人的德性修養(yǎng),它滋養(yǎng)高尚的人格情操與高雅的氣質(zhì)風(fēng)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