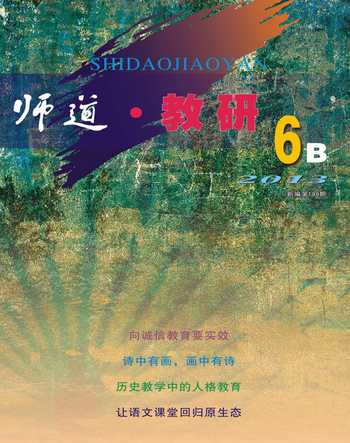“普九”教育,勿走極端
王愛娟
去年中考,我所任教的班中又有15人考上廣州市培英中學(重點學校,下稱“培英”),其余學生也被廣州市第65中、80中學錄取,升學率100%。消息一傳出,家長和教師都贊口不絕,群眾也拍手叫好,就連當地黨委和政府也發來賀信,還受到區教育局領導的表揚,真是形勢大好。作為班主任,我當然也滿心喜悅。因為近幾年的中考升學率都不錯,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學校“穩中求變”的管理理念。
幾年前,我校“普九”教育曾吃過不少“極端主義”的虧。先是領導和師生對實施“素質教育”、反對“應試教育”不夠理解,放任教師自行改革,有的科目不考試了,有的班級連作業也取消了。師生們重在搞一些被視為“素質教育”的活動,比如編節目搞演出,搞野炊或外出登山、踏青,串連兄弟學校搞球賽,參觀城市工廠等等,每一次活動都要停下課來,最多過后再補上課,名曰“調課”。這樣一來,中考時的重點學校錄取率偏低,家長們罵聲一片。后來我首先站出來反對這種“極端主義”的做法。紀律抓得嚴嚴的,課程上得滿滿的,練習布置得多多的,測試題目出得深深的,而社會活動一次也不搞,就連同學們一致要求的體育活動,也是限制他們在體育課上進行,其余時間不允許,還要求他們課余時間多回教室,自修時間也比其它班級多上一節。這樣實際上又走到了另一種極端,不但教師辛苦多了,同學們的體質也變差了。三年前曾經有好幾個學生經常患病,后來那幾個人沒有一個能考上重點線。特別令人遺憾的是當時的女班長因一分之差與“培英”失之交臂,就是因為她在中考時突然生病,一邊打針吃藥,一邊帶病應考,結果這個知識基礎比較扎實又勤奮用功的得意門生還是不能入讀理想的學校。學生知道情況后,幾天都臥床不起,不思飲食,還聲言不讀書了。家長十分無奈,當面質問我說報紙電臺都宣傳反對應試教育了,為什么現在還考試呢?我也心急如焚,前后家訪不下十次。經過一番和風細雨的思想工作之后,她終于堅強起來了,憤然表示去讀第二志愿的學校,一定要跟在“培英”的同學一比高下。
這件事曾一度使我陷入深刻的反思之中:學生是無辜的,雖然她因身體問題考少了一分,不一定不如高一分的同學,但她在學校一路歡歌,沒有經過一點大的挫折,在這方面我是有責任的。班長是她,團支部書記是她,學生會主席也是她,文學社長還是她,“三好學生”少不了她,“優秀學生干部”一定給她。一度認為“成績至上”的我,何曾想到給她一點挫折考驗呢?痛定思痛之后,我主動找學校領導檢討管理教育上的失誤,和領導一起總結經驗,從兩次“極端主義”的教訓中找出了“穩中求變”的策略:保證上課時間,大力開展課外活動;改革課堂教學結構,向45分鐘要質量,保留傳統考試,減少測試;鼓勵創新,支持實踐,講究德、智、體全面發展。這樣以后,我校的教學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了,以至去年中考又創佳績。
我以為學校“普九”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但改革不宜走極端。我們一定要防止極端主義反復重演,防止簡單片面的一刀切、一邊倒。所以說,實施素質教育是非常正確的,我舉雙手贊成,但實施素質教育并不排斥合理的考試,因為素質教育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素質的教育,而且古今中外的學校教育都考試。反對應試教育也沒有錯,但考試不一定就是應試教育。所以反對應試教育也不是取消所有考試。正如我國當代美術教育家吳冠中先生在為《世界現代藝術圖典》所作的序中所說:“傳統之所以有如此強勁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反傳統,反反傳統,反反反傳統的不斷發展……保管傳統的孝子和盲目崇外的浪子都不是創造者,也許回頭浪子倒居于優勢,既跨越了孤陋寡聞,又立足于土生土長。”這些真知灼見對教育改革來說可謂一言中的,十分精辟。其實我國的教育祖師孔老夫子也說過:“學而不思則殆,思而不學則惘。”我們既要反對死讀書,讀死書,反對脫離社會實際的閉門讀書;又要反對不讀書,不要書,反對不要知識,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活動。
總而言之,學校“普九”教育的改革應“穩中求變”,應在保留考試這個傳統的同時,考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反對那些濫考、偏考、偽考和對考試的濫用或曲解,反對一次考試定終身的弊端。我們應切實加強創造性的教育內容、增加社會實踐和發展個性的教育內容,變“應試教育”為“育才教育“,使我們的教育早出才、多出才,出真才、出優才。
責任編輯 魏文琦